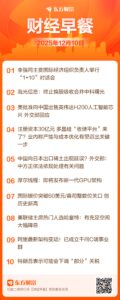一战种下的因,结下二战的果
【来源:虎嗅网】
1931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不为人知的战争》中写道:
“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双方都毁灭了。所有的皇帝及其继承人都被杀死或废黜了……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所有人都遭了殃;他们所给的一切都属徒劳。没有人能得到什么……那些从战场上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归来时无论是带着胜利的桂冠还是失败的噩耗,他们的家园都已被战祸吞噬。”
1928年,恩斯特·荣格在《作为内在经历的斗争》中写道:
“这场战争是暴力的开始而非结束。在这个熔炉里,世界被锻造出新的边界和社会。新的铸模想要被鲜血灌满,而权力则被铁拳掌握。”
他们所描述的战争,是带给欧洲人巨大伤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战争有结束的一天,但实际上,战争往往没有随着停战而结束。
一战就是如此,对于战胜国来说,1918年11月11日就已经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但对于战败国来说,它却是一场巨大暴力灾难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一战对欧洲的破坏性并不只是西线残酷的战斗,而是其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即在战后爆发冲突的地区,人们被革命、大屠杀、种族清洗和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彻底野蛮化。
1917年至1923年间,遍布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暴力冲突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而正是在这样的战争废墟上,极端意识形态开始形成,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别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胜利,并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1917—1923》一书中,德国学者罗伯特·格瓦特试图向人们揭示,对于一战战败国及其人民来说,冲突和流血事件直至1923年才暂告结束,同时,被遗忘的战后暴力冲突其实成为了欧洲堕入黑暗的关键一步。
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就是个例子,书中写道:
“1922年9月9日,由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而引起的仇恨降临到士麦那城。当土耳其骑兵开进这座奥斯曼帝国曾经最为繁华的国际化都市时,占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东正教基督徒一直在士麦那和平共处,但近十年的战争改变了这种民族关系。奥斯曼帝国在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1914年8月它作为德国的盟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发现自己又一次沦为战败国。”
残酷冲突使得穆斯林和基督徒都遭遇惨重伤亡,当希腊军队被土耳其民族主义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击溃后,在仓皇撤退时对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穆斯林居民一路烧杀抢掠,士麦那的基督徒担心会因此遭到土耳其军队的报复。
事实也确实发生了,罗伯特·格瓦特写道,土耳其军队攻占士麦那不久,士兵们就逮捕了希腊入侵的坚定支持者东正教大主教克里索斯托莫斯。一个旁观的法国水手回忆道:
“人群尖叫着扑向克里索斯托莫斯,把他沿着街道拖到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犹太老板伊斯梅尔从门口紧张地张望着。有人把理发师推到一边,抓了一块白布勒在克里索斯托莫斯的脖子上。他们扯下主教的胡子,用刀挖出了他的眼睛,砍掉了他的耳朵、鼻子和手。最终,饱受折磨的克里索斯托莫斯被拖进一条背街小巷,扔在一个角落里直至死去。”
大主教的惨死只不过是暴力狂欢节的前夜序曲,这令人想起了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时期对敌人城镇的洗劫。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估计有3万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还有很多人被土耳其士兵、准军事部队或是当地的青少年团伙抢劫、殴打和强奸。
当基督徒们的房子被烧后,人们只能逃到码头避难。英国记者乔治·沃德·普莱斯目睹了港口上的屠杀,并将之记录下来:
“一道连绵不绝的火墙,足有两英里长,锯齿状排列的20多处熊熊烈焰如火山爆发般喷吐而出,火舌扭动着蹿向100多英尺的空中……海水被映成深深的红铜色,最糟糕的是,成千上万的难民拥挤在狭窄的码头上,身后是不断进逼的烈火,面前是深不见底的海水,从那里不断传来恐怖绝望的疯狂尖叫声,几英里外都能听到。”
《战败者》所提到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一个界限明确的时间段,通常认为始自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的签署,迄于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然而,这个时间段只是对主要的战胜国,即英国和法国才有意义,它们在西线停止了敌对活动,的确意味着战后时代的开始。“然而,对于生活在里加、基辅、士麦那,以及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许多地方的人们来说,1919年没有和平,只有连绵不绝的战乱。”
俄国学者彼得·斯特鲁韦就这样描述自己的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停战协定而正式结束了。然而实际上,从那一时刻开始,我们所经历的和正要经历的,都是这场大战的延续和转型。”
一战后的许多战争,往往是新兴国家和旧国家之间的冲突,如苏波战争、希土战争等,它们爆发于哈布斯堡和奥斯曼等崩塌帝国的疆域,实际上是新边界的划定。还有一些国家爆发内战,比如匈牙利和芬兰。
暴力无处不在,旧帝国一个个崩溃,新政权的更迭充满了血腥。仅在1917年至1920年间,欧洲就经历了至少27次以暴力方式进行的改朝换代,许多都伴随着可能或已经爆发的内战。最极端的情况当然就是俄国本身,内战导致300多万人丧生。
罗伯特·格瓦特认为,战争扭曲了人性,也让暴力在战后持续,人们无法在战争的狂热状态下回到原先的模样。同时,战后各国政府多半疲于奔命,太多事情无暇顾及,也让许多群体遭遇困境和苦难,继而试图以暴力解决问题。尤其是背负着巨额赔款的战败国,崩溃不可避免。
至于一战后的民族自决,看似轰轰烈烈,也符合民众的呼声,但各种纠纷和冲突也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甚至无法解决。奥斯曼帝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许多人被迫离开祖先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前往完全陌生的“祖国”,同时又被“祖国”所嫌弃。奥匈帝国也是如此,诞生的新兴民族国家互相驱逐非本民族居民,无数人流离失所。
一战前的欧洲,处于一种高歌猛进的状态。人们已经忘记战争,甚至认为从此不会再有战争,工业和科技的进步带来太多憧憬。在欧洲的一些大都市,比如维也纳,物质与文化都极为璀璨,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光辉。谁也不会想到,一切竟然戛然而止。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深情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还有他所享受的极其充分的个人自由,也为大战的到来感到痛心。《战败者》中还写道:
“在1914年前,生活在罗曼诺夫帝国的犹太人遭到周期性的屠杀,而生活在哈布斯堡帝国的犹太人则相对安全,他们无疑认为,作为公民和臣子,这个双元君主国可以保证他们的权利和地位。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犹太作家斯特凡·茨威格或约瑟夫·罗特写了大量关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怀旧小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对罗特那样的犹太人来说,相比生活在一个在种族或宗教上有排他性的小国家,他们宁愿生活在一个能为少数民族提供法律保护的多民族的大帝国。”
匈牙利作家山多尔·马洛伊也见证了这一切。他的代表作《一个市民的自白》,就描述了匈牙利市民阶层的生活以及新旧时代的碰撞。1918年,18岁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因为身体羸弱未被录取。这当然不是坏事,因为应征入伍者多半成了一战炮灰。他随之进入布达佩斯的帕兹玛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一年后转入文学系,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
也是在这期间,还不满20岁的马洛伊选择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逃离——与他书中所描写的童年离家出走完全不同的逃离。1919年10月,为了远离布达佩斯的革命风暴和他并不喜欢的家族阶级,他前往德国。这似乎预示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他不愿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也厌恶革命,作为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偏偏未能生活在十九世纪末的田园牧歌中,等待他的唯有流亡。
无论茨威格还是马洛伊,都敏锐地看到了一切的实质:在暴力和极端之后,政治秩序的重建和民族国家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更不是简单以民主或专制便可明确区分。至于民族主义的潮流,固然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但人为且简单粗暴地进行疆域划定,显然不能解决那些延绵百年甚至千年的问题。茨威格和马洛伊对昨日世界的怀念,也绝非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而是对自由空气与多元化的追索。
类似沙俄和奥斯曼这样的大帝国崩溃,原本是历史必然,但带来的动荡可谓后果惨重。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派系冲突、意识形态冲突乃至农村与城市的冲突,在帝国的土地上不断上演。
同时,民族国家积极抢占领土的行为,必然造成一个现象:军队在争议边境地区交火,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对平民展开各种暴行。
原本在欧洲大陆上存在的多元化,反而在这样的重构中消失,为族群冲突埋下了更恶劣的种子。民族自决中的血腥暴力,也让许多潜藏的野心家们找到了“灵感来源”,也让二战的悲剧最终到来。
《战败者》中就写道:
“没有哪位政治家比希特勒对观察1918年至1923年间安纳托利亚的形势发展更有兴趣。……希特勒不仅佩服凯末尔对协约国不妥协的抵抗,还企图效仿他的方式,在经历战争失败后建立起一个完全世俗的、国家主义和民族同质化的国家。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政策,以及凯末尔对土耳其基督徒的无情驱逐,都在纳粹的幻想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它们成为未来几年希特勒美梦的灵感来源和计划的范例。”
所以,一切正如罗伯特·格瓦特所总结:“纳粹德国及其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公然实行的种族灭绝的帝国计划,主要应归咎于一战以及1918年至1919年间重新划分边界造成的民族冲突和民族统一主义。”
《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1917—1923》
[德]罗伯特·格瓦特 著,朱任东 译,译林方尖碑,2024年2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