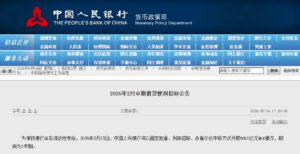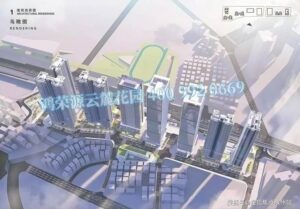拒当“文科女友”,从停止自证开始
【来源:虎嗅网】
对于“文科女友”的反抗,可能始于停止向自己不认可的世界证明。
4月7日,一校园媒体发布了一篇题为《游戏少年逆袭发顶刊,武汉伢李展拿下雷军奖》的推文,介绍一位雷军奖学金获得者的科研成就与成长经历。
文章本意是塑造一个励志学霸形象,但在“生活与科研的平衡术”的一节中写道:“文科生女友包容其非常规作息,包揽三餐家务,使其无后顾之忧;李展则用理科思维影响女友,鼓励她探索交叉学科。”
这一推文被指隐含“文科等于辅助”“女性应承担家务”的刻板印象,有些网友认为这类推文追求“造神”效果而“用力过猛”。
此外,“文科女友”“文理、男女搭档的平衡术”等标签在学科和性别的双重身份下,引发网友进行大规模的“反击”式发帖和“玩梗”——“我努力不是为了成为谁的文科女友”“本人文科男,招募一名理科女友”“可是妈妈,我就是别人的文科女友”。
网络用户通过参与梗的传播来缓解焦虑或表达不满,进而寻求认同和关注。但渐渐地,反击“文科女友”的帖子中充满了“国奖”“专业排名第一”“实习科研社团恋爱多手抓”等元素,人们似乎是在通过证明自己“足够优秀独立”来撕下“文科女友”的“辅助”标签,但陷入了优绩主义的新一轮规训中,甚至借此机会“起号”进行自我展示。
引发争议的公众号推文与反对其言论的互联网发帖同在优绩和量化的框架中,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人都是“输家”。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玩他们的游戏?
从抵抗到表演:“娱乐化”使问题失焦
推文将“文科女友”塑造为男友的后勤保障者和“跨学科思维”的提供者,本质上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浪漫化”包装,其暗含的价值取向与年轻一代女性网络用户的主体性觉醒形成冲突。
随着话题热度攀升,“文科女友”标签逐渐脱离具体事件,演变为一种新型人设构建工具。部分用户通过“高学历+反讽文案”制造反差感,既满足了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批判需求,又契合平台算法对“冲突性内容”的偏好。
在信息过载的网络社交中,公众往往通过关键词而非完整文本参与讨论。“文科女友”作为高度凝练的标签,天然具备“病毒性”的传播力,形成“文科VS理科”和“男性主导VS女性从属”的双重批判。
网民无需深究原文细节,仅需抓住“文理科+男女友”这对矛盾组合便可以进行大规模讨论甚至个人情感宣泄。
互联网生态中的“起号”逻辑中最常见的便是将身份特征转化为可量化数据。
最初互联网用户晒个人成就的反抗行为,本质是通过“自我展示”解构“文科女友”的工具化设定,但无形中迎合了主流社会对“成功”的量化期待,原本具有批判力的观点逐渐滑入“表演”的范围。
进一步地,在算法激励中通过“玩梗”吸引潜在粉丝注意。
“浪漫逆袭”文学、“平衡术”等“梗”的形成过程中,原始语境被剥离,“知梗,不知事”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文科女友”的严肃讨论也渐渐消失。
此外,女性主义核心诉求的表达也被极度简化与个体化,如“今天官微情侣分手了吗”“文科女友的父母知道该多难受”的言论甚至转向对个人生活的窥探与道德审判。
女性主义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必然与娱乐化产生交集,但其核心挑战在于避免批判性被流量逻辑收编、严肃性被玩梗消解。
当“利用娱乐形式反讽”仅停留在表象甚至走入更加刻板的优绩主义,对性别不平等与学科歧视的反抗便可能沦为“象征性”行为;当“批判性别歧视、学科歧视”与“制造对立梗”的边界被模糊,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可能就会被稀释为自嗨的口号。
“优秀”悖论:警惕人设背后的优绩主义新衣
在娱乐化的风险之外,强调“我比理科男更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优绩主义的惯有思维,与用户发帖的初衷——反抗“文科女友”叙事南辕北辙。
借由不断罗列数据与荣誉,个体看似在对抗以性别和学科划分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正是这一过程中复制了评价体系的封闭逻辑,将成功单一化,并以此为依据固化了不合理的结构。
强调“我也发过顶刊所以我不是附属品”,无形中承认了科研产出优于家务劳动的价值排序,也是对原文中获奖者女友的新一轮伤害。
福柯认为,现代规训机制不再依赖暴力压制,而是通过塑造理想主体形态实现控制。
如果只有那些符合特定范式的成绩才具有“资格”去定义自我价值,如果个体的身份被逐步固定在“优秀”或“非优秀”的二元分割中,那么任何未能达到标准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附属”或“从属”的一员。
当“最有力的反击”是绩点更高、实习更卷、拿钱更多,当反抗话语与被反抗体系共享同一套评价标准时,批判本身可能沦为共谋。
就像戴锦华教授在电影《初步举证》首映礼的映后交流中谈到的:“我自尊、自爱、自强、自律的同时,是不是其实也包含了对弱者,对不成功的女性,对受害者女性的某种不屑?”
正如《初步举证》中的法律精英泰莎,因性侵成为司法体系中的“弱者”,她的痛苦并非源于个人能力不足,但法庭依旧要求她以“完美受害者”的姿态自证清白,正如优绩主义要求普通人用学历、成绩证明自身价值,否则便沦为“失败者”。
所以,无论是旗帜鲜明的“优秀人设”,还是“我是分母,是小镇做题家,是孔乙己,是家务文科女友,是找不到工作应该反思的大学生”等自嘲,都没有跳出自证陷阱。
表面上的自我证明,实则是自我固化,因为这要求个体不断在已有标准中寻找认同感。
古希腊的阿斯帕西娅在男性主导的雅典开办沙龙时,从未试图证明女性与男性哲学家“同样理性”。真正的解放或许始于一个自问:如果明天所有评价体系消失,我们是否还能拥有自我认可?我们能否想象不以“证明”为前提的存在?
当社会不再提供“成功人生”的标准答案,我们是否敢于定义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文科女友”的反抗,可能始于停止向自己不认可的世界证明。
“爽感”陷阱:个体优秀不代表结构解困
劳伦·贝兰特在《残酷的乐观主义》中认为,人们对那些实际上强化现存秩序的文化产品投入情感,只因它们提供了对抗性的短暂快感。
在这个层面上,反抗“文科女友”的叙事中,平台助推“大女主”爽感帖文传播,本质是将性别议题转化为可消费的内容产品,既收获“支持女性主义”的道德资本,又通过流量分成获利。
当奖状、证书等的种种具体成就伴随着卡点bgm令人目不暇接时,观众很容易会陷入“女生独立自强就应该是这样”,或者“优秀的女生其实有这么多只是原推文思想陈旧”的错觉中。
英剧《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中,女主角玛德琳对自己曾经的精神偶像完成“复仇”,曝光披着喜剧、玩笑外衣的“厌女”的工作环境。有观众称之为“2024年最爽英剧”,称其“撕开表象”“祛魅反杀”。
但或许很少有人意识到,当玛德琳必须同时扮演“开得起玩笑的漂亮酷女孩”和“情绪稳定、专业过硬的职场精英”时,她的胜利并没有超出个人抗争而动摇系统,本质上仍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无奈。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中始终未被揭露的那则“厌女”笑话,类似于一个萦绕在所有人头顶的现实拷问——“采茶女”的工作环境、保洁阿姨的休息空间、家政工人被拖欠工资、职场孕妇遭遇晋升天花板等问题是否已被挤压到视线之外?
从结构性质疑滑向个体励志叙事时,会弱化和遮蔽系统性压迫的复杂性。
我们期待的不应是“玛德琳式例外”抑或“优秀女生不附庸”,而应该是每个女性、每个普通人免于恐惧的生存环境。
正如Z世代创作型歌手Chappell Roan在发表格莱美获奖感言时,放下奖杯,郑重地捧起本子“问责唱片公司”:“我告诉自己,如果我有一天赢得格莱美奖,我会要求那些从艺术家身上谋利数百万美元的唱片公司和音乐行业,提供给歌手们可持续的工资和医疗保险,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发展的歌手们。”
在一轮轮公共讨论中,为优秀的少数个体欢呼与正视多数弱势个体的困境并不冲突,少一次下意识的“自证”和“二次比较”,就能多留一分质疑和责问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