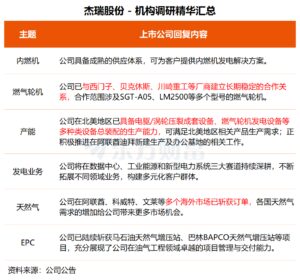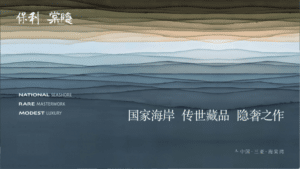马来西亚数字市场,有哪些出海机遇?
【来源:虎嗅网】
东南亚数字浪潮奔涌之际,马来西亚正以“黄金区位+政策杠杆”构筑战略高地。当前马来西亚数字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其数据中心市场规模预计从2022年的13.13亿美元跃升至2028年的22.52亿美元,年均增速达9.4%,其发展速度超越日澳、仅次于印度。
马来西亚新政府正在实施“数字经济强国”战略,算力基建与政策红利形成共振。值得注意的是,4月11日,深圳产业出海联盟与马来西亚有关方面签署了金额达220亿美元的《中马国际高科技生态产业园协议》。这种产业集聚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双重机遇——既是头部企业技术输出的竞技场,更是中小企业借船出海、融入区域生态的关键入口。
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MyCC)从2024年7月开始,启动了一项对其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市场审查,旨在评估和加强马来西亚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的竞争格局。进行初步调研后,该机构在3月对外发布了调研的中期报告。这份MyCC的中期报告可以看作是深入了解马来西亚数字经济的探索性工具,本文通过解读该报告,帮助读者深入了解马来西亚数字经济现状及未来趋势,希望对中国企业数字化服务“出海”能够有所助益。
一、马来西亚数字市场的自评估问题
1. 数字经济迅速增长,但市场集中度高,反竞争行为凸显
根据报告,2023年马来西亚的数字经济规模达4277亿林吉特,占GDP的23.5%,年增长率10.3%,远超整体经济的增速(2.4%)。ICT及相关行业提供120万就业岗位,占总就业7.8%,其中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及ICT服务为关键领域。
但报告似乎表明,某些市场趋势正预示着新兴市场失灵,例如数字细分行业的集中度或主导地位。
如移动操作系统与支付方面,Android(85%)与iOS(15%)主导市场,设备预装应用限制第三方竞争,Google Pay与Apple Pay抽取15%~30%交易佣金,挤压本地支付服务商;电子商务平台方面,Shopee(55% GMV)、Lazada(30%)、TikTok Shop(10%)形成寡头格局,强制物流绑定、搜索竞价排名抬高中小企业成本,限制价格自主权。数字广告和在线旅游等,也面临类似的情况。
2. “数据”成为马来西亚政府担心的监管核心议题
中期报告指出,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其收集、分析和应用能力直接决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同时也指出了,马来西亚政府对数据隐私和保护的担忧。MyCC认为,在马来西亚的头部平台,如Grab、Shopee、TikTok正在通过以下方式构建数据壁垒:
(1)用户行为数据垄断:平台通过高频交易场景——支付、搜索、社交——积累海量用户画像,形成“数据护城河”;
(2)算法优势:基于数据的机器学习模型优化服务,如个性化推荐、动态定价等,大平台正在利用这一算法优势挤压中小竞争者生存空间;
(3)跨市场扩张:利用数据打通不同业务线,强化市场支配地位,如Grab从出行延伸至金融、电商。
3. 政策与监管框架亟待完善
马来西亚已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特定行业的法律法规,以规范数字经济的关键领域,包括1998年的《通信与多媒体法》、2012年的《消费者保护条例》以及2024年的《个人数据保护法(修正案)》。其中,2024年《个人数据保护(修正案)法》引入了保护隐私的重要措施,包括强制任命数据保护官,并加大对数据泄露的处罚力度。
然而,该报告似乎暗示,现有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可能不足以应对这些发展,尤其是 2010 年《竞争法》,缺乏针对平台经济特点(如算法合谋、数据垄断)更新,难以适应数字市场动态。
具体而言,该报告认为现有的数字政策与监管框架仍存在缺陷:
(1)立法缺口:缺乏《数字经济法案》统筹数据共享、反垄断及创新激励;对于大型平台数据垄断风险,缺乏监管依据;现行《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未明确数据跨境传输规则,且未覆盖非个人数据(如匿名化数据集)的共享与使用;
(2)执法分散:马来西亚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分散在多个部门及机构中,如数字部、通信部、贸工部等,MCMC(监管通信基础设施)与MDEC(推动数字经济项目)在数据治理、5G部署等领域存在权责交叉,进一步降低了监管效能;尽管《国家数字蓝图》提供了战略方向,但执行中缺乏统筹协调;
(3)跨境执法无力:全球科技巨头(如谷歌、苹果)在马来西亚市场的垄断行为(如搜索排名偏袒、应用商店30%佣金),受限于《竞争法》属地原则,MyCC难以直接干预;马来西亚与东盟国家的数据治理合作停留在框架协议,缺乏具体执行机制;未加入《数字市场法案》等区域性协定,无法援引“守门人制度”约束跨国平台。
二、马来西亚数字监管趋势分析
从报告的整体分析和建议可以看出,马来西亚政府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数字市场的快速增长和集中化需要政府采取新的干预形式。基于上述数字细分行业的集中度或主导地位的分析,判断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出现了系统性失灵,因此政府应当引入更多且更集中的数字监管方法。
基于报告内容,马来西亚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下一步监管可能聚焦以下方向:
1. 强化反垄断执法,遏制平台经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马来西亚多次提及国际合作与欧盟《数字市场法案》(DMA),因此很可能效仿DMA,将大型科技公司列为“守门人”,禁止其捆绑服务、自我优待或限制跨平台数据流动。
在提及“Grab并购优步”的案例中,MyCC因缺乏跨境并购审查权,未能阻止交易后的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如司机佣金上涨20%)。因此,MyCC很可能会要求扩充其监管权力,使其可以建立“事前监管”机制,要求平台报备并购与协议条款。
2. 完善数据主权框架,平衡隐私保护与数据流通
平衡数据利用与公平竞争将是马来西亚的政策重点,既要避免过度限制创新,也要防止平台滥用数据权力。该报告提及2025年计划中包括成立“数字信任与数据安全委员会”,主要为了统一协调数据治理与跨境合作。
数据本地化,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马来西亚政府很可能会参考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进一步细化《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要求金融、医疗等敏感数据境内存储。
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与新加坡、新西兰等共建数字贸易标准。
3. 遏制细分行业垄断风险,推动本土数字基建与中小企业保护
马来西亚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强国,但是马来西亚却是世界前七大半导体产品出口地之一,也是全球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主要中心之一。2024年,马来西亚公布了该国的“国家半导体产业战略”(NSS),通过提供53亿美元的半导体补贴,来撬动约1062亿美元的半导体投资,成为“作为最中立、最不结盟的半导体生产地点”,作为发展5G与AI的基础设施。
具体到数字的细分领域,马来西亚将重点遏制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与扶持本土中小企业相结合:
(1)数字广告: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可能会强制谷歌、Meta公开广告竞价算法黑箱,拆分数据垄断业务,就像英国CMA 2023年要求Meta出售Giphy一样;另一方面,扶持本土广告交易平台(如马来西亚Premium Publishing Marketplace),削弱巨头议价权。
(2)电商平台:强制电商平台降低佣金率,参考印度2022年要求亚马逊、Flipkart佣金降至5%;
(3)在线旅游:出于对价格平价条款、征收高佣金率等行为的担忧,MyCC可能将设定佣金上限,并禁止价格平价条款,要求平台允许酒店动态定价,如意大利2024年对Booking.com的禁令;
(4)金融科技:马来西亚政府可能会效仿澳大利亚2023年制定的规则,将“先买后付”(BNPL)纳入央行监管,限制过度借贷。
总体而言,马来西亚正在力争成为东盟数字规则制定的关键参与者,很可能将采取“防御性监管”策略,核心目标是防止跨国巨头(主要是美国和中国数字企业)垄断、保护本土数据主权。通过报告的分析,其短期重点可能会集中在电商与支付领域反垄断,中长期则布局AI伦理与跨境数据治理。
三、对中国企业的建议
中国企业可以根据马来西亚监管的研判,将合规前置。除了在马来西亚设立本地合规团队,更需要实时跟踪《个人数据保护法》(2024修正案)的进一步细化和修订,以及2010 年《竞争法》可能的修订趋势,针对数据存储、算法透明度等要求调整运营。还可以参考华为在欧盟的“合规沙盒”模式,主动与当地监管机构合作测试新产品,提前规避潜在冲突,把监管成本转化为竞争优势。
但仅仅合规的操作还不足以应对监管风险。很明显,“技术民族主义”的趋势正在加剧全球标准分裂,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数据监管趋严,中国企业应当尽量避免在马来西亚市场陷入被动适配困境。比如通过技术合作、股权投资融入本地经济网络,以降低政策敏感度,就如TikTok与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共建直播电商生态;如有可能,优先采用本地数字基础设施,减少对跨境数据流的依赖,特别是中小型企业。
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MyCC)就中期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之际,科技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马上就该报告进行了评论和建议。该智库通常主张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时常作为美国科技企业的游说力量。在4月11日发布的这份建议中,主要是为了阻止马来西亚政府引入新的、可能事前义务的措施,避免美国企业在东南亚也遭遇欧盟一样严格的规制。
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也应当积极参与到当地政策制定和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例如通过行业协会,或者联合其他东盟合作伙伴,向马来西亚政府提议“监管沙盒互认”机制,推动中国标准与东南亚政策框架协同演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nternet Law Review,作者:互联网法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