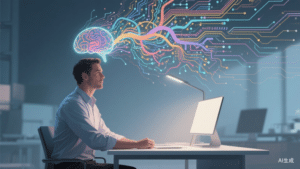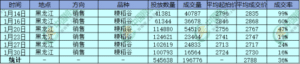“天地不仁”时代的希望哲学
【来源:虎嗅网】
早上听秦晖教授讲“周秦之变”,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变动与大一统帝国的崛起。这一变化对当时的士人、思想家、包括孔子,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2000多年前的那段时间里,周朝宗法制和礼乐制度渐渐瓦解,贵族权力分裂,战争频繁,民众动荡。对于孔子来说,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意味着文明的崩塌,因此他深深感慨“礼崩乐坏”。
孔子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他希望恢复和弘扬周朝礼乐文化,尤其是“仁”的思想——即礼仪与道德的和谐。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他说自己并没有创立新学说,而是以传承为主,要恢复过去的文化和道德规范。这种无奈,正如《论语》中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一直推崇的,是一种内心的合一与秩序,而不是迎合动荡的时代。
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感慨,带有强烈的末日气息,感受到一种文明和传统的终结。今天,我们或许也有类似“末日感”,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终结带来的动荡、政治与经济的不确定性,世界的稳定性似乎也在走向终点。
佛陀入灭(圆寂)前,也曾预言过人类将进入“末法时代”,意指佛法逐渐衰微、修行者难以证道的时代。
佛教把佛陀入灭后的时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正法时代(约五百年)。佛法兴盛,修行人能真正理解佛陀的教导,有很多人可以通过修行证果成道。
像法时代(约一千年)。佛法的外在形式(如寺院、仪轨、经典)依旧存在,但修行者多追求形式,证果者少。
末法时代(之后的漫长时期)。这个阶段中,佛法仍在流传,但多数人难以理解佛法的本意,修行人多而证果者几无,僧团腐化,众生烦恼深重。
所以,“末法”原意不是指世界末日,而是佛法的实修力量衰微、形式大于实质。我在这里只是借用这一说法。
问题在于,只有佛教会有“末法”思想,其他宗教里为什么没有类似说法?
根据佛教的理解,宇宙并非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周期性、不断变化的状态。这个变化不仅体现在个体生命中,也体现在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上。这个不算规律的“规律”和洞见,目前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
昨晚我在翻译一行禅师《Going Home:Jesus and Buddha As Brothers》时,他也讲到,佛教徒相信轮回,相信人有多次生命的可能性。佛教界很少使用“轮回”(reincarnation)这个词,而是用“重生”(rebirth)。人死后,可以重生,获得另一次生命。
但在基督教中,你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是获得救赎唯一的机会。如果你糟蹋了它,那么你将永远得不到救赎。你只有一次生命。
当然,不同文化对“末法”的理解也不同。中国人受儒道影响,常常将“末法”与“乱世”“劫难”联系起来。
在现实中,“末法”是否真的存在呢?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信仰的兴衰与人心的迷茫。现代人虽然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焦虑普遍,也容易让人认同“末法”说法。
我更愿意将佛陀提出的“末法时代”,视为他老人家发出的醒示之语,目的是鼓励人们不要只信形式,要真正实践佛法。
对当下的我们而言,这份提醒就是在乱糟糟令人沮丧的环境中,多反观内心,修身养性。更重要的是,有能力在纷乱世界中,寻得一份笃定、清净与觉悟。
时代复杂,但正如《法华经》所说:“一灯能除千年暗。”
只要有人真修佛法,哪怕身处末法,也能得道。
佛法之外亦如是。孔子,他当然是悲观的,但他没放弃,最后成为撑起“轴心时代”的重要一极。
个体的人,确实容易将眼前的困难与挑战看得无限大、压力山大。然而往回推八十年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无数个体在承受更为严酷的现实与人生。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提出他的独特史观,认为历史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一种波动、循环的状态,社会的变革并不总是通过一个清晰的“进步”轨迹走向终极目标。历史变迁不是完全由人类行动决定,也受外部环境和“天命”的深刻影响。
他的研究与思考最初是限于中国历史的,但他的非线性历史观、历史的周期性与惯性、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等思想,实际上具有全球适用性。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历史变迁时,都可以在这些理论中找到相似的历史动力和冲突。
几千年来,人类经历了无数“末日般”的时刻,从瘟疫、战争、王朝更替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的动荡都让每个人觉得“天要塌了”,读一读齐邦媛的《巨流河》之类的作品便可清晰了解这一点——毕竟生命过于渺小和脆弱。但人类还是一步步走了过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带孩子远渡重洋求学,身处文化和政治都高度复杂的美国,又目睹新的政治权力在全球挥舞关税大棒——这样的背景下,难免不感到迷茫。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我: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
寻求内心的合一与秩序,可能才是普通人最不坏的生存方式,也是唯一的解脱之道。
这种“最不坏的生存方式”,不依赖外部的安稳与保障,而是源于内在的自足和安宁。当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让人无所适从,能做的只能是回到内心宁静,获取踏实应对困境的力量。
是的,我已经有答案了,只是需要通过记录,引发一些回音来坚定它。
1. 承认不确定性,但不失希望
未来本来就从未确定,从国内到国外,看似安稳的日子可能随时翻转,动荡的阶段也会悄然翻篇,只是当时不觉而已。
把所谓“末法时代”想象成人类社会一个转折点——全球秩序重构期。旧的模式不再适用,新的模式尚未建立。这种“裂变”时期,总是令人不安,也是正常的。
但不安不等于灭顶,可能正是新生的前奏。
2. 小处着眼,大处着想
我没办法改变既成事实,也左右不了国际局势,但我能决定今天怎么过,能陪儿子读哪页书,能为自己的成长加一盏灯。
至于儿子,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相比一些同龄人,他能看到世界更真实的一面,会拥有更强的判断力与适应力。我既是护航者,也是他的同行者。
正如昨天American History课上,老师和他们讨论高额关税的问题,讲美国普通人怎么看待此事。这在国内或国内媒体上,看不到。
3. 看长线,种自己的田
哲人们常说“伟大时代不属于我们,但我们可以为未来播种”。
我们在异国上学生活,这段人生是我们自己的“田”,播下亲情、知识、经验、文化体验的种子。无论世界如何动荡,它依然可以开花结果。
“末法”如果有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别被时代裹挟。
4. 保持连接,不孤立自己
我相信,感受到“绝望”的一定不是个人化的体验,它更多是一种群体情绪。身处异国有时会放大这种感觉。
我体验,我读书,我记录,就是疗愈心灵的好方式。
铃木俊隆禅师在《禅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写过:
“我们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有的人抱怨风浪,有的人抓紧船舵。禅修的目的,不是让海平静下来,而是教你如何在浪中划桨。”
既然已经在浪中划桨了,而且还不会溺水,至少还会游泳求生,那就继续向前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跑步有毒,作者:跑步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