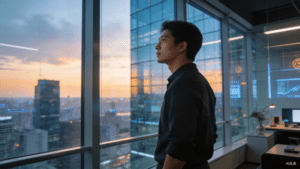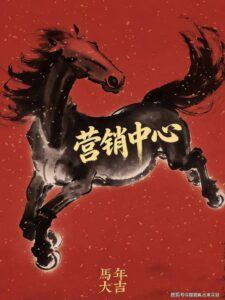江浙沪最流行的City Dig,早被河南玩明白了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九行Travel (ID:jiuxing_neweekly),作者:简墨
每到春季,全国各省市的绿地上都会“长”满人,尤其是野菜疯长的田野、森林、河边。浅露青叶的折耳根、蕨菜、茭白、水芹菜、艾草等纷纷成为桌上美食,甚至令无数人闻之颤栗的藿麻也一跃成为了南方人烫火锅的食材。
相较南方,北方大多城市总是回温晚、绿得慢,直到4月左右才能在田埂上觅得一些可以食用的野菜。稍早的有茵陈、荠菜等食叶的,还有越冬的鬼子姜、宝塔菜等食根茎的。
河南人从野外回到厨房,接下来就是“蒸春”。小时候,我经常和母亲一起到地里挖野菜,她总是能将那些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食材变成美味。
其中最常用的烹饪方法是蒸:将面粉裹在野菜上,先上笼屉蒸熟后,或浇上鲜辣的蒜泥汁,成为一道爽口凉菜;或下锅加蒜苗、韭菜等炒制后,成为一道热菜。
母亲告诉我,这种做法是她从外婆那里学来的,也是很多河南人代代传承的记忆。如今,在河南的餐馆里,还能经常看到蒸菜的身影。虽不似洛阳水席、道口烧鸡、黄河大鲤鱼等声名远播,味道却毫不逊色。
可以说,如果春天到了河南,不尝一尝这限定的蒸菜味道,就算白来了。
吃蒸菜,就是吃春
在河南驻马店市驿城区有一家稍显古色的饭店,白墙灰瓦和高高竖起的房角让人一眼就能想到烟雨如织的江南,甚至店名都带了“江南”二字。但有意思的是,这家店主打的不是南方菜系,也不是驻马店特色美食,而是信阳菜。
去年,我前往驻马店拜访朋友时,她曾特意带我到这家店里就餐,并极力推荐道:“这家店看着不华丽,但有很多特色美食。”其中一道名为“三色蒸菜”的主食,尤让人印象深刻:红白绿三种颜色的食材分开摆在盘子里,每种食材上都裹了一层淡淡的面粉。
朋友告诉我,这道菜是由胡萝卜丝、土豆丝和芹菜叶加盐、裹面粉上笼蒸制的,不仅可以当主食,也可以作为一道菜品。她说:“我会带每个来驻马店的朋友品尝三色蒸菜。”
用蒸菜宴客在我的家乡洛阳并不多见,以至于我后来还十分新奇地同另一位朋友推荐,对方却告诉我,蒸三丝在商丘也十分常见,不少主人家宴客时还会特意点这道菜,以表达日子蒸蒸日上的美好愿望。“只不过,我们多用胡萝卜、白萝卜和茼蒿,不过我更喜欢蒸扫帚苗。”言罢,她问我:“难道洛阳不吃蒸菜吗?”
洛阳必然是有蒸菜的,不过相较饭店里的正规军,各家厨房出品的蒸菜总是野味十足,且多在春季出现在餐桌上。幼时的扫帚苗、柳树芽、榆钱等裹上面粉,或被做成榆钱窝窝头,或被做成蒸扫帚苗、蒸柳树芽。一些野外生长的林木,甚至可实现全身食用。
其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种被称为“构树”的苗木,它在不少城市被用作行道树,一些地方还会用嫩叶喂养家畜。
而在洛阳,母亲每到春季就会用构树叶做绿面条,具体做法是将构树叶过热水后榨成汁,再和在面粉里做成手擀面。原本白色的面粉经构树叶浸染,变成绿油油的面条,口感似乎也更筋道。
父亲尤爱这一口,而我们这些小辈却更喜欢蒸构树穗:只需将穗子洗净裹上面粉,再上笼蒸熟后,把调配好的料汁浇在上边。入口咀嚼,蒜泥的浓香、辣椒油的辛香及醋汁的酸爽瞬间便可霸占味蕾,混合出独一无二的滋味。
所有野菜中,野菊花是我们家上座率最高的,它一年可采摘两次,多于春天和秋末冬初出现在田垄上。烹饪时,可以在蒸熟放凉后,于热油里加入蒜苗、大蒜等辛辣刺激的配菜,炒成热菜;也可以直接过热水后,加入鸡蛋、肉末做成饺子或包子的馅料。
与一般家常饺子相比,用野菊花苗做成的食物,总是自带一股菊花的馨香以及淡淡的药材苦,因此,母亲总会说:“吃蒸菊花就是吃春,吃完春就不会生病了。”
与菊花一样被赋予养生意义的,河南还有许多其他品类的野菜,比如茵陈、柳树穗、洋槐花等,甚至是长在路边的鬼针草也被视为有清热败火的奇效,因此,也有人将茵陈、蒲公英等晒干后泡茶饮用。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可食用野菜虽多,但经验不足者却有可能因为误食形似者,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像马齿苋和漆泽,乍看外观上并无明显不同,但前者可以利胆,后者却有可能使人腹泻呕吐。
我小时候到田里挖野菜时,经常弄混“毛妮菜”及其赝品,两者浑身都毛茸茸的,开蓝色或粉色的小花,但形近者味道发涩,与“正牌”天差地别。
好在,我虽不止一次采错野菜,母亲却从未苛责,只当是累积经验了。
一碗蒸菜,历时千年
离开河南到北京工作后,寻找野菜仍是春天户外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不过,有家乡味道的野菜难寻,当地人食用的野菜也多有出其不意之处,比如苦牒子、泥胡菜等都是后来才认得的。
即使偶尔碰见野菊花、构树穗,也多是在公园里,往往被视作野草,或与其他种植的花卉一起享受人工浇水、打药等服务。这类植物长出的叶子往往不可食用,且口感欠佳。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2024年秋季众人爬山时,难得在几株柿子树旁看到了几株金黄的野生菊花。细小的花瓣藏在已现颓败之色的鬼针草里,竟也出奇鲜艳。
将根部嫩芽细细采摘下来,装到口袋里,我几乎一路都在想该怎么吃这些难得的美味。但没想到一路仔细呵护的菊花苗奇苦无比、难以下咽,而这足以让在外漂泊的人心碎了。
这件恍惚想起来的小事,让我忆起了今年网上有关蒸野菜的一则新闻:一位外地游客在河南购买了一份蒸构树穗,食用后就因过敏被送医就诊,原定的行程也只能草草结束。
这两件事让人不由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神奇之处——野菜也有地域限制,有些能蒸的野菜,换个地方便只能换种吃法,或选择放弃食用了。
我曾问过母亲:“为何每年都要蒸野菜?”母亲却同我讲起了她10岁左右发生的一件事。
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前期,不少家庭的生活水平都十分低下,甚至是食用油都成了难得之物,人们日常也多以水煮菜果腹。
在这种情况下,姥姥到地里采了许多苍耳子,并用之榨了一小壶油。母亲告诉我,榨出来的苍耳子油如香油一样醇香,却具有毒性,她和家人吃完不久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有的上吐下泻,有的已经昏迷不醒。
类似的场景,曾多次在河南这片土地上出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大约是1942年前后,河南发生饥荒,人们被迫只能食用野菜、树皮果腹。由于油、盐短缺,炸或炒更是难以实现,蒸煮自然成了烹饪食物最易实现的方法。也正是一代又一代河南人通过不断试错,筛选出了那些口感好、可食用的“野草”。
每年春季,河南的土地上长满了挖野菜的人,只不过如今人们不再是为果腹弯腰。蒸春菜既已形成饮食习惯,也是为了养生。
少油、少盐的烹饪方法和自然生长的野菜,正符合年轻人对于有机饮食的定义。况且在河南的野菜食谱中,有不少中药材的身影——茵陈、构树子、蒲公英、灰灰菜等田间地头常见的野菜——都被中医认为具有防治中暑、感冒,以及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功能。
在历史上,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都曾多次到河南行医问诊、采药制药,汇编当地人的采食经验。河南禹州至今还有“药不到禹州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的说法。可以说,正是千年的生存智慧,谱就了河南的饮食文化。
如今又到春季,河南的大街小巷里想必已经处处蒸菜香,只等待食客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