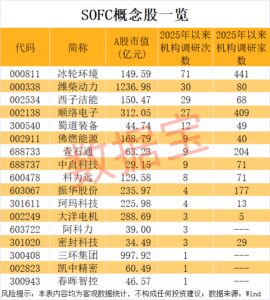向世界开源中国技术
【来源:虎嗅网】
让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明清时资本主义的萌芽。
我们先来看一本书——《天工开物》,此书是萌芽的文献典范,作者宋应星则是“江南道路”上“劳动者与思想者、工匠与艺术家”相结合的代表人物。他从江西出发,遍访江南农田、作坊、矿井,走访农人、瓷工、船匠等,身临其境,验证工艺细节,以“田野调查”式的科研方法,使其思想根植于劳动者的实践经验,把泰州学派的一句话——“百姓日用即道”写成了一本书。
此书载有18个行业、130余项技术,农业有“乃粒”“粹精”等,手工业有“陶埏”“杀青”等,冶金有“五金”“冶铸”等,以左图右史的呈现方式,如《花机图》《榨油图》等,我们不但可见其技术细节,亦能感受其人文温度。
他在记录技术时,常融入对工艺美学的品评,例如,描述青花瓷“白地青花,成窑为最”,评宣德炉“妙在宝色内涵”,《丹青》详述颜料调配“五色相宣”,将技术升华为艺术。
他本是诗人,能将科学叙事以诗性表达,其叙述既具有“格致”的精确性,还充满了诗意,其描述稻花曰“芳气袭人”,形容蔗糖结晶曰“如霜如冰”,诗性与理性交融,表达了一种士人视角的平民情怀,突破了“经史子集”的旧文体阈界。
他还是个画家,书中有123幅木刻版画插图,如《耕田图》《造纸图》等,以其写实画作,再现劳动场景,其人物动态鲜活,呼之欲出,工具结构精准,应能复制。其插图不仅是生产记录和技术图解,更是明代田野街头以及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卷,与徐渭大写意绘画共同构成江南艺术的多元景观。
他在思想上与泰州学派产生了共鸣——“贵五谷而贱金玉”,对工商“末业”价值重估,其平民立场,与之契合,其思想路线,也已转向“物质生产”,而非投入“心性修养”,以其生产实践为工商正名提供实证基础,还将“百姓日用”的“百工技艺”尊称为“圣人之作”,使之等同于士人学问——“内圣外王”。
当李贽还在对“私欲”作“童心说”的辩护时,其《舟车》篇,已详述商船运输的货物种类及其贸易路线,显示商人通过跨区域贸易积累财富的方式以及资本运作的“江南道路”,形成“以末致财”——工商、“以本守之”——耕读的资本循环。
“开物”的斯密型成长
在这样的循环里,有一种动力,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叫做“斯密动力”,即通过分工深化与市场扩张互动来推动经济增长。分工提升效率,但受限于市场,惟有市场扩大,分工才能精细化,如此循环不已,盖由“斯密动力”所致。
以此“动力”带来经济增长,即为“斯密型成长”,彭慕兰认为,1800年前的江南和英国,都处于“斯密型成长”阶段,但欧洲因殖民地资源与机械技术突破转向“库兹涅茨型增长”。
两宋时,以运河与海关——市舶司,枢纽国内外贸易,以分工形成专业化生产,并推动专业性市场扩张,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密型成长”,然其亦有不足,不足在于缺少技术突破。
黄宗智指出,明清江南“过密化增长”,便是“斯密型成长”的极限,由此产生了“内卷”,虽然国民经济的总量在增长,但其人均收入已然停滞,如此“成长”,核心机制虽为市场驱动,但增长方式仍属劳动密集型,人口过密,资源超载,市场整合与分工虽可在资源总量不变时优化配置效率,延缓或局部规避马尔萨斯危机,一如宋代中国、近代荷兰,但终究还是难逃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最终走向用战争来解决周期性饥荒的人口问题。
“斯密型成长”的局限就在于此,增长依赖市场范围扩大,但缺乏技术突破,易受资源与环境约束,若无技术革命,最终仍受制于生态上限,如清代江南人口过剩导致生态崩溃。
在《天工开物》中,我们似乎读出了一点“斯密型成长”的味道,书里的那些技术,不知传了多少代,无原创者,无发明人,只有师傅带徒弟,一代代,被市场驱动,参与分工。
他们是工匠,自由的工匠,奔波于田野街头,劳作于市井坊间,作者看他们,用了泰州学派的眼光,看得“满街都是圣人”,作者走到他们中间去,用文笔和画笔,双管齐下,记录了他们的工作。他看到的,已非自然原样,而是人为,故其书名,未尊自然而称“天道成物”,乃以人艺,因手工,名之曰“天工开物”。
这与机械制造走的不是一路,但它却是对“自由工匠”的极誉,若一手艺人,被人冠以“天工开物”,试问,还有比这更高的评语吗?中国极品丝瓷茶,无一不是“天工”之物。
中国传统中有一些伟大的艺术,纯然发乎信仰,成于无名氏之手,如敦煌壁画,同样,也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因无专利制度留名,“百姓日用而不知”,被淹没于历史的风尘中。
人似浪花,没于川流,故曰“逝者如斯”,然而技术传世,泽被民生,化为“百姓日用”,当为百代福音,焉能失传?故作者仆仆于山间田野,匆匆于市井街头,访问那些劳作者——“满街的圣人”,也就是那些“自由的工匠”们,他们究竟为何人?他们是在市场经济中自食其力的自由人,受雇于资本,但不失其身份。
《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制造业场景里的雇佣关系、分工模式及市场导向的生产活动,揭示了“自由工匠”群体的存在,书中描述的“机工”“矿工”“染匠”等角色,已具备了自由劳动者的核心特征——人身自由、技能自主、按劳取酬。
他们是“斯密动力”的源泉,是“斯密型成长”在江南自发的东方类型。仅以几行字迹,我们亦可略见其一斑。
书中《乃服》篇,提到了江南织造业的“机户—机工”模式——“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机户拥有织机等生产资料,通过支付货币工资雇佣机工进行生产,机工则自由受雇,按日或按件计酬。这种“出资”与“出力”的分离,突破了传统家庭作坊的依附关系,劳动者可自由选择雇主,体现了自由工匠的特征。
《五金》《冶铸》等篇则记载了矿业与冶铸业的雇佣关系,金属冶炼需“合众力而为之”,如炼铁工场中,工人分工明确,有“煽风者”“辨矿者”“锻工”等角色,工人通过出卖劳力获取货币报酬,以此形成非人身依附的雇佣关系。
其劳动特征,表现为流动性强与技能专业化。
书中记录的工匠,多有专门技艺,如景德镇瓷匠精于拉坯、雕刻,苏州织工擅长提花等,他们凭借技能在不同作坊间流动,不受地域或行会的限制,显示了自由工匠的职业属性。
他们按劳取酬,经济自主,书中多次提到,工匠“计日授值”或“按件付酬”,说明工资是其主要的生活来源。
这种经济独立性使其摆脱了封建劳役束缚,以此形成了一个由商品经济提供的“自由工匠”群体的社会背景。
书中记载了苏州、杭州等市镇,因丝绸、棉布贸易,催生了对“自由工匠”的需求,适其时,土地兼并推动生产力转移,《乃粒》篇提到,江南失地农民纷纷转向手工业谋生,成为“自由工匠”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来源。
这种转化,化为“半工半农”或专职匠人,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新质生产力的缩影。
作为新质生产力,“自由工匠”与传统匠人有别,其别在于弱化了人身依附。传统匠人隶属官坊,世袭匠籍,而《天工开物》中的工匠,多为“募工”,可自择雇主,能自我议价,其生产不由官府指派,非以贵族定制,乃以市场论价,劳资关系市场化。
故其收入,靠市场流通,景德镇制瓷,“一器工累数十万,一坯成必先利市”,这就要求形成专业化的市镇,但这还不够,还要能跨区域贸易,通过江河与海运,而货卖天下。
这些都是“斯密型成长”的历史场景,自由的工匠们当然也就成为被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了。
但他们身上似乎还缺了一样东西,那是什么东西?一种具有创新机制的东西,亦即革命性的“技术突破”。
“开物”与物理的分野
工业革命有两大动力,一为“市场驱动”,也就是“斯密动力”,一为“技术突破”,或曰“瓦特动力”,来自“创新机制”,以之衡量中国,江南不乏由“市场驱动”形成的“斯密动力”,但未有基于“创新机制”的“瓦特动力”,何以如此?
盖因中国工匠,以师傅带徒弟著称,重在师承,形成了一套“师承机制”,而非“创新机制”,故其技术发展,是在师承的基础上渐进,继以改良,而非突破“师范”搞创新。
以此来看《天工开物》,我们所见到的,便都是些技术传承性的总结,未见有技术创新的著录,其技术表现,停留于“斯密型成长”——技术革新与分工协作阶段,书中提到了提花机、水转大纺车等机械化工具的应用,通过机械传动提升生产效率,《乃服》篇描述了提花机需工匠分工操作“花楼”与“织机”,类似于工厂流水线雏形,体现了分工精细化与技术标准化的“法式”。
然其局限也很明显,其技术实录止于经验层面,堪称“实学”,追求经世致用,但未达科学原理,其《佳兵》篇之于火器制造,虽言及火药配方,却未深究其燃烧的化学机制。
故其目光聚焦于生产实践,而非科学实验,虽被称为“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然其于近代科学的实验性与数学化多有缺憾,其于西学,未能会通,称之为“科技的百科全书”,名实难副,若改称为“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则名副其实。
李约瑟以“中国的狄德罗”来对标宋应星,得其貌似,神则各异,本来各自殊途,各有千秋,何必硬要凑合?
当其时也,宋应星若能于“中西会通”方面,上承徐光启《几何原本》,旁及方以智《物理小识》,或能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从实用性的生产技术的局域里独立出来,开创中国科技的新局面,但他没走上这一路,不但从未涉猎《几何原本》,而且未读《物理小识》,因而错过了一次有可能在中国发生的科技革命。
《天工开物》于明崇祯十年(1637)刊刻,一经问世就被人收藏和引用。在宁波范氏天一阁内,便藏有此书的初刻本,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一书中,引用了它的有关论述。
比较一下这两本书,我们可见明清之际知识界的分野。先来看书名,这两本书都有一“物”,宋应星以“天工”为技术,从事生产活动,便是“开物”,而方以智则进了一步,要去认识“物”的原理——“物理”,若使之结合,会如何呢?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宋应星先行“开物”,再像方以智那样究以“物理”,将书名改为《天工开物及其原理》,那么实用性的生产技术就会向着理论化的科学技术转型了吧?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例如《佳兵》篇“开物”,就曾言及火器制造及火药配方,若它再加上《物理小识》的愿景,往中西会通处去深究一下造火器的动力学原理以及火药配方的化学反应机制,那么它就有可能发生从实学向科学的转变,从基于“百姓日用”的生产场景向追求科学原理的实验场景转变。
但转变并未发生,此虽由知识界的学术分野所致,但更由国运逆转使然,知识分歧的鸿沟,尚能以共识填补,事实上,方以智正在这么做,他比宋应星年轻24岁,这事,也应当由他来做,他在《物理小识》中,已经这么做了,但只是个开端。
这两本书,如今来看,本来就有互补性。
《天工开物》以著录生产技术见长,系统记录了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实践,如《乃粒》(粮食生产)《陶埏》(陶瓷制作)《舟车》(交通工具)等,《物理小识》则以理论探索为特色,探讨自然现象的科学原理,如《天类》(天文气象)《人身类》(生理医学)《金石类》(矿物性质)等,兼具理论思辨与实验观察。
在知识来源上,《天工开物》基于本土经验,聆听工匠口述,亲往实地观察,《物理小识》则融合中国阴阳五行自然观与西方科学地圆说、光学理论等,以“光肥影瘦”,解释小孔成像,用“气”的聚散,解释物质变化,建构其综合性知识体系。
两者共同构成明末科学“经验—思辨”的双翼,相比之下,《天工开物》更贴近社会经济需求,直接服务于生产实践;《物理小识》则偏向知识精英的哲学探索,与民生关联较弱。
此二者,一同反映中国近代科学转型的困境:技术经验未升华为理论科学,哲学思辨缺乏数学化与实验化系统。
若将《天工开物》的实证精神与《物理小识》的理论追求结合起来,或可趋于近代科学,但其受制于明清耕读社会结构,受制于明清知识界的学术分野,这使得“可能”终未实现。
但是,若能假以时日,假以岁月静好,那么困境虽在,尚能克服,然于国难时,覆巢下完卵尤难,科运怎兴?明清易代,此二人者,皆被卷入政治漩涡,《天工开物》因以“北虏”称满清,故有清一代,成为禁书,在中国失传三百年。
“开物”通往知识共享
两书命运,宛如一部中国科技史的悲情缩影,辉煌的技术如白日依山、黄河入海,却与科学革命失之交臂。
17世纪末,《天工开物》通过中国商船传入日本长崎,书中所言冶铸、纺织、农业等技术,推动了日本技术革新,其中,“沉铅结银法”“铜合金制法”被日本矿山业广泛采用,提花机的设计原理也启发了日本纺织业的技术改良,推动了江户时代丝织品的商品化生产,而播种机与高效犁具则被日本农民引入。
于是,日本出现了“开物之学”,以技术革新“富国济民”,或曰“夫开物者,乃经营国土,开发物产,富饶宇内,养育万民之业”,此非明治维新“殖产兴业”政策之先声乎?或曰其为“东亚技术书的巅峰”,其内容远超欧洲同期同类著作。1771年,日本大阪首次刊行《天工开物》,这是该书首个海外版本。此后多次再版,至20世纪50年代京都大学推出日文全译本后,袖珍本累计重印20余次,成为日本科技教育的经典读本。
《物理小识》传入,适逢日本兰学兴起,故以其原有的“中西会通”的成果来引领日本兰学,予以西学启蒙。
然其虽未如《天工开物》般直接推动技术变革,但其核心术语“物理”,却在日本经历了“侨词来归”的跨文化旅程,其以“质测”——实证研究与“通几”——哲学思辨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引导着日本兰学步入其“中西会通”的研究路径。
方以智曾以西方解剖学,修正李时珍《本草纲目》,开示其“中西会通”的思路,杉田玄白开窍,沿此一路,译《解体新书》,既取西医的解剖图谱,又据汉医经典,兰学由此开山。
那时的江户学者们,还通过此书理解了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并使之与荷兰技术结合改良他们的观测工具。
兰学初兴,依赖汉学提撕,《物理小识》一书,因此也就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科学的一条纽带,其知识流动,形成了一道跨文化的长虹,打了一个枢纽着东洋和西洋词语的“中国结”。
《物理小识》提供的不仅是术语的借用,还提供了一片文化交流的天空,让词语如星辰般在其中闪烁,以“物理”的“侨词来归”,开了一个东亚科学从传统向近代跃迁的好头。
“物理”源自中文语境——“万物之理”,“小识”一下,聚焦于天文、地理、医药领域,兰学以之对译西学“physics”,予以“物理学”含义回流中国,可见其“侨词”路径。
可惜的是,这两本书未能于中国本土相结合,却来到日本,反而被日本人结合,形成了东亚科技的一个雏形,也可以说是科学技术的一个东方主义的模本。这本应出现在中国,然而,易代之际,国运不济,书亦流离,被日本人捡漏,如获至宝。
这就使得日本人后发先至,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当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一同来临时,日本人已做好了《物理小识》的思想性与《天工开物》的技术性结合的科技准备,正是有了这么个准备的基础,日本人在科技的近代化方面,才能先行一步。
这一步迈出去,就走向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走出了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而这两本书在中国的命运,一本早已失传,一本传播有限,《物理小识》虽未如《天工开物》被禁毁,但它在中国的影响,则可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受众范围很小。
康熙三年(1664),该书首次刊刻,乾隆时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中,过了二百多年,到光绪十年(1884),再次刊行,试图扩大其流传范围,回应晚清西学思潮。但为时已晚,“中西会通”早已过了晚明阶段,其时,西学压倒中学,“西洋潮”之来,亦不必由“中国风”引领,说到底,就一句话:连“物理学”都来了,还要《物理小识》干什么?只能在思想史上给它留个角落。
而《天工开物》则一改其在中国失传的命运,在工业革命期间,它在欧洲传播开来,一传再传,影响越来越大。
从18世纪至20世纪,该书的不同刻本与印本,陆续在欧美各国的图书馆里出现,18世纪,巴黎皇家文库就藏有明刻本,1830年,法国汉学家儒莲用法文,首次西译了书中《丹青》一章有关“银朱”的部分,1832年,改以英文转译,发表于《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上,1833年,又以法文翻译了“制墨”部分,刊载于法国权威杂志《化学年鉴》和《科学院院报》,接着,他又把这一部分的法文译本转译为英文和德文,喊醒了欧洲学术界。
1837年,儒莲又将书中有关蚕桑部分及《授时通考·蚕桑门》译为法文,出版了法译本,而且取了个中文名,曰《桑蚕辑要》,将其所载有关植桑、养蚕、防治蚕病的方法,应用于当时突如其来且不知所措的蚕病的防治,挽救了欧洲蚕丝业,故其于欧洲深入传播,有欧洲学者认为“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
后来,达尔文读了这篇译文,在其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以译文所载的养蚕技术,言其人工选择及其变异。
1840年,儒莲又将书中以树皮、竹纤维替代破布造纸的技术,译介至欧洲,法、英、德等国据以改良工艺,缓解了欧洲因原料短缺引发的造纸危机,推动了造纸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书中记录的播种器具和高效犁具的制作方法,也推动了欧洲农具改良,提升了耕作效率。在冶铸技术方面,书中言及灌钢法、失蜡铸造法,填补了欧洲金属冶炼领域的空白,尤其“活塞式封箱”鼓风技术,其应用,也比欧洲早了数百年,还有书中记载的纺织机——“花机”,比珍妮纺纱机早近200年,冶铁技术中的“群炉汇流法”,则为欧洲工业革命提供了技术借鉴。
尽管《天工开物》“向世界开源了中国技术”,成为了“连接古代经验科学与近代实验科学的桥梁”以及全球化早期样式的“知识共享”,但它却未能“技术突破”成为工业革命的原典,其根源在于“创新机制”即“产学研一体化”缺乏,然此“机制”,瓦特竟在无意间得之,可以说瓦特才是“工业革命的幸运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25年4月21日第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