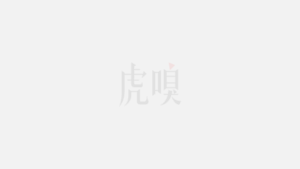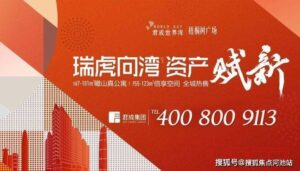巴西取代美国成最大供应国,中国大豆够用了吗?
【来源:虎嗅网】
中美经贸摩擦,再次让大豆供需平衡话题持续升温。
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中国每年需进口大豆以满足国内需求。但随着关税战导致贸易局势紧张,中国大豆产业链安全备受关注。这主要源于中国的大豆自给率已不足20%。国际地缘冲突、航运通道受阻等,大量突发因素都可能影响大豆供应稳定。
除波音飞机,美国大豆对中国出口,也曾是缓解其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据海关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大豆出口3285万吨,占当年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57%、中国大豆进口量的34%;出口额140亿美元,占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额的58%和对华货物出口总额的10%。
由于数量庞大,2018年大豆已被中国作为反制美国的主要手段之一。为满足大豆需求,中国开始加紧布局进口多元化及国产增量的双线方案。前者的标志,是来自巴西的大豆进口量不断提升,并延伸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贸易合作。
与之相应的,为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近年来也在不断提升大豆的自给率。通过实施大豆产能提升工程,国产大豆产量连续三年超过2000万吨。这提升了中国大豆产量在全球大豆总产量中的比重,也增强了中国在国际大豆贸易中的议价能力。但为缓解大豆供需平衡挑战,国产大豆在量质等多个方面,为什么仍被业内普遍认为有较大空间?
首先,中国的国产大豆生产结构,仍然存在“食用大豆有余、油用大豆短缺”这一结构性挑战。
从大类来看,大豆用途虽多,但主要被分为食用大豆和油用大豆。作为大豆的起源地,中国的非转基因国产大豆的蛋白含量高但含油量低,因此主要用来加工豆腐、豆皮等传统食品。
从数字来看,作为大豆消费大国,中国的年需求量约1.1亿吨左右,其中食用大豆年需求总量(含蛋白企业)约为1450万至1500万吨;油脂压榨转化的大豆,则需要进口超过9000万吨左右。
为巩固大豆扩种成果,近年来国家在内蒙古及东北三省持续推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促进大豆产销衔接,从而稳定大豆生产。随着国产大豆产量连年增加,国产食用大豆开始出现过剩现象,但油用大豆短缺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与进口以转基因品种为主的大豆相比,国产大豆的出油率相对较低(低于进口大豆3至4个百分点)带来的较高成本,使得其往往缺乏价格竞争优势。压榨成本和种植成本不协调,使得豆农和压榨企业较为依赖政策补贴等支撑。
此外,随着国内消费水平提高,居民对肉蛋奶需求攀升仍将维持一段时期,对饲料蛋白的需求也将不断上涨。而进口大豆除榨油,主要需求是用剩下的豆粕作为畜禽水产业的蛋白饲料。作为养殖大国和饲料消费大国,中国在这一方面需求和生产成本都相对较高。
整体而言,中国的食用大豆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常年消费量在1400万吨至1600万吨之间,但榨油及饲料大豆仍较为短缺,主要依赖进口。
在中国大豆进口量持续攀升的近20年间,类似话题已被业内多次讨论。由此引发的产业链后续一系列难题,其实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例如,与进口大豆相比,种植结构与产业需求存在不匹配,往往容易形成国产大豆销售不畅、进口大豆量居高不下。这其实也被普遍认为会导致国产大豆销售困难,从而限制产能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其次,随着居民食物消费保持升级,中国的食物供求仍会维持一段时期紧平衡局面。虽近年来持续增加国产大豆产能,但因国内“地少人多”的资源禀赋,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的平衡发展,也被普遍认为不可偏废。
中国的农业生产资源总量较大,但人均占有量低,资源约束明显。比如,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复种指数已从2001年的1.22上升至超过1.33,部分地区甚至高达3.00以上。
耕地高强度、超负荷利用,会造成质量状况堪忧、基础地力下降;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其实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国约50%的国土面积年降雨量低于400毫米,且气象干旱在华北、西北、黄淮等区域常年多发。
这些因素,其实都会拉低国产大豆的产量上限。也决定了大豆并非中国的比较优势产品,通过参与国际贸易满足国内需求,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农业发展现实的必然。
对于大豆这种“土地密集型”产品,中国农业贸易促进中心此前曾对此进行过测算:2017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1.2亿亩,产量1528万吨,进口量则达到9552.6万吨。如按照国内大豆单产每亩123.5千克来计算,进口9552.6万吨大豆相当于7.7亿亩耕地播种面积的产出。当年中国共有耕地面积20.23亿亩,大豆由国内自给,相当于要用44%的耕地面积种大豆,小麦和水稻等口粮的绝对安全,则必然会受到威胁。
与之相应的,则是一个所谓虚拟耕地的概念,其指粮食生产过程中占用的耕地资源,即将地区间进行的粮食交易看作是相应的耕地交易。究其意义,通过进口能在中国大豆及其他油料、猪肉、牛肉、植物油、粮食及奶制品供给安全方面起重要保障作用。
自2009年至今,中国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作为中国当前最大的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进口来源国,2024年中国对巴西进口量为4494.5万公顷,占中国虚拟耕地资源进口总量48.6%。其中,中国对巴西大豆进口处于第一位(7465万吨,占大豆进口比例71.1%)。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巴西进口量处于第一位的,还包括玉米、冻牛肉、棉花和禽肉等。
同样作为中国油料、油脂重要进口来源国的,还包括俄罗斯。从2015年起,中国自俄罗斯的大宗农产品净进口量开始大幅增加。2024年自俄罗斯的虚拟耕地资源进口量处于第七位,也已占中国虚拟耕地资源进口总量的3.1%。
第三,为更好平衡国产及进口大豆关系,中国正通过政策调整等方式,积极构建“食用大豆功能化、油用大豆高效化”双轨发展体系,即在支持发展国产食用大豆产业同时,发展国产油用大豆产业,破解结构性过剩问题。
从2022年起,中国开始实施大豆扩种计划,增产效果较为明显。以当年数据为例:国产大豆产量突破2000万吨,消费量约为1500万吨,开始出现仅靠食用无法完全消化的挑战。如前所述,虽然国产大豆也可进行压榨,但因出油率相对较低,压榨企业的积极性不高。
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其实是以优质的国产食用大豆及其制品替代部分动物性食品的消费,如此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豆对外依存度。但为解决前述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业界的建议也包括政策端、生产端、收储端、加工端、消费端等多个方面。
例如在政策端,就有部分专家学者建议,中国应构建精准调控机制,实现对食用大豆和油用大豆的差异化补贴。引导农民种植高产油用大豆,提高油用大豆自给率。此外,也可支持油脂加工企业采购国产油用大豆,通过工艺创新提高出油率。
近年来的中央及地方的各项相关涉农政策,其实已在向此方面进行转变。以中国大豆主产区、产量规模稳居全国首位的黑龙江为例:2023年时,该省已开始对高油高产大豆实施奖补政策,经审定“黑农531”“东农豆110”“合农80”等20个含油率≥21.5%的优良品种,可获得高油专项补贴。
在此基础上,再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例,也开始明确提出“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种”等相关内容。2025年,中央财政也将重点实施多项农业补贴,涵盖耕地保护、大豆玉米种植等核心领域。其中,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与稻谷补贴形成“主粮保障组合拳”。
与前述支持与巩固政策进行调整有关的背景之一,是2024年国产大豆产量为413.0亿斤(折合2065万吨),同比上年减少了3.9亿斤。同年,大豆播种面积为1.55亿亩,较上年减少了223.2万亩。而大豆单产则为133.3公斤/亩,增加0.7公斤。
在政策发展方面,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还包括4月7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在贸易战背景下,中国近年来不断采取各项措施,分散对单一市场农产品需求过大风险。为充分挖掘国内农业生产潜力,这一规划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多项新措施。
例如,为进一步通过增加国内供应降低大豆等进口需求,其也在重点针对粮食作物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薯类杂粮。挖掘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生产潜力,拓展油茶、动物油脂等油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作者:焦建,编辑:苏琦,责编:要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