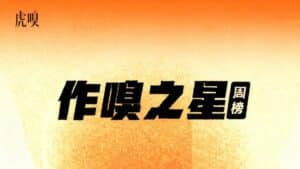人造子宫,对女性是解放还是压迫?
【来源:虎嗅网】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造子宫”这一原本只存在于科幻小说的产物,面世已是指日可待。但技术逐步成熟的同时,社会层面尚有大量需解决的法律和伦理问题。新技术将要进入的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具有种种不平等和偏见的社会。不尊重生育者自主权的群体可能会利用这些技术强化控制或加深阶级、种族分歧,这也促使我们思考这一技术突破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加拿大法律学者克莱尔·霍恩在《夏娃:关于生育自由的未来》一书中回顾了从十九世纪成为游乐场时尚的初代育儿孵化器到当今的尖端科学突破的漫长历程,深入探讨了这个时代最具挑战性的一些问题。
比如,人造子宫对于女性来说到底是解放的福音还是新的压迫?我们如何保护生殖和堕胎权利?曾在“优生学”名义下出现的历史悲剧会再现吗?人造子宫技术下诞生的孩子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标签去面对父母?这些伦理上的模糊地带和未知领域,都亟待填充和赋予新的伦理程序。
在这个充满质疑和魅力的现代生育故事中,本书以令人大开眼界、清晰明了的方式探讨了这一切对人类的未来的意义,也再次提醒我们,只有在有益于社会文明发展的伦理规范限制之下,技术的发展才可能真正造福人类。
与大家分享本书译者周悟拿的译后记。
《夏娃:关于生育自由的未来》的作者克莱尔·霍恩(Claire Horn)长期从事人造子宫和生育伦理方面的研究。她曾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求学,主要关注体外人工培育如何影响西方国家关于堕胎、父母身份和代孕等事宜的法律框架这一话题。
从作者优秀的学术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学科的跨界融合:生物学、伦理学、法学。我在翻译过程中也深深体会到作者的功力。她能在新技术对传统伦理发起挑战时迅速进行法律和伦理方面的联想,而且对于人造子宫、新生儿科技、堕胎相关法律的发展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历史梳理,处处体现出作为社科学者的严谨和审慎。
这本书最早在2023年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极快的速度引进,我在英文版刚刚问世时就迅速开启了翻译工作。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关注人造子宫技术的新进展。
的确,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不断向前推进。而且,截至目前,最新进展就发生在中国:2024年7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完成世界首例“去ECMO化人造子宫”动物实验,胎羊在脱离母体且无需ECMO(体外膜肺氧合)支持的情况下存活了90分钟。
新闻发布之后,机器孕育生命、男性“怀孕”等科幻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情节,又一次进入人们的日常讨论。
技术发展之后,如何定义“母亲”?
如若人造子宫技术发展成熟,“生育”这件事就不再和“母亲身体”绑定在一起。截至目前,我们所有人都是由自己的“母亲”孕育而成,都在另一个人类的身体之中经历怀胎十月,才最后呱呱坠地。如果科技进一步发展,这将不再是任何人诞生的必经之路,机器可能完全替代母亲的角色。
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孵化中心”对人类胚胎进行批量生产,还会通过化学和物理手段来调整胚胎未来的智力和体格,以确保他们符合预设的社会角色。20世纪30年代,第一款口服避孕药被研发出来,并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批,而赫胥黎创作《美丽新世界》的灵感也正是来自这项研究成果。不过,赫胥黎依然只是在想象中描绘那个冰冷又没有人情味的世界,现在的新兴技术似乎让这一切真的可能成为现实。
克莱尔·霍恩结合“优生学”的历史,把人类当下所经历的一切和赫胥黎塑造的未来世界进行了比照。比如,优生学观念的影响依然持续至今——在北美洲发达国家的医院和诊所,非裔和原住民女性及其婴儿依然面临种族歧视带来的危险,北美的医疗体系仍是围绕白种人母亲和婴儿建立的。在科技发展之后,若人类对于生育有了进一步的可掌控空间,是否真的会出现《美丽新世界》的场景?
人造子宫,对女性是解放还是压迫?
在现代社会,许多人支持体外人工培育,因为他们认为这项技术能成为“解放”妇女的有力工具。的确,若有机器代劳,那么女性可以免受十月怀胎之苦,不必在妊娠期间忍受孕吐、夜尿频繁、水肿等问题,也不必在分娩中及以后面临阴道撕裂、子宫脱垂、产后尿失禁等风险。
对于本来就身患高血压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女性来说,人造子宫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孕期的不适,还能免除女性自身承受的健康风险。的确,女性在繁衍后代这件事情上本就承受了不均等的负担和风险,男性天生无需承受这一切。若这项技术成为现实,是否能真的实现对女性的解放?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作者从开头到结语都提到,她在撰写这本书时恰逢孕期。她在结语中详细写下了自己在怀孕过程中的感受。比如,她写下了孕期的各种不适如何像海浪一般一次次袭来,而她无处可躲;医生也不会给出任何缓解性的“治疗”,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怀孕期间“忍一忍”是正常的。但她也记录了自己在孕育孩子时的兴奋和快乐,当她感觉到宝宝在肚子里踢来踢去,她感觉这是人和人之间最为深刻的一种联结。
如果人造子宫技术真的问世,女性是否会被剥夺怀孕的“独特体验”?人们对于性别角色、母亲角色的认知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毫无疑问,传统家庭观念中“母亲怀胎”的核心概念将被动摇,这在文化层面必然引发颠覆性的讨论。
可想而知,当未来技术已经普及,若有女性不愿使用人造子宫,甚至可能被指责为“自私”。机器显然比人更可控,而人类在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意外,也有孕育者不控制饮食或生活方式进而危及胎儿健康的情况。因此,未来很可能会有人指责那些想要自己怀孕的母亲:为何不用人造子宫?为何要冒险来选择自然孕育?
作者也提到,如果这项技术真的诞生,那也是诞生于一个仍由父权制主导的世界。如果我们缺乏警惕,这项技术给女性带来的压迫则可能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渗透到方方面面:
女性的子宫若被视为无用,因而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否会进一步被边缘化?若是技术已可以替代女性的生育劳动,女性在生育方面的福利和关照是否会被消解?若是技术研发、决策层多为男性,女性是否会失去生育方式的选择权?若是人造子宫被设为强制使用的技术,是否部分女性将不能决定由自己来亲身孕育孩子?
除了性别平等的问题,作者指出,在西方社会也有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考虑。作者几次提到,从目前几个国家的研发情况来看,人造子宫的实验器材耗资甚高。可以想象的是,未来这项技术必定成本高昂,那是否会导致贫困女性被迫选择“传统生育”,而富人享有无痛的科技生育特权?
机器孕育的胎儿,享有怎样的伦理地位?
作者不仅关注技术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和角色,也非常关心胎儿的伦理地位——而这才是这项技术研发过程中最为弱势的群体。作者对婴儿保育箱的发展历史也进行了回顾,而我震惊于这个过程中被牺牲掉的婴儿竟是如此之多。1903年,纽约市康尼岛的月神公园出现了长期的“婴儿保育箱展览”。因为那时的早产儿存活概率很低,最后很多孩子会被交到自负的医生手中,接受实验性的治疗,整个过程还会成为公开展演的素材。
当时的人们竟是以一种看客心态在“观赏”这些岌岌可危的孩子。在针对早产儿的研究中,最初根本没有道德准则来加以约束:“婴儿成了展览的内容,众人就像赶集一样蜂拥观看。”
从被孕育开始,胎儿就无法自己选择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若是提早降生,这些早产儿可能会面临许多并发症,而且大部分无法存活,甚至还要沦为展品。
作者把当时的这种现象和美国的博览会风潮联系起来:在1893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和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都有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成为活生生的展品。只有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才会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因为这种凝视和被凝视的关系就是权力不平等的直接体现。
更有甚者,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历史上,非裔美国人以及土著居民都曾遭遇系统性的强制绝育。如果人造子宫的技术进一步发展成熟,人类的繁衍是否会被某些自视为上帝的人掌控?谁又能保障这些弱势群体胎儿的权益呢?
在体外人工培育技术之中,胎儿或婴儿将被置于怎样的伦理地位,目前还无从得知。人造子宫中的胚胎是否和人类母体内的胎儿享有相同的权利?会否被随意终止妊娠,或是随意用于实验?如果有的父母一开始选择了人造子宫,后来又半途放弃甚至逃之夭夭,这个孩子该由谁来抚养?国家福利体系是否有相关举措来为机器孕育出的孩子提供保障?还是说,他们会被彻底放弃?
同时,作者也结合许多研究结果讨论了健康风险的问题。若是长期脱离母体环境,对婴儿的心理和生理发育会存在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都尚不明确。对于最早使用这项技术的人群来说,风险都是无法预估的。
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当屏幕上能迅速弹出一行行充满情感和创意的回复,人们纷纷惊叹:人工智能的诞生就好比是科技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生命。甚至有人爱上了手机里的人工智能,认为世间最完美的伴侣莫过如此。科技的创造能力可谓一日更胜一日。
再说回人造子宫,若科技真的可以“造人”,对人类社会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应该如何重新定义“母职价值”,如何重新看待女性地位,如何在生育自由的未来保障人类的选择权,如何不让科技的“解放”变成新式压迫的借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人造子宫成为现实的未来,在技术的光辉背后,作者让我们看到另一层隐忧:如果生育变成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作业,如果女性的身体从被歌颂的“圣地”沦为被淘汰的“过时设备”,如果母亲和胎儿的天然联结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我们真的能抵达所谓的“生育自由”吗?我们正在搭建的未来世界是比《美丽新世界》更美好,还是更可怕呢?
此时此刻,没有谁能给出答案。
《夏娃》,(加)克莱尔·霍恩 著
周悟拿 译,2025年4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 (ID:non-fiction702),作者:周悟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