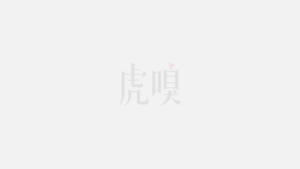任何人都不该暴露在太多恶意之下
【来源:虎嗅网】
2019年,作家蒋方舟开始了一场长达五年的互联网“脱退”实验。
所谓“脱退”,并非完全不上网,而是不再参加互联网场域里的公共生活。她清空微博账号,不追热点,不跟网友争执,偶尔在小红书发几张照片。为了增加深度交流,她把社交圈维持在最小范围。她减少微信聊天的频率,线下和朋友吃饭。
这场实验帮助她建立了写作纪律。每天上午10点到咖啡馆,写到晚上6点。随后回家做饭、运动、看电影。她找回了匀速的状态,结束十年以来的拖延症。
见到蒋方舟是2025年。此时,她已经写完新的长篇小说,也结束了这场实验。我们在咖啡馆见面,她在大厅直接选了一张空桌,顺手把墙上的讲座海报拍了下来。她讲话语速很猛,动作迅捷,像咖啡馆里上自习的大学生一样。让我想到朴树的歌词“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都卖掉”。
在她的描述中,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在小说即将写完的时候发生了,她感觉自己不再退缩、不再焦虑。她接纳了“逃避多年的软弱和耻感”,而“生命当中的黑暗正在撤退”。
这种感受,或许来源于她解决了一项人生课题。
九岁出书以后,她以“天才少女”的头衔出现在聚光灯下。每次听见周围大人介绍自己的成功履历,她体感不适,就像听见婚礼司仪讲“我们的新郎一表人才,我们的新娘美丽动人”。成年以后,相反的故事又出现了:辜负天赋,“天才陨落”。
她不得不学会防御,把公开发言当作“应战”,却被盔甲护住、压抑了本真。
舆论是一场巨大的棋局,她的人生课题则是:到底如何面对来自互联网的争议、恶评,又保证自己的表达是真诚的。最终,她找到的解决方式是——为自己写小说,并以此为锚点,重建生活。
以下是简单心理与蒋方舟的对话
流量曾经是我的敌人
简单心理:2019年,你发表“从互联网脱退”的演讲,你坦言自己极度地厌倦与畏惧,非常害怕说错话,害怕被讨厌。最近,你重新回到互联网。你说,自己“其实是一个需要被看到的人,无论激起的是哪种反应”。哪些事情改变了你的想法?
蒋方舟:这几年,我建立了自己生活的秩序,也突破了很大的瓶颈。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不再和广阔的外界交流的时候,我有一种溺水感,摸不清自己在哪儿,感觉自己在逐渐失重。
我想和外界交互,和什么东西撞上,无论是批评、认同还是讨论,这些反应回馈给我,自我才能变得坚实,也能有一个进步的方向。
从互联网脱退其实也出于自我保护。我意识到公共环境原本带给我很大成长。大家反弹给我什么样的反应,我再激发自己,这是很好的成长路径。
比如,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对我之前写作的批评,认为我太依赖文本,而不是生活,我认为这说的是对的,我的确接触文学先于生活,这干扰了我对生活那种原生的感受力。所以我知道了问题在哪里,这让我很开心。当然被看到之后也要适当保护自己,我在想怎么解决这事。
简单心理:如果再次看到不友好的评价,你的感受有什么变化?
蒋方舟:我想清楚了,别人的评价的确是身外之物。比如我再看到“天才少女”、“天才陨落”这样的说法,内心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觉得这只是一种最好理解的叙事。小时候看的各种文艺作品,都在塑造着我们对人和事的理解。“横空出世必伤仲永”、“痛苦涅槃后必东山再起”这种叙事里也夹杂着我们对自身的投射和期许。
问题在于,我不能让别人讲的故事指引我的人生,也不必自证、回击这种虚无缥缈的叙事本能。我得自己探索。想明白这些,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比较有底气和大家分享经验了。
简单心理:现在重新回到公共环境,回到公众人物的位置,你有哪些保护自己的方法?
蒋方舟:只要有一两个掌握快乐和平静的开关在自己手里,对我来说就够了。我之前看一篇文章,里面有个比喻:每个人的心灵都可以看作一个院子,院子里面有个木屋,屋里面还有卧室或者书房。很多朋友可以走进院子,木屋的钥匙交给几个特别在意的人,而最核心的书房、卧室,钥匙会交给两个人。
我很迷恋这个比喻,自己的生命秩序、情感秩序,确实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更加重视私人关系了,原来充满爱和包容的小环境,能够让我得到情感支持。太多东西是不可控的——流量、时代变化、工作机会,都由别人决定,但私人关系让我觉得,无论我做什么,都会被支持。
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私人生活不重要。我更会被表面的生活吸引,比如颁奖典礼哪个明星来了,参加企业家的晚宴,都是更光鲜的活动。现在我不愿出差,有出差的活动能推就推了。如果一周过去还没有好好聊天,就找我妈聊天或者约朋友聊一个下午。
简单心理:之前提到,“上热搜”可能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当一个人“上了一次热搜的时候,就想天天上热搜,写一次10万+的时候,就天天想有10万+”。回到互联网做内容,有哪些需要警惕的东西?
蒋方舟:我感觉流量是自己的一大敌人。流量有两个特点,一是量化的数据:今天点击5000,明天点击6000,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数字;二是流量的成功无法复制,流量之神的眷顾是随机的。如果我很看重流量,等于把自己的主动性上交给一个严苛的“他者”,感觉挺糟糕的。
在这种背景下,读者的评价包含着陷阱,最大的陷阱可能是赞美。这跟我性格的弱点有关,我从小就渴求赞美,容易被评价带着走。如果今天得到赞美,明天别人不赞美了,我就会患得患失。这种打击比一开始有人讨厌我更大,我会为了挽留别人的好感,做扭曲本意的事。
我做了一档自己的播客,不敢翻评论,每次都请同事帮忙收集反馈。主要怕自己潜移默化地迎合大家,看到好评,下次肯定还想听大家夸我。
过度自我保护,不是一个本真的状态
简单心理:公众人物难免有人黑。你曾主动找最恶毒的评价来看,想给自己的心灵“洗冷水澡”来使之更强大。这个方法实际效果如何?
蒋方舟:大概在退出网络之前,我会去一些问答网站,比如知乎,反复看那些让我伤心的评论。很多答案越刻薄就越高赞。我想,看多了内心就强大了。但不仅没有用,还会让我产生异化。
那段时间,无论对生活里还是网上的人,我都会预先竖起防备,更不要说毫无保留地对待对方。晚上在家里吃饭,我都很难相信家人是友好的。
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该暴露在太多恶意之下。就我的处境而言,只有在爱的注视和环绕下,一个人珍贵的敏感、脆弱才能被保护。
简单心理: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是一个人不害怕被黑就是“内核强大”,你怎么看?你尝试过修炼“内核”吗?
蒋方舟:“内核强大”绝对不属于人的天性,而是对异化的美化。被黑跟人生中必然会面对的悲伤、苦难不一样。那些东西,人必然会遇到,但陌生人毫无理由的恶意,不是必须处理的课题。
用这个东西衡量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是不合理的。一个人内心强大的标志可能是他如何应对必然经历的悲伤,比如亲人的离开、疾病、贫穷。一个人如果能从这些困境中走出来,甚至去书写、表达,确实是强大的。
有人认为你是公众人物,是“成功的人”,就必须得面对恶评——拿这份钱就要受罪。这也有道理,因为公众人物就是要接受评价。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悖于人的心灵结构。如果能对恶评泰然处之、甚至甘之如饴,无论是否公正,都觉着争议越大、收益越大,所谓“黑红也是红”的时候,人们的内心或许发生了异化。这样做,就失去了从人本身出发的判断标准。
这是不合理的,过度自我保护不是一个人本真的状态,所有人都喜欢坦诚的、真实的。我也觉得一个人只有足够坦诚,自我才能生长。
《凪的新生活》
简单心理:互联网的历史也不短,在你决定脱退之前,它曾经带给过你滋养的记忆吗?
蒋方舟:有的,是关于朋友的记忆。我刚玩微博是2012年,那会儿还在读大学,认识了一帮80末、90初的网友,后来大家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印象很深,我有次发了条深夜emo的微博,一个陌生网友评论“你就想要大家来夸夸你”。这人有点讽刺,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审慎地看了他所有微博,觉得他是个好人,也很聪明。
我就给他发私信,说认识一下。我看到他有条微博提问:怎么买到某本书?我说我有这本书,你要不要?最后我们约着周末到书店见面。
我最早认识李诞也是在微博,他当时还是个大学生,微博名叫“自扯自蛋”,我看他写的小句子有意思。那时候,我在课余时间常常约着微博上认识的人一起吃饭、听讲座。
简单心理:最近这些年,你还能在互联网交朋友,或者说收获相似的感受吗?
蒋方舟:现在很难了,很难复制那时候的安全感。那时候网友聚会的模式放到现在想想,有点不可思议。古早互联网,还没有“营销号”和“微博大V”的概念,就是分享生活。
当大家把流量看作财富,通过展现某种生活方式来接活很难从一个人的微博看到ta本真、直白的那一面。认识一个人,还要去辨别ta发微博的目的,怀疑是不是为了起号、立人设,是不是广告。
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现在不断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可能提前就想好被拍摄和记录下来是什么样子,提前做预设。这样做,有可能反而剥夺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力。
“我最懊悔的是,没有利用好我的痛苦”
简单心理:你在播客节目里提到,“在40岁之前,没有充分的把生存经验表达出来”,这件事是你最大的焦虑。为什么这件事对你来说如此重要?
蒋方舟:这两年,我重新看西尔维亚·普拉斯的《钟形罩》、邱妙津的《鳄鱼手记》,特别感触。这是20多岁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东西,30多岁的人就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了。
我很幸运自己能在20多岁的时候赶上经济上行时期,不会为下一顿饭焦虑。但相比于生存、攒钱来说,我现在对生命更真实的体验是时限。20多岁最纠结的那些问题,在32~35岁之间,我想明白了。比如两性关系,比如他人跟自我之间的关系。
好处是我不再为之痛苦,坏处是与痛苦随之而来的激情就也消失了。作为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人,试图重新为这些事感到痛苦,其实很可笑。这个事让我非常懊悔,我没有利用好我的痛苦。
简单心理: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实痛苦也是好事?你平时怎样处理自己的痛苦?
蒋方舟:对于创作者,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财富。如果没有利用好,它会从你的指尖流逝掉。如果我20多岁的时候,对自己的写作纪律严格,以及对自己的生命经验足够诚实,我也许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
我一直写日记,把自己的经验“用福尔马林泡着”。幸好还保留着生命当中的痕迹。可能我未必能再回到当时的感受,但至少留下这些东西以后,我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以后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时候,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情绪的时候,我会去翻检这些记忆。
简单心理:从去年下半年到年底,你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今年即将出版。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里面提到——当30岁到来,你忽然面对一种恐惧,怀疑自己是不是活错了,有种“巨大的失败感”。很多人迈入三十岁的时候都会体验到某种懊悔感。怎样去消化这种感受?
蒋方舟:可能我解决的方式就是——什么时候重建都来得及,重建的前提是承认人生当中的一些时刻是遗憾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
我现在就认清,20多岁的自己是不够好的。比如说在两性关系上,我20多岁迷恋被爱,现在觉得那时候虽然是真实的,但我现在不会这样。我20多岁的时候,工作纪律不好,有非常强的拖延症,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经历,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十几岁的时候进入到大众关注的场域,说了很多哗众取宠的话。我会因为自己作为年轻女性进入到男性的俱乐部,而觉得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为这种东西沾沾自喜。现在再看,那是不想继续再过的生活。
我要面对它是错的。我把它拆毁成废墟之后,也相信在任何时候重建都是来得及的。我确实花了两三年去建立工作纪律。
简单心理:你在其它公共发言里提到,这几年你终于接纳了“逃避多年的软弱和耻感”,而“生活当中的黑暗已经撤退”。这是怎样的心态变化?
蒋方舟:我去年写小说到后半段的时候,进入了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每天去咖啡厅工作,从上午10点到晚上6点,回家以后电脑都不开,开始运动、散步。
我从来没有不为自己正在写的东西焦虑过。原来,我做很多工作都是被推着走的。20多岁的时候,我写小说、出书是因为我需要一两年出一本书,这是我的工作。要出什么我也不太知道,想到什么我就去写。
我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不愿意回头看写的东西。现在我一遍一遍地改稿,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是我的作品,不只是我交的差。
进入了某种匀速的状态之后,我发现原来能把一件或许在能力之外的事情,给干成。现在我知道明天能继续,后天还能继续干,还能把它一直干到成为止,这个事儿我不会放弃。
我找回了童年的某种感受。小时候,我经常等爸妈下班带我出去洗澡、去公园散步。工作以后,工作和生活的分界常常变得模糊了。界限回来以后,我知道下班的时间就是属于自己的,一点焦虑和恐惧都没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