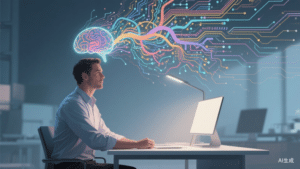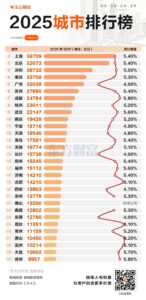历史不提供经验,但提供视角和信念
【来源:虎嗅网】
“从一档历时两年半的播客节目到一套三卷本实体书,他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网罗中文世界20多位中青年学者共同撰稿,为中国的全球史研究打开新视野。他将思想史的关怀带入全球史研究,‘宅兹中国’的同时又放眼世界,让历史超越国家和地理的界限,在全球化退潮的当下,重申‘全球联系’和‘世界公民’的意识。”
历史学家葛兆光75岁了。在接受访谈前,他需要先戴上助听器,才能听清楚坐在对面的来访者的问题。
过去几年,他把一部分工作重心放在了《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上。最早在2018年,葛兆光向梁文道提议,想做一档关于全球史的播客,并为此写下了一份详尽的大纲,包括内容方向和对各个章节的设想。
次年6月,播客《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正式上线,其撰稿人囊括了20多位中青年历史学者。随后两年半里,200多集音频节目陆续播出,受到广泛好评。其间葛兆光撰写导言和结语、修订全部文稿、完善参考书目和年表,付出许多精力。
声音告一段落,文字接续而来:去年年初,三卷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出版。葛兆光花了几个月时间,将节目内容编纂成书,这段面向学界与大众、横跨声音和文字的全球史的讲述,终于更加完整。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葛兆光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2024-4
葛兆光的历史视野向来开阔,从中国到海外,由思想史到全球史,不拘一隅。同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也始终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新周刊》对葛兆光的两次拜访,从2024年夏天到2025年春天,横跨两个年份。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世界动荡不休,许多曾被视作常识的观念反复受到挑战。对于这一切,葛兆光始终关注。在他看来,过去几年对于世界史,尤其是对于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梳理,在当下显得更具意义和启发性:“我们跟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文明、国家是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平等的,这是我们做全球史的目的。”
春天的复旦大学校园,草木萌发。在葛兆光位于二十几层的办公室,能望到校园内外的忙碌人群、穿梭车流,也能保持观察和思考的静谧。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形成,研究历史“不提供具体经验,但是能够提供一些视角和信念”。
“人类毕竟是要互相交往的”,葛兆光这样概括这种信念。
葛兆光。(图/聂一凡摄)
“把第一步迈出去,后面就好办了”
《新周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改变了以往将中国史与全球史分开对待的历史研究传统,把中国放入广阔的全球史视野里,同时强调“从中国出发”。历史视角如此转变之后,有什么新的发现?
葛兆光: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被介绍进中国。尽管在国际上,它已经成为一种很大的研究潮流,但是在中国,很多时候还是止于理论阐述和介绍,没有好好地去自己写一部,更没有认真思考中国学者应当怎样叙述自己的全球史。
从中国出发去谈全球史,就会看到一些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谈全球史时也许探讨得不够的事情,这就构成一种互补。我一再强调“从中国出发”,并不是强调中国在全球史中的份额、地位和意义,而是给全球史提供来自中国的观察角度,也反过来用全球史的视野看中国历史。
一方面,面对全球史中的很多事件、人物、现象,由此有了一种中国观察的视角,比如对于罗马为什么不能像秦汉那样形成一个去地方军事化的,制度、文字、习俗同一化的帝国,我们有了来自中国角度的解释;另一方面,对于很多中国历史上的事件、人物、现象,我们也有了一种全球史背景下的新解读。
比如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谈到1255年法国基督徒鲁布鲁克在哈剌和林的蒙哥汗面前与佛教徒辩论教义,(蒙古帝国对于宗教管控的)尺度那么宽松。可是,第二年同样在蒙哥汗面前,佛道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结果却是禁止《老子化胡经》,严厉打压道教。
为什么尺度突然收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从面对西亚、欧洲转向面对东亚的中国,蒙古人发现,宗教与族群认同在东西方不一样,而东方的宗教也许会成为蒙古帝国统一世界的障碍,因此原来自由宽松的宗教政策就变了。这样,对于蒙哥汗以及后来忽必烈面对佛道时的政策,我们就有了新的了解。
其实,只要放宽历史视野、转换观察角度,不光能增加很多新知识,也会改变很多旧观念。比如,我们会注意到:原来在欧亚大陆,粟特人、波斯人始终是那么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穿针引线人;原来伊斯兰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的崛起和扩张,给世界的东西两端都造成了这么巨大和直接的影响;原来“新大陆”美洲的发现,给亚洲和欧洲带来了如此多的变化;原来对现代国际社会那样重要的《海洋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隐隐约约和东部亚洲海域有关;原来在历史上,日本不仅从中国拿去很多东西,也曾经是中国木材、白银和铜的重要来源地。
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很多,看看我们那套书就知道了。有人觉得,我们的全球史可能涉及面很广,但是还不够深入。我想,确实不够深入。三卷本,100多万字,要想把全球史写得非常深入不大可能,但是我们做的是第一步,把第一步迈出去,后面就好办了。
《新周刊》:几年前,你在一档节目中谈到,很多关于历史的概念、节点、转折,往往是后世赋予前人的。要怎么避免这种后世讲述历史时的一厢情愿?
葛兆光:我们很多看待历史的习惯,是“后见之明”:把喜欢的东西拔高,把不喜欢的东西贬低,甚至把从自己兜里面掏出来的东西塞到古人的兜里面。为了解读得出奇,就不断加码,越说越玄,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每个人都难免有“后见之明”,但也要尽可能顺着历史去梳理。以前我写《中国思想史》《中国禅思想史》,都是希望先回到历史语境里面去,然后再跟着语境去体会当时的人是怎么想的。
就像现在剑桥的昆廷·斯金纳等学者强调的,研究思想最重要的是研究语境中的思想,我们不能离开某种语境,人为地去拔高或者贬低。所以,以前柯林武德就讲,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到过去的心灵里面去体验一下,然后才来叙述的。
另外还需要有宏观的眼光、对历史整体的了解。我们写全球史,可能每一段讲述都不会像过去的国别史那样深刻、精专,但是描述出宏观的、平衡的、全面的历史,让各种文明同时空呈现,才知道我们自己在世界历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中国思想史》
葛兆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2
“我们感到困惑,所以不得不重新打量历史”
《新周刊》:身处转折和剧变的时代,“见证历史”成了一种普遍感受。在人生当中,有什么瞬间也给你带来过这样的历史感受?这种感受又如何影响你?
葛兆光:前两天我们还在感慨,我这一代(50后),有幸生活在没有大战争的时代,比父辈幸运得多。但是没有战争带来的枪炮硝烟,并不意味着历史就会那么平静,生活就会那么顺畅。
在我记忆中,对我影响很大的事件很多。从小的说,在我个人历史上,1960年全家从北京下放到贵州的一个县城、18年后的1978年我考上北京大学改变命运,都算是大事吧。但是从大历史而言,我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恐怕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转向,等等。
个人的小历史,处在国家的大历史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时势比人强”:如果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没有根本性地变好,个人的命运只能像一条小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
《新周刊》:最近两年,全球化不断遭遇新挑战,互联网、AI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改变普通人的思想和表达。面对诸多变化,作为研究思想史与全球史的历史学家,你有什么体会和思考?
葛兆光:坦率说,最近的世界变化太快,现在人们常常讲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什么都不确定,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于是就会很迷茫。我也觉得这很悲哀。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更熟悉“过去的故事”。在过去的故事里,我们能够看到,如今世界的文明、规则和共识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是多么艰难。我们原本以为历史会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虽然也明白“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总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就像以前伟大人物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是没想到,最近有些曲折甚至成了挫折。
我们感到困惑,所以不得不重新打量历史。历史不会那么重复,我们只能从历史里面得到一些感知,这些感知不能当作策略来应付现实的变动,它不提供具体经验,但是能够提供一些视角和信念:世界越来越小,人类毕竟是要互相交往的,所以有些现代的价值还是需要的。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著
中华书局,2011-2
《新周刊》:2024年度刀锋图书奖的主题,是“壮阔的平凡”。今天的全球史、思想史研究,以及更多的历史研究领域,如何照见那些细微、具体的普通人生活?反过来说,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关心全球史?
葛兆光:我非常赞同“壮阔的平凡”这个主题。其实,从1902年梁启超开创现代中国历史学以来,学界一直都在号召历史学要改变过去总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研究传统,也一直在强调,历史上很多意义重大的变迁,不一定都是英雄造时势,其实更多是时势造英雄。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现在历史学研究的变化,就是从关注中心到关注边缘、从关注上层到关注下层、从关注特殊到关注一般,这就像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强调的“长时段”的重要性:看上去平静缓慢的变动,有时候反而是最重要的。
其实,全球史和思想史,也不一定都只是宏大叙事和精英视角。许多小事情、小人物,像卜正民研究维米尔的绘画、沈艾娣研究山西一个天主教村庄,都可以写入全球史。
我给沈艾娣那本《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写过推荐词:“谁也想不到中国山西一个不起眼的村庄洞儿沟,居然会和遥远的神圣罗马教廷曾有过三百年的互动。……全球史并不一定要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其实它更是一种方法,试图发掘各种微妙的全球性联系、交流和影响。”
《东京札记》
葛兆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望moutain,2024-1
同样,思想史也在变。我在1998年就提倡发掘“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强调思想史一定要注意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因为这样的思想史,才能呈现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真正常态,而不只是少数天才的灵光一闪。
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导言和结语中,我反复在讲,历史学一方面要叙述自己的历史,强调国族认同,培养理性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则要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处在全球文化与文明联系中,必须怀有平等、慈悲和友爱的胸怀,与全球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人和平共处,共享文明成果,尊重国际规则,要有世界公民意识。
如果说国别史强调的是前者,那么全球史就是在提倡后者。因为只有了解全球互相联系的历史过程,才能打开你的胸怀,拓宽你的视野,消除你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