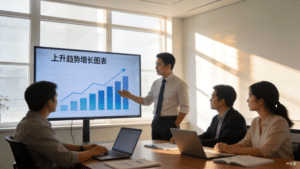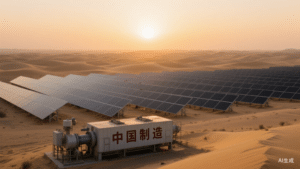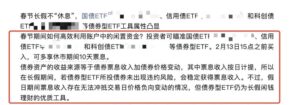无戏可拍,表演系毕业生开始打零工
【来源:虎嗅网】
具体到演员,则是“片酬大幅缩减”“无戏可拍”的境地,新人或者不出名的演员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
2025年4月18日,曾经在几部小众国产电视剧中出镜的女演员黄鹿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刚才跟我经纪人聊天,她说现在北京待着的演员基本上都没有活干,可以面试的剧组特别少,我已经一年都没有去见组了,整整一年。”
2025年4月14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生许鹏发视频称已退圈回老家,接替80多岁的爷爷赶集摆摊,视频迅速冲上热搜……
“艺考学表演开始,我们其实都是有演员梦的。”杨海波语气轻快地说道,但现在,这个刚毕业的表演系学生,正被愈发严酷的行情挤出演艺圈。
“铺天盖地”零工群
在成都念表演系的大三学生叶诗涵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念书这几年,她前后加了十来个“零工群”,以便海淘工作机会。其中7个是学长学姐给免费拉的,还有3个是她在写真店老板那里花钱买来的,每个群价格2~3元——那个老板也认识一些制片和经纪人,会时不时发布各种拍摄需求。
“非中戏、北电、上戏毕业的学生,如果要做演员,就要接受长期打零工的状态。”从业十年的演员经纪人赵俊峰告诉我。
杨海波学校也有不少零工群,做平面模特、拍广告宣传片是招工的主要内容。他的一些师哥师姐因此成了品牌方联系学生的“经纪人”,还能赚上一笔,“比如品牌方拍摄项目,说今天要找十个人,预算每个人给1000块,对接人拿走400块,同学拿到600块……有人一个月就可以赚3万块”。
但群里不少机会不是“拍戏”而是“做戏”:
比如帮社交平台账号拍摄短视频内容。“抖音很多个人账号下面发布的短视频都有剧本,请表演系的学生演,像那些假情侣、街头采访视频都是。”杨海波说,这些视频拍摄一条一天能挣800~1500元,每天只拍2~4小时,而且规定同样的角色内容在180天内不能为其他公司拍摄,大学四年他总共在这件事上挣了大约10万元,“不过这样的零工通告在疫情后越来越少了,很多公司为了省钱干脆开始找自己公司的员工拍,反正不难。”
或者招募“职业充场人”,一些品牌会在群里发布通告,只要到场,每人可以拿到100块钱一天的报酬;还有为相亲节目招募男嘉宾演员的,他说,“有节目是一个人给3000块,但是你一定要长得帅。上去以后你的资料都是他们给你编的。”
感觉零工群里的需求日益离谱,杨海波特地翻出招聘软件找过演员的工作,信息栏里有一家公司写“招演员”,视频面试也聊得很愉快,对方对他的表演系学习经历很感兴趣,可实际到了公司地址一看——“是中国人寿,招的是保险销售”。
他回想起该工作岗位的招聘要求,“要亲和力强,身高达到一米八,男主角必须口才好、随机应变能力强”,他觉得这事更离谱了。
叶诗涵觉得零工群里的工作机会“看起来铺天盖地”,但真能被“砸中”的概率却很小,她是那种“想到就要去做”的性格,常常是一个月投递了几百次个人资料,也收不回一次剧组回复。她已经习惯了“石沉大海”的普遍状况,但这天,她迎来了一次例外。
这是一部现代剧,要试女三号。对方发布的通告包含了剧本类型、拍摄时间、薪资、所需演员情况等内容,这和其他通告没什么差别。录制试戏视频的时候,叶诗涵把相机对准自己,努力想象着剧本中的场景、搭档的表情、动作、语言,却始终难以进入状态,最终只发了一条自己并不满意的视频过去。没想到,没过几分钟(试戏视频时长都没到),对方回复道:就是你了。
叶诗涵先是激动,而后疑惑起来。她又反复看了几遍通告,发现没有说明拍摄地点。追问之下,对方答复说在陕西省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县城,随后立即开始催促她买火车票进组。她没敢再继续沟通:万一是把我骗去搞传销呢?——三年前,四川音乐学院表演系就曾有女学生被骗去川西拍摄,结果陷入传销组织,被关了一个多月。
类似的通告叶诗涵后来还遇过几次,当她看见2025年初演员王星被艺人经纪骗至缅甸电诈园,以及2月中国传媒大学音乐剧专业学生龙莉莎因短剧招募演员而被骗入传销窝点两则骗局时,并不觉得奇怪,“很多人都说,演员没被骗只是因为没有遇到为你量身定做的骗局”。
好在,叶诗涵无意间在写真店拍摄的一组照片被老板选作样片挂在店外展示,她顺水推舟,把这件事包装成“为企业拍摄广告”写进个人履历里,刚一开学就成功接到了一条饮品类平面模特拍摄邀约,没有剧情设计,对演技也没有要求。拍摄当天,叶诗涵来到摄影棚,花两三个小时做造型,按照对方的要求摆动作、展示商品。“1小时100块,太轻松了”。
有了这次拍摄经历之后,叶诗涵投递平面模特工作变得顺利了一些,常常会有经纪人前来邀约。两三次拍摄后,她望着摄影师手中的照相机镜头时,心中好失落,平面模特好像只看中脸蛋和身材,“这和我学的毫无关联,我想演戏”。
最好的1%,也难免急转直下
在演员经纪人赵俊峰看来,想达成“演员梦”有硬性条件,签经纪公司这条出路,只适用于1%的表演系学生,诞生在北影、中戏这些最好的学校里。
但近几年1%的状况也没有那么理想了。尤钲渲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2025年初刚杀青了一部戏,戏里有刚从中戏、北电毕业的年轻演员,他觉得他们“形象气质都特别好,放在3年前甚至5年前,一毕业就能当偶像剧男一号,一定会被大公司签掉,但现在的状况并不是。”
事实上开设表演系的国内知名院校正在不断缩招,上海戏剧学院招生人数从2018年的70人下降到了2025年的54人,下降比例高达20%;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人数也从2022年以来下降了6%;中央戏剧学院2025招生简章中也取消了偶剧和动作表演专业,表演系招生总人数从2024年的85人进一步缩到68人。
不稳定的大环境是从2020年开始的,到了2023年,境况急转直下。尤钲渲2020年上半年没接到过一部戏,“好不容易那年6月接到一部戏,很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又起来”。他有记账的习惯,他看了看自己的账本,直到2023年1月,包括广告在内一年平均拍5个戏,“命运还还挺眷顾我的,一年还能挣个十五二十万”,“可是从那以后,突然就没戏了”。
那段时间,甚至后来大红大紫的年轻演员蒋奇明也在困局里。当时他发过一条“在线求职”的微博,姿态摆得很低:“本人(蒋奇明)本职工作是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虚岁二十八,疫情期间赋闲在家,没有额外收入,不知是否有北京公司愿意接纳入世以来只干过演员工作的‘社会人’……”
2024年,尤钲渲发现市面上演员的工作类型开始改变,从剧集、电影变成了中央6台的数字电影,或是一些小成本的院线电影,以及地方文旅投资的宣传片,“电视台的电视剧只剩下了红色革命题材”。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开始研究拍摄微短剧,那年他接了两部微短剧,都饰演的是反派一号,合作的演员是《甄嬛传》里演温太医和沈眉庄的演员,以及尹正和郭晓婷。
尽管尤钲渲身边的导演、制片人朋友都劝他:不要去拍竖屏,会毁了你。但他决心顺势而为。
“竖屏短剧已经占据了影视市场的半壁江山,时代变了,就像当年网大起来的样子,”尤钲渲感叹,“是你活的类型不对了。”
鄙视链、横漂和女二号的床戏
演艺圈有一个通识是,只有演了长剧、电影才叫“演戏”。这些表演系的学生告诉我,“老师说不要演短剧”,“如果你做了短剧的话,在行业里边儿就不可能再让你去演话剧或者是演电影”。
2022年毕业的周琪在上学时,就听老师谈起过演艺行业内的“鄙视链”:演技水平、播出平台以及作品的艺术性等因素共同决定了鄙视链的排序,短剧只需要靠剪辑来推进剧情,演员的表演能力几乎不做要求,处于鄙视链最底端。
但在无戏可拍的情况下,短剧变成了包括尤钲渲这样的老演员和更多表演系毕业生迫于生计的选择。“我身边的同学在上学的时候就能靠短剧养活自己。”周琪说。
已经拍了半年短剧的叶诗涵说自己并不是不想演长剧,只是现阶段能接触到的只有短剧。在零工群找不到靠谱的工作,她决定主动出击,利用暑假去横店:“我觉得演短剧并不丢人……”
到横店之前,她打印了厚厚一大摞个人资料。剧组会在横店剧组组讯公众号发布演员通告信息,她把剧组地址都导入地图,按照距离远近排列出最便捷的路线,然后依次前往,每天就像发广告传单一样发自己的资料。
剧组都在酒店驻扎。叶诗涵敲开第一个剧组的房门,两三个工作人员坐在一张简易小桌前。她递上自己的材料后,对方随意翻了翻,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询问她是否毕业,她如实回答后,对方说:“要是有合适的,我联系你哈。”
叶诗涵觉得这可能意味着自己大概率被淘汰了。
两个月时间她几乎都是汗津津的,奔波在一个又一个剧组投递材料。她算了算真正进组拍摄的时间,只有10来天,工钱日结,挣来的很快又全部花在了其余40多天的跑组路费、吃饭、住宿上。她不确定追梦拍戏的这段时间,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横店没有地铁,为节省时间她基本打车出行。一天跑8个组,车费就得80元,加上吃饭和住宿,每天200元就这么花出去了。在剧组休息的间隙,她还要抓紧录新的试戏视频——她感觉自己对时间和金钱都失去了概念。
但真正能劝退这些00后表演系学生的,是在短剧拍摄现场工作人员的性骚扰。有一次,叶诗涵的拍摄要穿抹胸礼服。现场制片人看到她后,目不转睛,手也不自觉摸了上去。叶诗涵大声呵斥道:“你干什么,有病!”顿时吸引了全剧组的目光。当时戏已经拍了一半,剧组不好换人,制片人只能作罢了。后来,她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写真时,这名制片人还会评论“这小腰真细,这腿真细”,叶诗涵觉得一阵恶心,把他屏蔽了。
2024年李婉晴从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学院刚毕业,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结识一位短剧制片人。对方看过她的资料后,让她尽快进组饰演恶毒女二。直到开拍前一天对方才发来剧本,里面有床戏,她截图问对方尺度,得到的回复是:片子要上正规平台,尺度不会太大。
进组定妆时,导演走到李婉晴跟前看着她的服装,边说衣服不够收腰,边上手使劲抓她的腰。李婉晴尴尬往后退了一步,可导演又把她拉回去,说:“你这样不行,要把这个收一下。”为了赚钱,李婉晴只能忍耐。
剧本上的床戏如制片人所说用借位拍摄,但李婉晴仍能从导演眼中看到不满。床戏这一场拍了好多条才通过,拍完那天,导演面对在场所有人说道:“这剧拍得哪儿哪儿都挺好,就是这床戏拍得不好。”
李婉晴是那种特别温和的人,受了委屈也会一忍再忍。但那天散场后,她在化妆间忍不住大哭一场,发誓再也不接这类拍摄。而这次拍摄的片酬,好几个月后都没到账。
这些朝不保夕的“零工”感受是短剧从业者遇到的普遍情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 研究员田元在田野调查里发现,短剧从业者们几乎都在审慎思考微短剧“是否堪当一项‘体面的工作’或‘事业’”,微短剧成为了一种从业者普遍以“零工状态”参与的片场。
走进“零工经济”:一门生活的必修课
2024年底,杨海波找到了毕业以来第二份全职工作,入职了一家位于杭州的MCN机构做HR,主要工作是把其他行业的俊男美女招募进来当主播,这在直播行业里叫“洗人”。
在招聘软件上,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招团播”之类直白的字眼,而是写“招演员”“招模特”,“因为这样才可能筛出外形条件不错的人”——他发现自己开始以当初保险公司骗人的套路,在骗这些表演系学生。
等到表演系毕业生来到现场发现不对劲,他会以过来人的身份,设身处地去和对方沟通生存需求的问题,“如果是刚毕业的学生,我就会问他,怎么会想要来做演员,我看你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是哦,在这个杭州生活压力很大,你来我们公司我觉得你外形条件很好,你可以把资料发我一份,我传到库里,我们这边的拍四个小时有800块钱。”
此时,对方会被这样的说辞打动,暂且放下“演员梦”。但他们一开始不会知道,杨海波会在深夜的直播间里午夜梦回,不屈不挠地演起程蝶衣。
斜杠青年李婉晴也有靠演戏养活自己的愿望,可在以打零工为主的现实面前,实现这个愿望尤其遥远。在上海的这半年,李婉晴将自己所有的收入累加起来,总共 24250 元,平均到每个月只有 3666 元。就算加上尚未结清的款项,总收入也不过3万出头。她苦笑:“真的只够房租。要不是家里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我真不知如何在上海生存下去。
去年在横店时,结束了跑组的叶诗涵到一家兰州拉面店里吃一碗面,只是三十来块钱的一餐,居然扫不出钱来了。她这才对演员的零工生涯有了切身的体感,“是时候对人生有一些规划了”。
为了生存,更多的表演系学生,走向了“零工经济”的广阔天地。毕业于2017年的唐皓阳曾送过外卖、闪送,一手拿着简历,骑着送外卖的电瓶车在城市街道中穿梭。尤钲渲也曾在接不到戏的时刻,用自己的车注册了网约车平台,当过半年左右的网约车司机。这份“零工”让他有了不少意外收获——他每天在车上与人聊天,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他说即便是有戏拍的演员,也会发现自己始终生活在剧组封闭的小社会里,“我们实际上对外面的大社会体会得很少”,所以接触社会、体验各种生活是演员的必修课。
前不久,朋友又向尤钲渲递来一份临时工作的橄榄枝,请他去帮一所学校排话剧。这所学校在北京门头沟的村子里,因为学生想去参加戏剧比赛,10个四五年级的孩子要排一出20分钟左右的小话剧,需要找指导老师。他一口答应这个不挣钱的工作。
他每周给孩子们上2次课,一次2个小时,最终话剧排出来了,学校也没告诉他比赛名次,但他心满意足,“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对演戏这件事儿失去兴趣了。不是因为我演不好,挣不着钱,而是因为我的形象在这儿摆着,不是大侠就是将军,要么反面人物比如歹毒的科学家、老板,所有角色都是同质化的……当我想去设计一些东西,很多导演都告诉我,老师,你想法是很好的,但没有这个时间让你去发挥了。”
在那所乡村小学,尤钲渲感觉自己干了件非常正确的事情,“至少在那两个半月里,这帮小孩很开心,接触到新的东西”。
如今,尤钲渲也不再执着演戏,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规划:如果到45岁演员的路依然没有什么起色,就会换一条路。他在横店打听过,表演指导老师一个月能有2到3万元薪水,他寻思着自己也许可以去那里当个老师,“就不指着这个(演戏)生活了,指着别的生活。”
演员梦未了
杨海波改行后的生活并不如他所愿。由于在杭州的薪资没法负担生活成本,他决定离职回老家做娱乐主播,“这样起码不用付房租”。他每天在直播间的收入也很惨淡,比如2025年这个4月,每天只挣几块钱。好在他最近突然接到了北京一家剧团的面试邀请,他决定北上再试一试,“毕竟北京资源还是更多”。
梦想好像就在那里,但他不知通向那里会是怎样的路。
“如果你想当演员,那就得以你的主业去养,因为演员永远是吃不饱饭的,除非是明星。”周琪说,在她彻底不做演员之后,周围朋友总问她“为什么不当演员了”,“我就会告诉他们,你知道张颂文吗?这些厚积薄发的演员熬了2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还是在北电中戏,我只是中等院校,不知道要熬到多少年才能熬出来。”
一转眼,周琪大学毕业已经过了四年,她已经数不清自己打过多少种零工,熬过多少波折和委屈:
她做过动捕演员,每天携带动作捕捉装置,让游戏、动画里虚拟人物的动作变得和人类一样流畅。工作结束后,周琪无意中在电脑看到对方公司领导的微信界面,上面备注着她的工资,实际是每天1600元——但最终她只拿到了600元报酬。仔细想来,大概是经纪人从中抽成拿走了1000元;
她还去武汉考过舞蹈教师资格证,专业课老师认为她的肢体表达能力比语言和情感表达更强,当面给她推了联络人的微信名片。这是一份兼职工作,一小时费用100多元,一个月下来只有两三千元;
她觉得不够花,又去抖音直播间做娱乐主播挣钱,“唱唱歌跳跳舞”,后来一天播到8个小时,下课以后回家从晚上11点一直播到第二天早上7点,父母只有吃早饭的时候,才能看到她……
如今,周琪彻底转行,做起了一家新能源品牌汽车的直播间主播,在直播间她只需要正常介绍车型、促成销售即可,“投了几百份简历,只有这个看起来靠谱的公司回复面试”,她不想再过那种做3个月再失业3个月的零工生活,她对自己现在有五险一金的主业很满意。
只是时不时地,她还是会怀念起在沉浸式剧场的时光——那是她毕业以来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和演员直接相关的工作,周琪说她当时很快乐,但现在剧场已经倒闭了。
那是一家可以住进去体验整晚惊悚戏剧的游戏剧场酒店,游戏设定这是一家民国时期酒店,整栋楼里有超过50个角色,和30多条剧情线。简历投递以后第二天,周琪就收到了面试通知。
面试她的是剧场老板,先叫她记下一段剧本里的台词。导演介绍,这段台词属于一名三重人格的女角色,一种人格是12岁小女孩,第二种是30多岁的女子,第三种是60岁的老太太,需要把每个不一样的人格体现出来。周琪读了三遍开始演绎。整个面试时间总共40分钟,前20分钟用来背台词和回答基本信息,后20分钟用来表演,以及回答关于剧本的问题。“好过瘾,比我直播啥的有趣多了”,周琪回忆道。
还有一次,她需要扮演一个长发女鬼。
她戴上了厚实的假发,用披散下来的头发挡住脸,她的使命是极尽神秘,把10多个观众,一个个追到不同房间里,触发下一轮剧情。房间有窗玻璃,周琪需要在玻璃外面继续扮鬼吓观众。结果状况发生了——当她吓完观众转头准备离开,头“咣当”一声撞到出了故障的栏杆上。
恐怖气氛一下烟消云散,10多个人上一秒都快吓哭了,下一秒在房间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
当时周琪撞得太猛,脑袋发晕,觉得要倒下了,这时候脑海里一个声音倔强地提醒她:“这是一个舞台,即便演错了也不能穿帮,不能变成演出事故。”
作为一个快要晕倒的女鬼,她强行站住,绷住凌厉的表情,深呼吸。努力稳住状态以后,她带着那一抹燃烧的演员之魂,“飘飘然走了”。
文中周琪、李婉晴、叶诗涵、赵俊峰、唐皓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