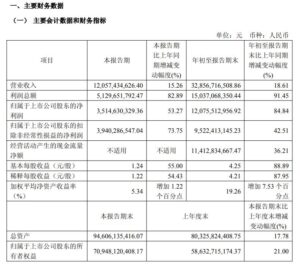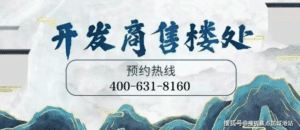在都柏林寻觅乔伊斯的踪迹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金衡山
乔伊斯塑像在北厄尔街口,比邻都柏林的主干街奥康奈尔大街。塑像身躯比真人要大一点,形态独特;乔伊斯头戴呢帽,帽檐斜翘,一副小圆眼镜扣在脸上,身穿大衣,一只手斜插在裤子口袋里,衣襟掀起,另一只手拄一根文明棍。他的脸半翘朝天,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这家伙不屑什么呢?
乔伊斯塑像 作者/供图
奥康奈尔大街上有很多塑像,皆是一些为爱尔兰的独立而发起各种运动、甚至献出生命的名人,大街上还有一根高高的尖塔,全钢筋建筑,甚是壮观。相比这些,乔伊斯的塑像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似乎也没有多少路人理睬他,偶尔有几个游人匆匆拍照,然后又匆匆离开。
不过,都柏林大概是不会忘记这个老乡的,尽管他早早就离开了这个城市。这里有他的出生故居铭牌、有他父亲带着全家从郊外搬入城内的住处。有为他专门建立的“乔伊斯中心”,位于离城内步行二十分钟左右的一个住宅区,同样是一处不起眼的普通住房,但是究其历史,则可以回溯到18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就有联排三层公寓,乔治时代的风格,可以想象其时的都柏林已经颇具规模。
而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与此地的主人、一个在《尤利西斯》里时常出现的都柏林著名人物有点关系的乔伊斯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可惜我造访的那天是周一,中心不开门。只能朝门看上几眼,发现门口有破碎的啤酒瓶碎片,估计是爱喝啤酒的本地爱尔兰人兴奋之余留下的,他们不会是乔伊斯的拥趸吧?
其实用不着去问这样的问题的,都柏林留下的乔伊斯的印迹太多太多,有好事者探寻梳理乔伊斯作品,尤其是《都柏林人》与《尤利西斯》,做出推断说,即便都柏林不在了,人们也可以从其笔下的描述中画出一幅这个城市的街路图来。由此可见他与其故乡的紧密关系。
1912年后,乔伊斯离开了爱尔兰。从此他的脚再没有踩上过爱尔兰的土地。但是都柏林人似乎并没有忘记他,更重要的是,乔伊斯的写作浸透了太多他故乡的气息和风土。乔伊斯是被当作现代主义大师在文学史上留下大名的,不过其风格本身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早先的《都柏林人》这部后来被称为经典之作的短篇小说集中,乔伊斯的写实风格明显,故事中出现的地名多为真实之地。
这部作品的巅峰之作,最后一个故事《死者》的发生地就在都柏林中心城区利菲河上的乔伊斯桥一侧的一座公寓里。为很多文学爱好者所熟悉的这部作品中的一个小故事《阿拉比》,开篇就说到一个地点——北里士满街,那是一个死胡同。
按图索骥,在离市中心(走路半个小时左右)不远的住宅区找到了这个地方,还是原来的地名,似乎要比胡同大一点,是一条街(原作中说的就是街),街的尽头有一幢房子,二层的别墅,就叫“阿拉比厅”(Araby House),所以是一条此路不通的街。
街道一侧有一些较低矮的平房,街名上有“村舍”字样。原作中,叙述者提到他们这帮半大孩子在街后面的农舍里撒野玩耍打闹,那里还有马厩。现在当然看不见了,但从这些房子的破败样子来看,可以想象一百年前的景象,同时也可以大致肯定此地在很多程度上保持了原来的基本模样。
小说中还专门提到了里士满街区的一个天主教学校,现在可以看到街另一侧有一幢颇有模样的大房子,前院门楣上有一个十字架,大概也与教会有关。最令人好奇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个小男孩在其叔叔家楼上的窗户里望出去,看街边站着的一个大女孩,他那时心中正翻腾着少年的懵懂,热切地想象女孩的美好与美丽,乔伊斯有非常真切的描述,读来让人感同身受。
1904年,二十岁的乔伊斯遇见了他的缪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诺拉,开始一段浪漫之旅。是不是有可能回首往事时,乔伊斯把那不可忘却的初恋之情放到了故事中的那位少年身上,尽管小说结尾时少年在经历了一番生活遭遇后突然醒悟,解剖了自己心中的虚荣感,但少年曾有的对美好情感的渴望应是非常真实的,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乔伊斯在小说中发明的“顿悟”(epiphany)写法让故事在瞬间产生了飞跃的可能,这种无论是叙述方式上还是思想感受上的高度跳跃贯彻在这部短篇集中几乎所有故事中,在《死者》中叙述者的对已经逝去的爱的突然感悟,让读者难以忘怀。从文学地理的角度看,是不是也可以从象征的手法读成乔伊斯对都柏林的一种思念与缅怀?
小说出版时,他已经离开了故土。现在回过头来看《阿拉比》,那个“我”叙述者的叔叔的公寓是附近哪幢楼里的房间?这还真不好断定,可以确定的是小说尽管用的是第三叙述者与“我”叙述者的结合,用更加学术的语言说,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与第一人称视角的融合,但很显然,可以看出小说中很多地方透露出“倒叙”的影子,其中提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只是一笔带过,也足以表明乔伊斯写实主义的深刻内涵。
由此,可以过渡到一个相关话题。爱尔兰是一个小国,但文化上绝对大大地超过了“小”的范围。在都柏林,在乔伊斯曾经读书过的天主教大学学院老校区(他于1899—1902在这里上学),现在成为了爱尔兰文学博物馆。在这里,发现了过去熟悉但不知道其爱尔兰原籍的不少大名鼎鼎的作家,如萧伯纳、王尔德、贝克特,还有写《格里佛游记》的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原来他也是爱尔兰人。这些作家大多在爱尔兰以外成名,但爱尔兰人把他们视为自己的骄傲,这自然是一种文化大国的表征。
顺便提一下,19世纪30年代在牛津以推动天主教复兴运动闻名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主教是这里的第一个院长。此外,当然有更多的爱尔兰本土作家,如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记得早年学英语时读过他的一个短篇,幽默诙谐又充满韧性禀赋,留下很深印象,现在看来很有点爱尔兰人的特征性格。
非常有意思的是,博物馆的咖啡餐厅提供很可口的午餐,色香俱全。埋头饕餮时,偶然抬头看到对面墙上有几幅图画,其中一幅画的是桌子上漂亮地摆着的一盘菜肴,那是一只烤鹅。图的下方有一块铜匾,上面是一段文字,凑近看觉得有点熟悉,再看落款,原来摘自乔伊斯《死者》中叙述者参加一次宴请的描述:“一只肥硕的烤得焦黄的鹅放在桌子的一端……”看来乔伊斯也可以在餐厅里出现,为进餐助兴,文化大餐在这里倒确是有了实证。
博物馆有乔伊斯专场展览,展出《尤利西斯》的各种译本,此书出版于1922年,1927年就有了德语版。在各种译本中发现了金缇先生的中译本。似乎这本意识流方式强烈的书在世界各地有很多读者。或许当真,不过有一处展出的材料值得注意,乔伊斯把他的书送给了他的一个朋友,后者又把书借给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位女士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在日记中写了读此书的感觉:有趣,怪诞不经,还有很多让人不快的内容,无法在吃饭时阅读。这是写于1926年的一段话。
乔伊斯的这本书曾被当成禁书,出版当然遇到了不少麻烦。有一个1936年的版本由大画家马蒂斯插图,画的是两个类似毕加索立体型人体的交合动作,很是暧昧;展出提示插图旁边原作的内容是描述主人公布鲁姆与女友就餐场景,其中提到裸体仙女,提示又说马蒂斯的画基于荷马作品《奥德赛》而作,他根本没有读过乔伊斯原作。当然他知道此作与《奥德赛》的关系。这或许也暗示了《尤利西斯》与一些读者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乔伊斯的暧昧文字造成的后果也是其时一些爱尔兰作家面临的困境。
1922年爱尔兰独立前后,作家们要面对文字检查法案,他们自然也奋起抵抗,展出的作家联合声明表示其维护言论自由的努力,以及改变道德观念的行动。不过相比之下,展览更多内容聚焦在独立后爱尔兰作家探索民族文学的路径与遭遇的困惑。
大诗人叶芝在一首诗里写下“一种可怕的美诞生了”。所谓“美”更指巨变时刻带来的迷茫、迷思与迷惑。有关这位在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参与了各种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在展览中并没有见到很多,有点让人不解。
博物馆对面有一个绿地公园,里面有一尊乔伊斯头像,中规中矩,严肃、有点憨厚的脸容。雕像下面刻有他说过的一句话:“这里的绿地是我的最爱……”可见早在那个时期这个城市就有了让市民休闲的地方了。
相比之下,公园一角叶芝的雕像就非常夸张,简直就是奇特,没有头像,没有手脚,只有大致是S形状的半个身体的抽象形态。创造者是要表示叶芝诗歌不同时期风格的迥异,还是其文学内涵和思想精神的深刻?
公园里还有关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爱尔兰大饥荒的雕塑,两座没有头颅的、干瘪的躯干,一座虽有脑袋但面容空凹、坐在地上的塑像,边上是卷缩着身体的一个小孩像,同样没有头颅。这应该是一家人的形象,放置于历史的具体情景中,这一点都不夸张。其时大饥荒让一百万人死于饥馑,也是史上爱尔兰人大批移民美国的时刻。这里的人用文化的方式表现历史上的苦难,这也是文化可以发挥的作用,它让记忆不能抹去。
在这座各个角落都矗立着纪念雕像的公园里,大概最招人注意的是王尔德的塑像。脚蹬皮鞋,身穿时装,中分长发披耳,一只手在半胸,似乎手握一卷诗书,另一只手握紧拳头搁在身边。他眼睛半眯,嘴角微翘,像是在讥讽什么。他躺在一块凹凸不平的巨大山石上,一只脚斜伸,另一只脚半弯,上半身翘起好像随时要从大石块上一跃而下,去为他的名声争斗。
雕像前还有两尊搁在黑色长方块大理石上的塑像,一尊是一个全裸怀孕女子像,头斜歪着似要对视后面的王尔德,另一尊是颇有点类似古希腊雕像的男子半身像。在两尊塑像大理石台座上刻有王尔德曾经在作品中展现过的名言警句,如“准时是时间的小偷;生活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很复杂;我们都陷于沟壑中,但有些人却眼望星空”。
不知道这两尊塑像与石头上的王尔德像有什么关系,但感觉这里不只是在展出其作品的语言与思想的机智与隽永,而更是在暗示这位19世纪后期文坛风云人物的跌宕起伏的人生,而这其实与都柏林有关。跟他打官司、控告他的律师曾是他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读书时的同学。
王尔德面临的不只是一起同性恋案件,更是涉及诽谤、反诽谤、地下性活动场景、暗探调查、审判与破产等等,透露的是时代变迁时的种种纠葛与复杂。显然,雕像的创作者有着敏锐的眼光,出色的表现力。在这个都柏林的公共花园里、在乔伊斯曾经热爱过的这片绿地上,文化又一次展现了其奇特的力量与魅力。
傍晚时分,在城内转了一圈。沿着美丽的利菲河,走过半便士桥,进入都柏林城堡广场,绕弯到圣派特里克大教堂,回头路过酒吧街,乔伊斯曾经在这里的一家酒吧喝过吉斯尼黑啤,最后又回到他的塑像这边。晚上八九点,天光依旧大亮,路上行人渐少。永远的乔伊斯永远地撇着嘴,他属于世界,更属于都柏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金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