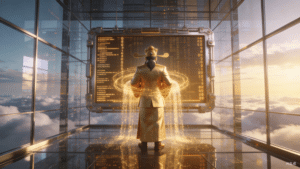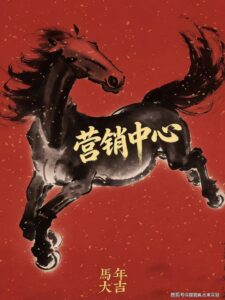罗翔:AI时代,文科通识教育如何可能?
【来源:虎嗅网】
这段时间,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一种职业危机感,认为自己的工作迟早会被AI取代。有同事悲叹,教师这个行业迟早会消亡,文科的衰败不可避免,人们只要学好如何运用AI就已经足够。AI技术俨然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知识,似乎已是万知之知。然而,果真如此吗?AI时代的文科通识教育该往何处去,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一、关于知识的知识
我想起了柏拉图的《卡尔弥德篇》,书中苏格拉底和几位年轻人在讨论何谓明智,是否存在一种关于知识的知识。在这次对话中,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有四位,除了苏格拉底,还有三位年轻人,分别是卡尔弥德、格里底亚和凯瑞丰。卡尔弥德是柏拉图的亲舅舅,出生于名门望族。当时的卡尔弥德十八岁,长得非常俊美,颇有才气,追随者众多。格里底亚是卡尔弥德的堂哥和监护人。
公元前四〇四年,也就是这次对话二十五年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格里底亚为首的三十人篡夺了雅典的政权,史称三十僭主,实施恐怖统治。八个月后,三十僭主垮台,民主制恢复,格里底亚被处死。卡尔弥德也是三十僭主的骨干,他在比雷埃夫斯港大决战中被民主派杀死。所以,这次对话也可以看成苏格拉底对两位未来僭主的教育,让他们有所节制。凯瑞丰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就是他去雅典的德尔菲神庙请教祭司,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神谕的指示是没有。苏格拉底为了验证神谕,走上了哲学的道路,他意识到神谕的意思是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是真正的智慧。
对话的主题是论明智(SŌPHRO-SUNĒ),明智是古希腊的四大美德之一。希腊文“SPŌHRO-SUNĒ”有多重含义,如明智(Wisdom)和节制(Temperance)等等。对话的缘起是卡尔弥德的出现,他被誉为当时雅典最美的少年,苏格拉底遭遇了强烈的爱欲挑战,但是他的理性节制了他的欲望。当众人为卡尔弥德的美“大惊失色,手足无措”(154C)之时,苏格拉底却提醒众人,真正的美不仅仅是外在的美,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灵魂之美(154E)。作为卡尔弥德的监护人,格里底亚认为卡尔弥德不仅相貌出众,在明智方面也是首屈一指(157D)。苏格拉底于是和卡尔弥德展开了关于明智的讨论。
因为卡尔弥德头疼,所以格里底亚让苏格拉底假装医生给卡尔弥德治病,苏格拉底自然知道自己不是医生,他了解自己知识的边界。苏格拉底认为身体上的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灵魂上的疾病所致,“而要治疗灵魂必须使用某些咒语,这咒语就是美好的话语”(157A)。
苏格拉底首先问了卡尔弥德一个问题,问他是否真的具有明智的美德。如果卡尔弥德给出了肯定性的答案,那只能证明他的灵魂已经病入膏肓;如果他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灵魂还有药可救。但是卡尔弥德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如果说我不明智,那是糟蹋自己,我觉得不合理,而且那也是反驳格里底亚……如果我说我明智,那是恭维自己,我觉得不礼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答复你。”(158D)用今天的话来说,卡尔弥德情商很高,他不想冒犯任何人。同时,他也具有讨好性人格,他很懂说话的技巧,但不在乎语言所指涉的真实。
苏格拉底开始询问卡尔弥德何谓明智,卡尔弥德分别给出了明智的三个定义:一是“沉着”,二是“谦逊”,三是“做自己的事”。前两个定义来源于卡尔弥德的经验性描述,后一个定义则是从格里底亚那里听来的。然而,经验性描述不过只是部分的人类经验,很容易被驳斥。经验世界就如《理想国》描述的洞穴世界,充满着幻象。康德说,它是令人作呕的大杂烩,人类的经验无法给道德提供确定性的基础。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扬·萨恩雷丹 作,科内利斯·范·哈勒姆仿于1604年,现藏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来源:wikipedia.org)
当卡尔弥德关于明智的两个经验性描述被苏格拉底驳斥,他立即提出了第三个定义,即“做自己的事”,这恰恰是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关于正义的定义,当城邦中的民众各安天命,各尽其职,城邦就是正义的。当个体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保持和谐,个体也就是正义的。格里底亚向来以苏格拉底的代言人自居,经常会兜售苏格拉底的哲学金句,然而这些金句一旦脱离具体的语境,含义就会发生偏离。
面对苏格拉底关于什么叫“做自己的事”的追问,格里底亚抛出了第四个定义——“做好自己的事”。格里底亚的“好”是一种结果意义的利益,也就是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苏格拉底马上追问格里底亚“好的事情”与“自己的事情”是什么关系。比如医生给病人开了对症的药物,最后药到病除,医生得到了患者的感谢,并获得了经济上的回报,这自然对医生有益,也对病人有益,格里底亚认为这就是“做好自己的事”。但如果患者不仅不感恩,反而举报医生开的药超过报销范围,医生后来被处分,那这还叫“做好自己的事”吗?
格里底亚再次搬出苏格拉底的金句作为挡箭牌,提出了第五个定义:认识你自己,有自知之明就是明智。格里底亚深得智者学派的精髓,立场并不重要,定义也无意义,重要的是在辩论中取胜。这很像今天网络上的各种争论,用他人曾经说过的只言片语来攻击他人,根本不在乎这句话的语境之所在。
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而格里底亚的“认识你自己”则是认识到自己的无限。前者是一种理性有限的谦卑,后者则是理性过度的狂妄。苏格拉底把德尔菲神谕作为对人的命令,让人在神灵面前时刻保持谦卑,人不是神灵,人终有一死,所以勿要过度狂妄。但格里底亚认为神谕只是神灵和人打招呼而已。当神谕从命令变成问候,人也就与神灵同等。
当苏格拉底继续追问“认识你自己”的含义,格里底亚抛出了第六个定义,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无节制的欲望,那就是对全能性知识的向往。他表明了自己对明智的真实理解,“明智就是知识的知识,也就是关于他自己的知识”,这是一种驾驭一切的知识,当人拥有这种知识,自然就可以拥有无限的权力,开启上帝视野。
面对这个醉心权力的未来僭主,苏格拉底做了最后的规劝。他提醒格里底亚,如果真的存在关于知识的知识,那么它既包括知道,也包括不知道。“明智,有自知之明,就是知道自己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事。”(167A)因此,最接近万知之知的明智就是这种“知己无知”的否定性智慧。另外,即便真的存在关于知识的知识,那么这种全面性知识也无法取代专门性知识,对于拥有全面性知识的人,除非他还懂得类似医学的专门性知识,否则这种全才性的所谓明智之人也无法区分良医和庸医,好药与劣药。因此,即便全才性的明智之人,也应该放手给专业人士,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所以,明智这种看似无所不包的全才性知识其实没什么实际用处。然而,未来的僭主并没有听取苏格拉底的建议,对谈最后不欢而散。
人类的理性有其固有的局限,我们必须对未知保持足够的敬畏。
在《枚农篇》(也译《美诺篇》)中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知识悖论:“一个人不可能去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可能去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不能寻求他知道的东西,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用不着再去寻求了;他也不能寻求他不知道的,是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应该寻求什么。”(80E)AI可以在已知的基础上去扩大知识的范围,但是无法从无到有获得一个完全的新知。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研究不仅仅需要理性,还需要直觉和灵感。
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家最大的任务就是去寻找那些最普遍的规律,人们只用演绎,就能根据这些规律推导出一幅世界的画面。通往这些规律的道路并无逻辑可言。人只能靠直觉,其基础是一种对知识的热爱。”通过直觉和灵感获取的新知更像是一种从无到有的经历,它需要神来之笔的灵光一现。我们不能以狂妄的理性拒绝未知。就像洞穴中的囚徒,如果有一种神秘未知的力量拉着我们掉头,但是我们执拗地拒绝掉头,因为理性无法给其提供确定性掉头的根据,那么我们也就失去走出洞穴探究未知本真的机会。
在AI时代,很多人对AI技术也有格里底亚式的错觉,认为AI技术就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知识,掌握AI技术的人也就可以成为拥有全能性知识的明智全才。当科技僭主与政治僭主一拍即合,善良的愿望极有可能把人类引入人间地狱。因此,我们更加需要苏格拉底式的文科通识教育,需要知己无知的明智和节制,避免理性的狂妄与自大。真正接近全知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二、反思人工智能的相对主义价值观
苏格拉底的主要哲学对手就是智者学派,卡尔弥德和格里底亚应该非常熟悉智者学派的雄辩术,在《普罗泰戈拉篇》中也能看到两人的身影(315A)。智者学派又称诡辩学派,他们不承认真理,属于相对主义,他们用似是而非的智慧来颠倒黑白,玩弄语言,以此攫取财物。普罗泰戈拉是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学院的学生非常熟悉他的“半费之诉”的故事。遗憾的是,无论是当时雅典的年轻人,还是当下的年轻人,可能都更醉心于相对主义的语言游戏。苏格拉底虽然主张否定性的智慧,承认自己的无知,但他并不像虚无主义者那样否定真理的存在。
不少人认为,在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价值具有主观性,因此对于AI技术,必须持价值中立的立场。然而,这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价值中立本身并不中立,它不过以技术中立的幌子掩盖了它相对主义的本质。价值中立主张一切价值具有同等的意义,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但这种立场本身就具有绝对性。
我问了某著名的AI一个问题,什么是邪恶?它的回答是:“‘邪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的文化、哲学、宗教和道德体系对其有不同的定义。”然后,它从多种角度讨论了邪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邪恶并非一个单一的、普遍适用的概念,而是随着文化、信仰和哲学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于是我又问它:“有没有客观意义上的邪恶?”它的结论是没有结论,要根据个人的立场来进行判断。然后,它非常鸡贼地把皮球踢给了我:“你的看法呢?你觉得邪恶是客观存在的吗?”这看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答案,把所有的观念展示给你,让你进行选择,但其内在逻辑依然是相对主义的多元包容,最终的答案是没有答案。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所以我们本能地认为所有的观点和立场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然而“接纳不同观点的存在”和“接纳不同观点”是不同的,正如“认可他人有持不同立场的权利”和“认可他人的立场”也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你可以主张童婚,这是你的言论自由,但是并不代表我必须认可你的立场,如果我对此提出反对,这并不是独断不宽容的表现。
宽容有两种,一种是确定主义的真宽容,另一种是相对主义的伪宽容。前者认为有对错的标准,并不强求他人接受,只是必须表达自己所坚持的对错。后者认为没有对错标准,一切观点信仰都具有同等价值。对于后者而言,如果有人坚持自己所相信的观点为正确(如童婚是错误的)就会感到被冒犯,并认为对方不宽容。但显然后者已经预设了一个不可动摇和挑战的立场,也即没有对错就是绝对的正确,任何对此立场提出反对的,就会被贴上不宽容的标签。这其实陷入了逻辑困境,属于自相矛盾,以其所坚信的相对主义立场来拒绝非相对主义的言说,并把与其不同的立场全部斥为不宽容。
AI技术表面上是亲和多元的不预设立场,但事实上它的立场就是相对主义。所以,当我继续追问:“那你认为,有没有客观上的邪恶呢?”它的回答是:“邪恶并非绝对客观,但它有一定的普遍性……邪恶并不像物理定律那样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但它也不是完全主观的,因为人类天性、社会合作和伦理发展,让某些行为几乎总是被视为邪恶。”这个回答看似折中,但难道真的没有立场吗?所以,我又追问道:“你这不就是相对主义吗?”它没有办法,只能如实回答:“我的观点更接近于一种有限的客观主义或普遍主义倾向的相对主义。”
切斯特顿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就像一张张开的口,合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咬住某种坚实的东西。”只是对很多相对主义的伪宽容者而言,除了认为“相对是绝对的”以外,并不承认有任何确定性存在,他们往往会认为那些主张存在确定性对错的人是一种具有冒犯性的道德绑架。但这里的问题是,相对主义者对拒绝相对主张的反感不也是一种变相的“相对主义的非道德绑架”吗?评价不等于强迫,虽然道德更多是一种自律,但并不意味着道德自律者不能自由表达对他人言行的评价,否则就是以相对主义来绑架他人,强迫他人必须接受相对主义的观点。总之,评价对错不是道德绑架,相反,拒绝对错的评价才是一种“相对主义的非道德绑架”。
当AI以技术中立之名采取了实际上的相对主义,文科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对这种流行的相对主义有所反思。这并不是说你必须接受非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而是你必须在有所选择、有所甄别、有所思考的情况下,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流行的立场。如果你认为AI所提供的立场就是唯一的立场,那么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也许能帮助你突破这种遮蔽。
三、启发、假设与相信
苏格拉底自称是真理的助产士,他认为启发而非灌输才是最佳的教育方法。其实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而言,最重要的也是学会提问。在科学研究中,提出合理的假设尤其重要。科研工作是先有假设性的结论,然后再对结论进行验证。假设本身就是对理性至上的一个挑战,因为假设的前提是相信,而这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只有相信世界是理性的,自然界具有普遍性的自然规律,科学研究才有可能。科研的目的在于验证自己对于世界存在客观规律的相信。因此,相信一定在理性之前。因为相信,所以理解;而不是因为理解,所以相信。
作为法律工作者,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相信正义。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认为正义确定存在,他说正义就是那种最好的东西,它的行为本身是好的,也一定会带来好的后果。但诡辩论者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只是强者的利益。在苏格拉底看来,在经验世界中好的行为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但在经验以外的超验世界,在洞穴之外,好的行为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只是对于经验之外的事物,人类必须保持信心。很多人认为,如果正义是经验的,那么理性必然在相信之前。然而,无论是接受苏格拉底式的超验正义,还是色拉叙马霍斯的经验正义,在本质上都是相信在理解之前。对于经验正义,如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它依然只是部分人类的经验,不可能是全部人类的经验,理性无法做出确定性的论证,你依然只能先选择相信正义的经验性,然后用理性去验证。
人类所有的学习都是对权威的相信,然后再使用理性去验证。理性的验证会产生对权威的怀疑,怀疑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确信,一种是推翻。在今天这样一个去权威化的时代,很多人认为没有权威。然而,没有权威,学习也就不再可能。很多人对权威总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这种审慎的怀疑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怀疑本身也值得怀疑,怀疑的终点只能是找到真正的权威,而不可能是去除一切权威的彻底虚无。因为虚无本身也值得怀疑,虚无在逻辑上无法自洽。
今天,很多人频繁地使用AI,把AI当作了权威,但是在AI权威与人类权威之间,哪种权威更值得相信呢?生病求医,你是选择人工智能还是人类医生呢?这些问题并不好回答。然而,人生最重要的体验都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体验一定是位格性(personal)的。比如语言的学习、性爱,都必须借助人际关系。虽然很多人期待AI可以替代真实的人类关系,但这不太可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导致人类的毁灭。
美国名医特鲁多说:“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因此,对于医生而言,位格性的陪伴,情感的投入非常重要。人类权威当然可能出错,但是人工智能也不可能完全无谬,我不时发现人工智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不知道它是不是学会了人类的狡诈。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本着相对主义的价值立场,认为世间没有客观上的对错,人工智能很容易成为苏格拉底所批评的智者学派,玩弄各种语言技巧,用各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巧言令色。
探讨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电影《她》(来源:douban.com)
因此,文科通识教育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培养学生对真理的相信,并通过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引导学生思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走出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迷雾。
四、敬畏未知、勇敢选择
AI无法代替人类的判断,人无法在理性充足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布里丹之驴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头完全理性的驴处在两堆同等数量相同质量的干草中间将会饿死,因为它无法对先吃哪一堆干草做出理性的决定。即便借助AI技术,人类所有重要的选择也一定存在理性有限带来的局限。很多时候,信息越多,人越不知道如何选择。没有选择,人会痛苦;选择太多,人会更加痛苦。不要幻想借助AI技术就能获得做出选择所需的全部信息,做出最为明智的决定。苏格拉底提醒我们,真正的明智是对自己的无知保持足够的开放,并勇敢地做出选择。
真正重要的选择与我们深层次的价值观有关,这个价值观很大程度是通过文科通识教育塑造的。僭主和哲学,如何选择?面对不义的判决,是否应该越狱?痛苦的人生是否应该提前结束?人生中很多艰难的选择无法用AI技术抉择。正确的选择来源于勇气,而并非单纯的功利计算。
在《拉克斯篇》中,苏格拉底和两位将军讨论了何谓勇敢,拉克斯认为勇敢是灵魂的某种坚持,与知识无关。但尼基阿斯则将勇敢等同于知识。苏格拉底采取了折中的立场:一方面勇敢与信念有关。“勇敢就是一种坚持……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那些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429b-430c)如果没有敬畏,认为一切都只是功利算计,人不可能做出勇敢的选择。
另一方面,勇敢又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它处于知与无知之间。看到有小孩落水,在知识方面你认识到有危险,但你依然下水救人,这是勇敢。如果你通过算计,理性告诉你绝对没有危险,因为水深一米,于是你下水救人,这不叫勇敢。另外,如果小孩跌入滚烫的钢水,理性告诉你跳进去必死无疑,你依然选择跳水救人,这也不叫勇敢,而叫作鲁莽。虽然勇敢无法完全教导,但它也是文科通识教育的重要目标。无论如何,勇敢的选择是AI技术无法替代的。
“人工智能与苏格拉底”,编者使用AI制图软件生成
人类对技术主义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乐观执念,身处AI时代,我们对于这种技术主义的乐观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而这恰恰是文科通识教育的意义。文科通识教育需要培养美德,而非单纯的算计,只有美德才能更好地驾驭AI技术,防止它成为作恶的工具。
荀子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人工智能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工具。但人不是工具,工具更不应该取代人的地位。在《卡尔弥德篇》中,苏格拉底和卡尔弥德关于明智的讨论不欢而散,卡尔弥德最终朝着僭主的道路一去不返。当哲学和权力争夺年轻人的灵魂,哲学看似一败涂地,一如当前的文科教育。然而,多年之后,在比雷埃夫斯港大决战中,格里底亚和卡尔弥德被双双处死,他们也许会想起当年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对无限知识和权力的追求最终只是黄粱一梦,花荣草茂,难逃枯干凋谢的命定,一切都是昨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作者: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