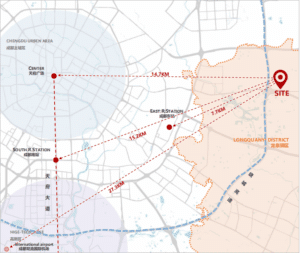“学了蛤蟆功,打跑资本家”
【来源:虎嗅网】
都市神话是时代的哈哈镜。
打倒资本家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神话,也是都市神话文学母题“roughneck – 粗野工人”的新版本。
如今,中国抖音为这种神话提供了更新补丁:
学习蛤蟆功打倒资本家。
现在你在社交平台上,检索蛤蟆功、螳螂拳、资本家这样的字样,就会发现一条崭新的、符合时代情绪的流量赛道,我愿将之总结为:
生物拟态在资本批判上的研究与实践。
乍一看,他们的作品各有各的扭曲和抽象,但在创作内核里有着极为相似的趋同性。
这种趋同性首先体现在文案结构上,要素由年轻、通透感、鄙视感、学武术和战争叙事组成,具体表现是这样:
“xx岁,看透社会,坚决n+1(即1必要条件,n次要条件):n可以由打光棍儿、不贷款买车买房组成,1即坚决不给资本家打工,躲进深山学武术,意欲干翻资本家。”
这种视频虽然看上去都很劣质,选取的人物形象、场地设计和武功招式都很精巧。
在人物方面,创作者刻意通过劣质面料(或衣不遮体)来打造表演者生活不如意的状态,有些特意强调大学生身份的视频,还会用证明昔日荣耀墙面奖状和悲惨现状来进一步强调荒诞性。
在场地设计方面,创作团队刻意选择那些野地寒舍,不是大野地,就是水泥地出租屋,这种操作不但可以跟人物形象形成互文,也能加强一种神秘的避世感,为学习到神秘武术的剧情,埋下伏笔。
武术招式的选用就更有意思了,选的都是民间武术,特点都是以小搏大。
螳螂拳在官修史料里不见踪影,但在民间口述史和口传武术谱牒中,被称为民间好拳,大概意思就是不是花拳绣腿的皇家武艺,而是实战性强的好使杀招。
在1928年南京国术馆成立后,修编的《山东国术概况》里,编辑就特别提到:
“螳螂拳技,灵动急速,尤适近身缠斗,多为乡团练武,镖师雇护之需。“
相比较螳螂拳,蛤蟆功则不入流,在小说、民间传说和武侠游戏里,总是跟拙劣艺人、骗子和不入流武者挂钩。
在官方史料里蛤蟆功亦不见其踪,只在民间笔记杂谈才能发现。最早提到蛤蟆功的笔记,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杂抄本《奇门秘籍小录》将之称为:小道也,意思就是难登大雅之堂。
1990年代初,青岛地方武术研究会组织过一次针对老拳师的采风项目,据民间武术爱好者回忆,在访谈中青岛螳螂拳传人李昆山说:
“小时候在码头上,看见过卖艺的苦力有练鼓腹硬功者,练得小腹鼓如鼓,称为‘蛤蟆气’。练成后可在近身时以腹部冲撞对手,略有实用。但此类功法多属江湖奇技,非正门武艺。”
仙剑奇侠传里的蛤蟆山
选择这两种民间武术技法作为推翻资本家的设计,突出了视频强调的草根感和以小博大的野心。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份降配版的新时代爽文,走的就是一个幻想性的复仇高潮路线,精准踩中了时代情绪的前列腺,用10几秒的短视频,把弱势群体,逆境打磨,奇遇加持,翻身逆转几个关键要素都集齐了。
符合时代情绪,但并不新鲜。
在国际民俗学上,学蛤蟆功打败资本家的叙事被称作是“Revenge of the Humiliated – 被侮辱者的复仇”在全球各地都不罕有。
在布鲁范克的《都市传说百科全书》中就记录了一个西方非常流行的类似故事,名为“钻井工人的复仇”大概意思是:
“矿井工人在工作中,不小心把工具掉进了刚钻好的深井里,再经过千辛万苦捞出来之后,却被领导解雇,于是愤怒的矿工把刚捞上来的工具又扔回了矿井,并说了一句:好吧,那我也不需要这把工具了。”
受侮者的复仇叙事,从来不会成为真实的历史。
按照故事形态学的说法,它们只是某种乌托邦式的愿望,这种故事的流行是对社会压迫的本能反应,也是对朴素正义的文化向往,更是对小人物逆袭的普世渴望——这种情绪既包含惩恶扬善,也有对于努力就能改命的渴望。
取材于江户恐怖袭击事件的《忠臣藏》之所以能成为日本的民族史诗,就是因为它击中了被侮者叙事,至于戏码背后的真实如何,无人在意
无论你的品味如何,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互联网上最流行的新兴内容,总能精准映照出社会的心理现状。
从“正道的光”到“听我说谢谢你”,短视频早已把社会的水有多深探得一清二楚。阿Q最爱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今天,中文短视频里又兴起了练蛤蟆功、打螳螂拳、打跑资本家。这场景变化,标志着近两年职场心态已经从佛系,滑向了另一种情绪波段。
虽然文本上已经升级到了行动层面——练武术,但现实是他们在算法中又轻盈又无效,与其说是一场反抗,不如说是一次逃亡式演出;每一拳都不是打出去的,而是演给世界看的,也是挣流量的。
一百年过去了,武器从钢鞭变成了肉身,敌人从地主变成了资本家,而泥潭中的人,从未停止对胜利幻觉的复吸。
这种成瘾性,在于它能编织出一个线性发展的世界,就像魂斗罗: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发展都是可以预期的,一切敌人都是明确的,一切正义都是能通过数学公式化的操作实现的,只要忍耐,就一定能争取到更大的胜利。
但遗憾的是,没有这么简单的世界存在过。
有一种说法“手执钢鞭将你打”这句词,出自元末明初出现的绍剧《龙虎斗》中呼延赞鞭打宋太祖赵匡胤的戏码,也是一种民间神话,投射了当时老百姓对英雄的向往,过瘾就完了
繡像南北宋志傳,1892
都市神话和都市传说最大的区别在于,都市传说表现的是阶段性的恐慌,是一次性的恐怖故事,而都市神话则是一种持续性的认知叙事。
它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真的能改变命运,而在于它让命运听起来像是能被改变。如果你在网上冲浪,就会对这点有更深的理解。
互联网遍布讲经人,人们擅长坐而论道,擅长语言攻击,这就像是1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居民一样,天天聊神学,辩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一个意志还是两个,但对近处奥斯曼的炮声充耳不闻。
辩题可以随时更换,方向可以随意切换,从国际局势到职场恨意,张口就来。聊的都是自己无力触碰的废墟,好像说得越多,就越能给无力的伤口做金缮。
光明会、昂撒、犹太资本都是都市神话
天花板之下,存在真正的资本家吗?打跑了想象的恶人,世界真的就能好吗?如果敌人是虚无的,目标就是失焦的,实践也就无从谈起。
正因此,当现在人们对于义理的向往正变成一个抽象的笑话,一个悬浮的概念,未来人或许只能说:这帮人只是以它为名,打发了一段无聊时间。
可他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领悟,所谓的抽象,不过是无力感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扭曲镜像,他不是行动的宣言,而是镇痛的迷幻药。
至于未来,答案在风中飘。
文章标题:“学了蛤蟆功,打跑资本家”
文章链接:
阅读原文:“学了蛤蟆功,打跑资本家”_虎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