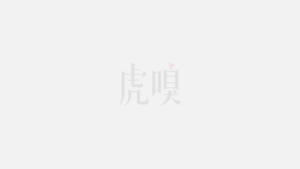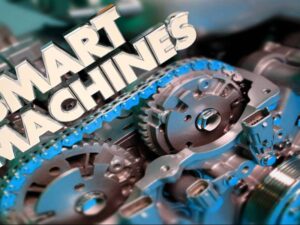我在中亚做游学,年入70万,还水了个博士学历
【来源:虎嗅网】
一
昨天,我回到塔什干,酒店扔下行李,随手发了个朋友圈,不到五分钟,一个久违的头像跳了出来。
阿文,旅界创立初期的第一批记者,当年稿子写得飞快,头发掉得更快,后来一走了之,说是去中亚“闯荡”,从此杳无音信。
择日不如撞日,阿文想约我叙叙旧。
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在市中心一家露天烤肉餐厅碰头,他一出现就给我整乐了,穿一件短袖Polo衫,胳膊晒得黝黑发亮,手机上还挂着个学生证夹,像极了来实习的中介老师。
在中亚摸爬滚打七八年,阿文活力不减当年,他说自己现在专做两件事:一是当留学中介,操作中国人来中亚读书,二是开始筹备乌兹别克斯坦的地接旅行社,决心把中亚旅游生意做大做强。
看他混得不错,我们很快聊到他的第一桶金,阿文神秘一笑,称正是帮中国人在中亚刷学历。
他说,熙哥,你知道吗?咱们这边QS世界大学排名150左右的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一年制硕士学费就3-4万人民币,然后住宿、吃饭加上学费,一年七八万元人民币基本全包,是不是特划算?
我寻思便宜是真便宜,可谁来读啊?
阿文说这你就不懂了,来读的人多了去了,“国内小地方体制内、医生、老师,一些需要学历评职称的;还有一些奔着国内大城市积分落户、人才引进政策的,最极端的是已经有编制的人,用这个学历可以免笔试。”
我好奇,“那他们真的上课吗?”
阿文立刻说,哥,你这个问的好,“他们读的是一年制硕士,实际上七八个月就完事,来这待几个月,剩下线上搞定,我们还提供住宿、翻译、注册一条龙服务。”
他说,这两年哈国政府在推进经济改革,对外来留学生极为欢迎,尤其是中国市场,他的客户里,几乎没有真正关心学术的,但每个人都清楚这张学历能“落地”在哪。
阿文怕我不懂,还努力解释,称要是像他这种中俄边境小地方出来的人,在老家再有点关系,拿到一个高学历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直接人中龙凤了。
“比如说走这个免笔试的人才引进,再比如说评个职称,我们这个学历可是太有用了。”
这些年,阿文的中国客户群体日渐稳定。
他回忆自己去年经手来读哈萨克斯坦硕士、博士的中国学生已经有30多个了,扣掉一些打点成本和实际运营开支,一年还能剩70多万人民币利润。
“这就不错了,有时候我们还能整点丝绸之路高校联盟青年领袖这样的国家级荣誉,是可以写进档案里那种,那也是不愁中国客户的,算是赚外快啦。”
二
听阿文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近期关于北京协和医学院“4+4”学制的那场大讨论。
近期这段时间,网友一直在质疑2020级“4+4”试点班的金某木其博士论文相比其他博士论文篇幅过短,正文仅有12页的内容。
阿文听我说完,笑了,那还不是她傻?你让她来中亚念医科,能查出来毛病算我输。
看阿文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挺佩服,但还是有些不理解,就问他,“留学生意这么一本万利,为啥还要搞旅游呢?”
说到这,阿文眼神多少有点黯淡了,他说“留学生意香是香,但窗口期快没了。”
他认为原因是,“现在越来越多国内中介进来,把中亚这边大学都包圆了,以后学生只能通过大机构报,像我这种个体户,越来越难混啦……”
风口急转,阿文决定做两手准备,“一边还能接几单老客户留学单,一边做中国人来中亚旅游。”
他说这是从留学转到游学,让自己的客户边游边学,玩着就把毕业证拿了,情绪价值给他们拉满。
至于灵感,阿文回忆去年有几个客户过来上课,每到周末、节假日就让他带团旅游。
今年,他发现这需求比预期还强,“来中亚上课顺便玩一圈”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来乌兹别克斯坦旅游的需求最大。
阿文是看到风头会立刻转舵的人,于是开始筹备中亚地接业务,客户除了留学生还有不少潜在客户,“大家都是托我来落地的,信任感比普通团强,比起散客,我的成本低、转化率高。”
他分析这两年中亚旅游在国内火爆的原因,“说白了,中国人对中亚还是好奇的,尤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免签之后,这边成了新蓝海。”
再说到中亚的旅游资源,阿文就更兴奋了。
在他看来,乌兹别克斯坦是人文旅游的胜地,哈萨克斯坦胜在自然风光,两者互补性很强。
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四柱神学院/旅界实拍
这一点,作为疫情前就深度玩过哈萨克斯坦,现在人又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游客,我深表赞同。
哈萨克斯坦这边有雪山、大漠、峡谷、湖泊,堪称“免票、人少版的新疆”,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又到处都是拍照的绝佳背景,适合一生爱出片的中国女人。”
大阿拉木图湖/旅界实拍
我问阿文,“所以你想吃定这波中国流量了?”
阿文点点头,他说“我觉得时间窗口还剩两三年。再晚就卷起来了,而且,现在国内飞塔什干航班也多了,成都、广州都有,搞不好就能赶上中亚旅游的红利前夜。”
他望着窗外的夜色,语气突然正经了一点,“和留学一样,我想干三年,再不干就真晚了。”
三
撸到最后一串,阿文突然想起了什么:“哥,其实我这几年,也顺手水了个中亚博士。”
我顿了一下,差点没噎着:“你说你?博士?”
阿文认真的点点头,他说,“熙哥,真博士,每年四五个月,三年就能搞定,反正我也在陪客户上课、翻译材料,顺带着把自己资料也提交上去了。”
我忍不住乐了:“你这叫陪太子读书,结果自己当了国王。”
阿文哈哈一笑,他说,“说实话,也是为了后路做铺垫嘛,万一中亚这块就真支棱不起来,咱还可以回家呀。”
他跟我解释说,这两年哈萨克、乌兹别克正在做经济改革,整个中亚商业机会明显变多了,尤其对中国人很友好,所以也越来越卷……
“华商也越来越多了,啥都能干,旅游、教育、装修、翻译,甚至物流每门生意背后都有无数国人在抢食……”
他把茶一饮而尽,语气认真了几分:“所以我得两手准备,一边看旅游能不能搞起来,一边把帮国人刷学历当收尾做个一两年。如果都搞不成,我老家还有个事业编岗位是停薪留职状态,所以这学历你懂……”
我沉默了几秒,想起初见阿文时,他还是个刚毕业,一心想在北京闯出名堂的毛头小子,岁月是把杀猪刀,他被社会毒打过,也在中亚收获了人生第一桶金,时代沉浮之下,更多了一些足以在异域谋身立命的城府。
或许,每一个在中亚打拼的中国人背后都藏着几层不为人知的故事,背后的酸甜苦辣只有本人最清楚。
塔什干City Park夜晚音乐喷泉/旅界实拍
就像阿文坚定地说自己不是投机,是选择在大势来临前,站在有利位置等风。
我信了。
白天燥热难捱的塔什干,夜晚泛起阵阵凉意,送我回酒店途中,阿文看着路边呼啸而过的出租车,忽然说:“哥,我是认真的,这里(中亚)是块好地方,不怕你写,就怕中国人来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