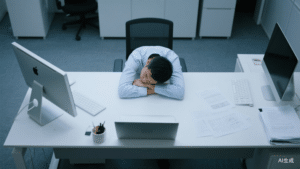“软实力”理论奠基者逝世,在美国软实力危机时
【来源:虎嗅网】
国际政治的泰斗、哈佛肯尼迪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5月6日去世,享年88岁。没有国际政治学生能够避开这位老爷子,我也一样。
软实力衰退与否,有不同视角
作为软实力概念的奠基者,他的离开正值一个微妙的时刻——美国的国际软实力似乎正在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从内部被破坏。
但要注意,视角不同,对软实力的判读会完全不同。
对于老特的MAGA基本盘来说,美国的软实力可能正如日中天、万国来朝。对于这群人而言,原先有强大的软实力但毫不运用,就像段誉有着震古烁今的内力储备但不知如何使用,是彻头彻尾的浪费,直到老特上台,犹如萧峰战神附体,把80%的实力打出了150%的威力,是真实软实力的大提升。
这也是老特班子的内宣口径。
但在国关学者和其他国家来看,尽管约瑟夫·奈在历史上曾多次反思过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否行将衰落,他很可能从来没像今天一样,强烈地感受到下坡路的威胁如此迫在眉睫。在去世前,在老特的上一任期,他的看法可以用他自己的语言概括:“川普担任总统四年,对我、对美国和对世界来说都很煎熬。他很难相处,因为他对国际事务的情境智力很低,而且他高度自恋,限制了他的情绪智力。”
一个难相处的人不一定是坏的共事者。有的领导很难相处,对下要求严格、挑剔,但你知道他会让你提升进步,并且分利益的时候公平甚至大方,你不太会有怨言。但如果这个领导反复无常、苛刻且理由不能服众,很多时候让人觉得只是为了挑刺而挑刺,以批评来立威,你不会敬佩,也不会想追随。
对外和对内不在自己阵营的人,老特无疑都是那个“难相处”的人。如果对内还有整体国力提升这样的业绩可以交待,对外几乎很难让人心生好感,因为他似乎也并不想带着国际体系获得什么共同利益,核心的目标都是蛋糕的再分配,换言之就是他要的更多。这不会让跟随者产生向往之心,只会造就屈服者。
这和2018年那次看起来完全不同——当时的结果是罕见而意外的三赢:美国通胀没上去,多收了关税;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反而上升、科技自主化获得了大量投资和扶持;新兴市场获得了FDI投资和承接了部分供应链转移。
但输家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当时声音不响。MAGA群体发现美国财政刺激下贸易逆差更大了,制造业转出更积极,中美的企业家即使联手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工人也不愿意分给自己一杯羹;物价上涨了,但自己的工资收入落后,也没享受到股票上涨的红利。
所以你看美国国会某个委员会的名单,除了佛罗里达这个老特大本营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受中国制造冲击的州分:
美国自己的研究中,加州(电子产品生产转移、洛杉矶服装业转移以及中国对农产品进口的关税)、伊利诺伊(曾经的机械制造业大州)、密歇根(底特律、汽车制造)、俄亥俄(克利夫兰等金属加工、钢铁制造带)都是深受冲击的。
像加州体量足够大、多样化,转型了,以至于今天经常将被抛下车的人遗忘,但这些群体一直存在。
我自己在芝加哥生活学习过4年,也公路旅行途经过克利夫兰、底特律,对城市衰败的结果触目惊心,从一人进工厂全家不愁生活,到逐渐萧条衰落,是很难接受的现实,而且重要的是他们手里有选票。
美国永远认为自己在衰落,但哪次会不一样?
回到奈本身,上两次学界质疑美国衰落的时间点,分别是1990年和2004年,即苏联解体前后和911后。奈实际上是从软实力的角度对这些质疑做出回应,认为美国的软实力仍然强大。
西方学界乃至民众常有自身衰落论,反复出现。这可能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表现,也可能有历史传承。似乎总有强盛、凝聚、崛起的东方(或者敌对力量)在构成威胁,而自身是散漫的、弱小的,要到最后一刻才集聚力量反败为胜。不知道这是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蒙古西征、一二战留下的后遗症,还是托尔金魔戒等文学塑造的一脉相承。
从今天反思来看,90年代,伴随着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美国实际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在苏联垮台后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国。而911加上之后的金融危机也并未损伤美国的元气——但确实这些事件都给了中国崛起的绝佳战略窗口。
在那个时间点质疑美国霸权的衰落,其实很需要勇气,但也符合学者居安思危的心态。当最大的敌人倒台后,自己所领导的军事-经济集团是否有瓦解的风险?如果安全保障和军事防线的重要性剧降,那美国用什么方式确保自己的领导权?
如约瑟夫所预料,领导力的基础是多元化的。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美国的价值观、提倡的经贸合作方式、对科技、制度理性、经济效率的追求,成为了全球共识。
似乎谁追随这套经济理性,谁就能率先进入现代性的门槛。
即使深陷腐败、贫困,或者国民性随遇而安不思进取的国家,也会在潜意识中知道什么是好的,也会在口头上高举支持市场化、民主化的大旗。
就像电影里坏人失忆后,第一反应本能是想做回好人。
中国加入美国体系,实际上成就了美国体系的高峰
回头来看,在“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之后,中国的入世和对美国市场经济(其实和欧洲的市场经济非常不一样,在诸多细节上)很多理念的追随学习,乃至反超,成为了推动这个体系登峰造极的催化剂。中国的崛起一度并非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反而是一种助长,向世人证明,即使是这样庞大的13亿人口,只要能学习美国模式,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和供应链分工,也能脱贫致富。
但也正是神速的进步,快速拉近了双方的距离。让美国突然醒悟到这套制度对中国的帮助反而更大,以至于内部一部分心怀不满的人群要撕碎制度本身。
软实力似乎不再重要,因为世界进入了硬实力掰手腕的时候。
但如果将软实力理解为除了军事硬实力以外的权利,老特又似乎在全力发挥软实力,用经贸、技术、货币等一切手段让对方屈服。
认知差别的根源在于什么是软实力的基础。如果仅依靠综合实力来威压,那老特确实把美国的软实力发挥到了透支超频的水平,提升到了意外之喜的高度。狂热的“爱国者”们会击节赞叹,而不考虑反噬。
如果将软实力的基础理解为合法性,让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地跟随美国、做美国想让他们做的事情,那老特的行为是完全背道而驰。
正如约瑟夫·奈写过:“如果一个国家能让自己的权力在他人眼中显得合法,那么它在实现自己的愿望时遇到的阻力就会减少。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人就会更愿意追随。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准则,那么它就可以免于很多被迫改变。如果它能支持一些机构,使其他国家愿意以主导国喜欢的方式引导或限制它们的活动,那么它就可能免于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行使强制力或硬实力。”
老特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相反:让自己在自己建立的体系中显得不合法,也不合理(但对于自己的选民来说非常合理,扬眉吐气);对国际社会放弃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在乎是否追随,而在乎是否屈服。主动绕过这些自己设立并占有主导权的国际组织,一对一找国家谈判。
而奈提出软实力的最初背景,就是为了反驳当时流行的“美国衰落论”,指出美国的实力不仅在于军事和经济力量,还在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的吸引力这些无形资产
20年来,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反复登台,正如世界的映射
这20年间国际体系的跌宕起伏,正好是国际关系学界中,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学者交替轮换占上风。
在国际关系101时,我的入门读物是现实主义的那一套书。这是出发点、原点,而非奈的新自由主义。
我依然记得读的第一本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必备读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精简的假设、回归人性本初的状态和绝妙的推理,丝丝入扣。
基本的假设:国际政治是一场无政府结构,没有一个凌驾于全球的权威能够决断。所有的国家都以存在和安全为优先考虑,构成了现代现实主义的基础。
简洁清晰,自证。
就像赵鼎新老师说的,越是接近于数学公理的社会学理论,越有生命力,因为你无法将其击败,只能抛出大量的例子去反证它,并成全它的高度。
现实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体系。最早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就已经悟出了这样的道理,甚至今天还演绎出科幻界的“黑暗森林”理论。
从一战到冷战,现实主义大行其道。
冷战结束后,长久的和平和美国主导体系的繁荣,乃至中美蜜月期,大家一度相信软实力和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认为很多共同的目标、软性的交融、相互的模仿学习会带来长久的和平和国家之间的协作。甚至还有“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这样的理论。
奥巴马和他给中国的十年签证就是最好的注脚,这可比申根大方多了。我们很多人至今仍在享受那个时代的便利。
但自2018年贸易战以后,中美关系随着国力的接近开始急剧恶化,经过了疫情的物理间隔后,双方进入了第二轮贸易战,彻底的官方敌对姿态。
钟摆又回到了现实主义。似乎都在验证了我们学校另一位知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理论——《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国之间必有一战。
我们开始忽视、看低那些软实力和文化制度属性上的交融,而重新回到了最基本的原点——安全和建立在硬实力上的权力。
米尔斯海默出乎意料地倒是非常受中国欢迎的学者,他和闫教授在清华的多次互动,会场挤得水泄不通。
中国对美国文化产品的认同度在下降
因为其实我们也打心眼里认同这一套。90年代的浪漫主义已经过去了,看美国电影听美国音乐的时代过去了。说句实话,今天美国文化产品的感召力真的在下降——我深度怀疑是因为对现代性和理性的背离和理解分歧。
例如,科幻对未来的想象反而脱离了现实,无论是外太空还在大规模冲锋和刀战,都不如真的基建狂魔拍的饱和救援、大工业建设来的切实际,总有点披着外太空的中古歌剧味。
对于更理解制造业、工业体系的国民来说,总觉得饱和轰炸、远程无人机群、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更符合对未来的想象。
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也出现分歧,例如警民关系、邻里关系,很多国人在电影里看到的自我保卫,人人为自己和高度融合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无法引起共鸣,更不能理解cop随手拔枪就射有着高度美国特色的原因。社会形态分化也是造成吸引力下降的原因。
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但很可惜,约瑟夫·奈老爷子看不到了。他在最后见证的是现实主义的抬头和美国本身对软实力的背离,不知道他心里会有何感想。
这可能是全球性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主义似乎深埋在中国每个人骨子里。我们也开始认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不去深究发动一场战争的正义性。我们将其自圆其说,是被迫的,是对东扩的预先反制。
道义在今天更重要,也是我们摆脱外交围堵的机会
但软实力都不再重要了吗?我并不认为如此。软实力的两个基础:工具理性 和 道义,同样重要。我们有时候过于抬高前者,但已经吃过了亏。
其实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应该有深刻的体验。更符合道义的事情,做得明显更顺,朋友更多,即使强权要利用实力碾压,也能找到盟友。
在没有最高仲裁者的国际局势里面,有的时候,道义反而是实力以外最坚实的盾牌。道义从经济本质来看,可能是对全局最优的追求,是多次博弈后的均衡结果,是长期博弈后利人也终归利己、制度摩擦最小的安排。但确实不一定是短期内对自己最优的安排。
就像刘玄德以道义对抗曹孟德的实力。
当俄乌陷入僵持,不再成为主要议题后,我们在贸易战中的道义定位,就明显更顺畅。
这可能反而是我们在软实力方面重新拿回上手的关键转机。
最后,IMF一篇论文对中英软实力的指数衡量,目前美国仍然领先全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嬉笑创客,作者: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