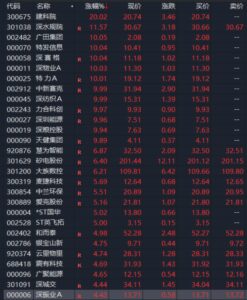当妈妈说“不用可怜妈妈”,就是对女儿最好的托举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 (ID:jdxl2000),作者:慌慌,责编:罗文,题图来自:AI生成
在常见的东亚母女叙事中,母爱常与牺牲绑定,以“为你好”的名义对女儿进行隐秘控制与情感索取。如果父亲的角色长期缺席,母亲容易将对伴侣的情感需求直接转向女儿,让女儿在情感上反哺自己。
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女儿,往往习惯于“讨好母亲”,忽视自我需求,当母女之间形成这类不健康的共生依赖关系,会极大地绞杀女儿的独立性,也会造成关系中长期的失衡与越界。
今年让许多人泣不成声的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以下简称《苦尽柑来》)给出了一种全新的母女关系范本:在三代母女的叙事中,它勾勒了一种母亲以女儿实现自由、享受人生为前提的托举。
第一代母亲光礼在济州岛以潜水捕捞的海女工作为生,她常年操劳,却对女儿说:“爱纯,可怜的是我,不是你,不要退缩,要尽情享受自己的人生”。
有别于以爱为名的索取,这是一种坚定地将女儿的人生与自己的苦难划清界限,要女儿往前一步的母爱。
当母亲的托举不再是一种自我牺牲式的情感绑架,母女关系可能呈现出什么模样?女儿们又可以如何践行自己的人生?《苦尽柑来》给出了温柔而有力的答案。
今天是母亲节,这篇文章写给尽力托举女儿的母亲们,也写给一边爱着母亲,一边努力成为自己的女儿们。
一、当母亲成为力量来源
在父权制社会,家庭中的大部分权力都由父亲转交给儿子,但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却发生了中断。女儿在社会化初期缺乏女性权威,很难发展出对女性身份的认同。
不同于许多年代剧囿于男性主导的家庭结构,将父亲或男性长辈置于叙事中心,《苦尽柑来》自始至终都将母亲的形象置于叙事核心。
爱纯的母亲光礼、爱纯本人,以及她的女儿金明之间构成一条清晰的代际传承线索:母亲托举女儿,女儿承继母亲的精神与生活智慧。
光礼在爱纯父亲去世后改嫁,将年幼的爱纯留在家境较为宽裕的叔叔家生活。当她得知爱纯在叔叔家甚至吃不上一条黄鱼时,她掀翻了爱纯叔叔家的饭桌,将爱纯带走,并告诉第二任丈夫,如果你对她不好,那么被赶出去的不是我的女儿,而是你。
“她是我的女儿”——不论是光礼还是后来的爱纯都曾愤怒地喊出这句话,其背后含义是“我的女儿值得最好的,她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身为母亲的她们会始终以女儿的感受和权益为先,捍卫女儿的边界和未来的可能性。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海因茨·胡科特曾经提出的“自体客体”概念(自体是你思想世界中的自己,狭义的自体客体首先指的是父母),妈妈是女儿的自体客体,孩子从婴儿期从母亲的眼中体验到快乐与骄傲的闪光便是一种镜像效应——有助于形成自我概念。而母亲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女儿如何看待自己及周遭的世界。
正如“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译者陈英所说,唯有母亲的权威被重新树立,女儿才能更顺利地完成自我赋权,从母女关系中获得力量。
这部剧里很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与以资源与权力为核心的男性传承不同,在赋予母亲核心地位的《苦尽柑来》中,女儿所传承的是母亲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生存智慧。
过去,母亲往往扮演父权家庭结构中的辅助性角色。然而,剧中重新确立了母亲的权威,爱纯以“光礼女儿”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重要的男性角色也被塑造为女性意志的支持者。自小就跟在爱纯身边的梁宽植曾说自己的梦想是做第一先生。
光礼在29岁时早早患病去世,但她坚实的母爱是爱纯生命的底色,也在爱纯之后的人生中不断回响。当爱纯与丈夫宽植陷入经济困顿时,奶奶因光礼临终前的托付而出资为爱纯夫妇买了一艘渔船,这成为爱纯一家重新生活的起点。
当爱纯因意外丧子而悲痛不已时,光礼在梦中告诉她:“如果有一天生活变得无比艰难,你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无论如何,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拼命挥动胳膊和腿,你就能穿过黑暗的海水,看到天光,重新呼吸”,爱纯从海女的生存智慧中汲取勇气,穿越丧子的暗夜。
二、“不要可怜妈妈”
《苦尽柑来》的动人之处,正是这份在贫乏与束缚中仍努力托举下一代的力量感。
不论是光礼还是爱纯,她们即便在匮乏的物质环境下,也会将女儿的感受与意愿置于首要位置,全力托举女儿,给予女儿自我实现的可能。
生存焦虑没有让她们失去爱的能力。她们没有对女儿进行情感绑架。这在东亚的现实和文学影视作品中都很稀缺。
更常见的是把女儿当老公的妈妈们。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Susan Forward)在《情感勒索》中指出,情感勒索的本质,是在亲密关系中通过制造内疚、恐惧与责任感,来操纵对方。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母亲与女性的意义是不同的。“女性”身份不被允许的自私和占有欲,在“母亲”身份中无限地被容忍。一切以母爱名义的作为都应该被理解和原谅。因此,母亲会以各种微妙的方式阻止女儿远离,有时这发生在潜意识中,她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4]
第一种方式就是让女儿愧疚。很多母亲因自身的情感匮乏,将子女当作意义的唯一来源。越是自我感薄弱的母亲,越可能将“我养你”、“我为你牺牲”当作情感抓手。
但不论是光礼还是爱纯,她们期待的都是女儿对自己人生的主体性,而非对自己的服从。
《苦尽柑来》以扎实而丰富的日常养育细节,描摹了两代为女儿掀桌的母亲形象。
当婆婆和奶奶试图让金明成为海女时,爱纯同样掀翻了祭桌:“她是我女儿,不是为这个家当牛做马的。”她鼓励金明骑自行车、登船,一次次地打破传统与习俗对女性的限制。当金明以家里的经济条件为由想放弃出国留学时,爱纯卖掉了家中唯一的房子支持她。
“外婆在海里游,妈妈在地上跑,我才能在天上飞”,金明在飞机上泪流满面说出的这句话形象地勾勒出三代母女命运的代际变化,获得了许多年轻女性的共鸣。
这种托举同样包含对女儿的期待,只是不同于对女儿的索取,光礼对爱纯的嘱咐是“不要退缩,尽情享受自己的人生”,当爱纯成为母亲后,也以自身行动践行着她对金明的希冀:“我希望她要什么有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每一件她想做的事都能去做”。
当然,金明和爱纯也有冲突。在大学期间,金明忙于学业与打工,有时会对爱纯的频繁通话与过度关心感到烦躁。
这种冲突呈现的正是女儿的安全依恋状态。
根据依恋理论,个体在安全依恋关系中更容易表达真实情绪而不会担心被抛弃,正因为金明知道母亲不会用爱的撤离作为威胁,她才敢放心地表达自己的不耐烦。
对东亚母女关系有所洞察的日本精神病学家斋藤环指出,母亲通过奉献(受虐式控制),让女儿感应母亲的痛苦,产生负罪感;通过同化,把重新过一次自己的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
但爱纯从来没这么做过。从观众视角看,离开济州岛到首尔上大学的金明确实完成了爱纯年少时被迫中断的梦想,但爱纯从未向金明传达出“续写我的命运”的期待。
晚年爱纯曾对金明说,“不用可怜妈妈,我用自己的方式找到幸福,我的生活中也有阳光……我的人生没有白活”。
这句人生的总结陈词,表达出一位母亲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即便为儿女操劳,她仍旧是人生的主体,她的一生并非全然的牺牲,而是一段真实完整、充满尊严的生命旅程,不需要依赖女儿完成自我价值的确立。
如果母亲经常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就不太会对女儿使用“内疚感控制”这种伤害性的方式。[2]
爱纯正是这样理想的妈妈。
不索取愧疚感的母爱,建立在母亲对自己生活价值的确认之上,这样的母亲同样会鼓励女儿成为独立个体,创造自己的人生。
三、愧疚,不一定是枷锁
“我讨厌妈妈这么穷,更讨厌因为我妈妈才变得这么穷”,金明清楚正是自己的求学掏空了家底,仿佛她自我实现的道路与家庭利益被置于天秤的两端。即便妈妈总会选择她,但她也目睹家庭为此承担的代价。
即便母亲的托举不求回报,女儿也难免将之视为自己必须承担的心理债务。因此,当弟弟银明因担保欠债入狱,家庭财务陷入危机时,金明四处借钱周旋,她情绪激动,质问道:“我怎么可能不去借这笔钱?”金明已经被愧疚感裹挟。
这种愧疚感并非单单源自母亲明确的要求,有时更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内化,认为自己必须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才能回应这份爱意。
金明身上呈现的是东亚语境下的女儿们普遍拥有的一种心理机制:当母亲努力地托举我,我要如何才能回应这种爱?当东亚女儿们被愧疚裹挟,她们有可能会失去自我探索、自我独立的能力。
所谓的“情感勒索”也许不会威胁我们的生命,但会夺走我们非常珍贵的一项资产——自我完整性。自我完整性反映着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感,是我们用以辨别是非的中枢。它反映了我们的身份、信念,我们愿意做什么,有什么原则。[2]
愧疚一定会威胁到自我的完整性吗?这个议题在剧中有了更好的走向:实际上,愧疚并不必然成为女儿自我的枷锁。
当金明面对男友的母亲“做家庭主妇”的要求时,金明不卑不亢地表示她并不比男友差,她有能力,也有自己的职业野心。
在家庭的托举之下,金明秉持着“只要我有尊严地生活,就能让我爸妈以我为荣”的原则,勇敢地在外部世界争取资源和权力,很好地发挥自己人生的主体性。
咨询师王雪岩曾在与“简单心理”的对话中提到,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独立的、有力量的自我是必要的,“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他能逐渐意识到,很大程度上我怎么做,我怎么理解,如何感受这个世界,我就能拥有什么样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来讲,拥有内在力量的金明“成为了一个成年人”。她不仅不懈追求自己的人生,也鼓励母亲爱纯重新开始写诗,继续这个停摆的梦想。
母女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女儿的性别与母亲相同,这种镜像认同让母亲既是榜样又是需要挣脱的对象。当母爱不以牺牲之名进行情感勒索,女儿便能坚定地走向自己的人生,识别出母爱与债务的微妙区别。观众为《苦尽柑来》流的眼泪,或许是一种情感代偿。
没有被好好爱过的女儿,被父母情感勒索过的女儿,能在剧中看到一种坚实的托举和无需偿还的付出。
这是东亚语境下最温柔坚实的母女关系——不勒索的爱、可被感知的支持、和一个被允许自由成长的女儿。
她不需要靠挣脱来成全自我实现。她可以愧疚,但不必被愧疚压垮,愧疚甚至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动力来源。
在这份母女关系里,利他的爱和对自我认可的独立精神可以同时存在。一个母亲不必为了女儿泯灭力量感,女儿也不需要为了偿还母亲而自我憎恨,在承受爱的重量时不失去自我存在的确认。
参考文献:
[1]《危险关系: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2023),斋藤环,上海人民出版社
[2] 《情感勒索》(2018),苏珊·福沃德,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3] 《挣脱母爱的束缚:母女关系中的伤痛与疗愈》(2022),于玲娜,人民邮电出版社
[4] Jianqin, Xu. (2020).”Rereading Klein’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 ”—the evolution of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four generations of Chinese women.”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3, no. 1: 50–59.DOI:0.33212/ppc.v3n1.2020.5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 (ID:jdxl2000),作者:慌慌,责编: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