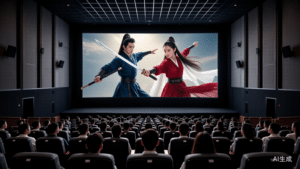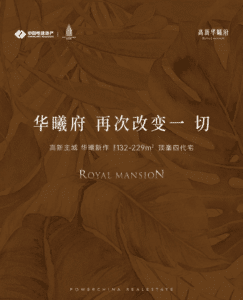政府如何“既出钱又监管”?美国住房援助体系的启示
【来源:虎嗅网】
作为一个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的住房体系高度依赖私有房屋市场,而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住房援助体系(Assisted Housing)占比很低,受益者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7%。由于规模较小,美国的住房援助体系很少被研究者关注,其制度安排也鲜为人知。但实际上,该体系已有近百年历史,其间经历了多次修正和完善,积累了很多经验与教训,也形成了一些兼具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安排,值得研究与借鉴。
一、美国的住房援助体系
1. 美国住房援助体系的历史沿革
美国的住房援助体系由联邦政府拨款、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执行,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支持或补贴。这一体系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根据《1937年住房法》,联邦政府设立了美国住房管理局(United States Housing Authority),由其提供拨款和低息贷款;并在州和地方层面成立了半官方的“公共住房机构(Public Housing Agencies)”,由后者负责建造公共租赁住房。这一法案的最初目的是在大萧条后为经济困难家庭提供廉租公共住房,同时通过创造大量住房建设项目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然而,随着项目落地,人们逐渐发现,由政府牵头建设并运营公共租赁住房不仅成本高昂、效率低下,需要花费大量财政资金,而且聚集式廉租公共住房容易导致低收入人口聚集和种族隔离,甚至发展为贫民窟。鉴于公共住宅项目的建设需要取得当地社区的同意,一些社区因担心低收入及有色人口聚集可能带来犯罪、社区环境恶化等问题,强烈反对在自己社区附近建设公共住宅1。
有鉴于此,6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陆续推出政策,将私人部门引入了住房援助体系。具体包括三种形式:
(1)政府直接购买私人承包商建造的房屋用作公共租赁住房,以节省政府牵头建设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2)政府从市场上租赁私人住宅,再以低价转租给低收入家庭,差价由政府拨款补足(此种做法被称为“项目制租房援助”);
(3)由低收入家庭自行在私人住宅市场寻找租赁房源,政府则向这些家庭发放“住房券”(Housing voucher)用于支付部分房租,以减轻其房租负担。由于私人住宅的房源分散,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低收入人口聚集的问题,也能帮助获援助人群更好适应周边环境,走出经济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住房援助体系的房源逐步发展为以私人房源为主、公共住房为辅的格局。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巅峰期,美国公共租赁住房的数量也仅有140万单位左右。随着越来越多使用私人房源、以及部分原有公共租赁住房的老化拆除,到2023年,公共租赁住房的数量已降至88.6万单位(图1)。
图1 1980-2023年美国公共租赁住房数量
数据来源:美国国会研究处,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
注:2009-2010年间统计方法经过调整,前后数据并不完全可比
2. 美国住房援助体系的现状
截至2023年,纳入美国住房援助体系的住宅数量约为513万单位,占美国住宅存量总规模的3.6%,低于2022年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7.1%,见图2)。约905万居民获得住房援助,占美国总人口的2.7%2。目前,在住房援助的三种主要形式中,公共住房占比仅有17.3%,项目制租房援助占29.1%,住宅券补贴占比最大,达53.7%(图3)。
图2 2022年OECD成员国社会租赁住房占各国住宅总量比例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图3.2023年美国住房援助体系不同援助方式占比
数据来源: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
经过多次改名和职能重组,目前美国住房管理局已被住房与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取代。HUD负责在联邦层面提供拨款,并管理和评估州和地方层面超3,000家公共住房机构。针对不同援助方式,HUD设计了不同的评估系统以评估州和地方层面公共住房机构的运营及财务等情况。
表1列举了公共住房评估系统(PHAS)的各类子系统和主要评估指标。地方公共住房机构需要就自己管理的各个项目定期向HUD报送数据并获得评分。评分较低的机构需要提高申报频率、制定改进计划、接受HUD的更强监督甚至被接管;评分较高的机构则可降低申报频率,且更容易获得联邦拨款。
表1.美国公共住房评估系统(PHAS)主要指标
数据来源: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
表1显示,在对地方公共住房机构进行监督和评审时,HUD不只是关注公共住房的供应量,更关注其运营的效率与质量。例如,通过监督入住率、租金收缴率、房屋安全与卫生、以及公共住房机构的财务健康状况等指标,HUD可从多个维度评估其拨款是否得到有效利用,以确保住房援助项目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避免出现由于房屋位置偏远或质量低劣导致入住率偏低甚至大量闲置的现象,形成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防止地方机构出现“重供应、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
地方公共住房机构则负责对各自区域内申请住房援助的家庭进行资格审查,并设定租金标准。只有收入低于一定标准(通常为所在地区年收入中位数的80%)的家庭才有资格申请。获得补助的低收入家庭大多为老年人、残疾人及有孩家庭,其所付租金被设定为不超过其年收入的30%。
不过,由于拨款不足、房源有限,美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住房援助无法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2023年,合资格的申请家庭平均需要等待25个月才能搬入补贴住房或获得“住房券”补贴。获援助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仅有17,201美元;其中,94%为超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低于该地区收入中位数的50%),77%为极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低于该地区收入中位数的30%)3。绝大部分低收入家庭无缘享受政府的住房援助。
二、对购房者的融资支持体系
在公共住房体系之外,美国政府还针对私人房屋市场设立了官方或半官方机构,通过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支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方式,帮助购房者改善融资条件、降低融资成本,间接地支持民众通过私人房屋市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
1. 支持购房者使用住房抵押贷款融资
1930年以前,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规模小,且非常碎片化,银行通常只提供浮动利率、期限在3-5年的本金非摊销类抵押贷款产品4。贷款人不仅需要承担较高的利率风险,且每3-5年就要重新协商条款并申请续贷。
此外,不摊销本金意味着还款期间仅支付利息,到期才归还本金;若贷款人在到期后无法续贷,就需要一次性偿还大额本金,还款压力巨大。大萧条期间,由于房价快速下跌、失业率大幅攀升,大量银行在贷款到期后抽贷,导致本就经济困难、无法偿还本金的购房者大量违约。违约后,银行拍卖抵押房屋,令房价进一步下跌,加剧了经济危机。
为缓解这一问题,1933年,联邦政府成立屋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通过发行政府支持债券融资,再从金融机构处收购已违约的住房抵押贷款并进行债务重组,为购房者提供固定利率、期限长达20年、摊销本金的住房抵押贷款5。不过,联邦政府认为,重组贷款只是应对大萧条期间房地产危机的临时措施;长期来看,为购房者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仍应通过市场机制。因此,在完成其使命后,屋主贷款公司于1936年解散。
1934年,联邦政府还成立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违约保险,鼓励金融机构推广固定利率且期限更长的贷款产品。随后,联邦政府又于1938年成立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一方面发行债券融资,另一方面在二级市场收购抵押贷款,为贷款机构提供流动性。
得益于上述机构的设立,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快速增长。到2023年底,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规模已接近14万亿美元,与GDP的比率由1945年的不到2%升至超过50%(图4)。根据联邦住房金融局(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FHFA)的数据,1963年,美国新增住房抵押贷款平均到期期限为21年,贷款/价值比约72%;到2023年,这两个指标已分别上升到2029年和81%,抵押贷款已成为购房者便利可靠的融资工具。
图4.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规模及与GDP的比率
数据来源:美联储,美国经济分析局
2. 推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主要贷款人为银行和储贷协会,他们以较低的利率吸收存款,然后发放住房贷款(大部分为中长期限的固定利率贷款),从中赚取利差。然而,60年代后期,由于越战导致政府赤字大幅扩大,叠加两次石油危机,美国的通胀和短期利率迅速上升,储户纷纷提取存款,转而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国债市场,导致银行和储贷协会的抵押贷款商业模式濒临崩溃。
为此,1968年,联邦政府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拆分为房利美(Fannie Mae)和吉利美(Ginnie Mae),并于1970年成立房地美(Freddie Mac),通过这三个主体大量收购住房抵押贷款,并以此为底层资产打包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再出售给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更多类型的长期投资者,从而为银行和储贷协会释放了更多流动性。
在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分拆为房利美和吉利美时,联邦政府将持有的全部房利美股票出售给私人,使其成为一家私有的政府赞助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GSEs)并上市6;而吉利美则一直由财政拨款,是政府全资拥有的机构。房地美在1970年成立时就是一家私有的政府赞助企业。
虽然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股权上属于私有企业,不占用联邦预算,但作为政府赞助企业,其经营活动需获得政府许可并接受监管。市场认为,这些企业的融资活动具有联邦政府的隐性担保,这令它们能以低于一般私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在资本市场进行大规模融资,从而间接降低了购房者使用住房抵押贷款的融资成本。
众所周知,在私有化之后,由于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以盈利为导向进行市场化运营,其经营策略更激进,承担了过高风险,在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也令公众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等资产证券化产品产生了怀疑。
为避免危机扩散,美国联邦政府接管了“两房”债务并购买其优先股,使“两房”处于政府托管状态,并于2010年退市。在此过程中,联邦政府根据《2008年住房和经济复苏法案》专门成立了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负责对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进行监管,并成为金融海啸期间联邦政府重新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后的托管人。
尽管如此,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等机构的成立无疑加快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进程。截至2023年底,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余额已接近9.4万亿美元,占全部住房抵押贷款总规模的67.2%(该比例在2008年后均保持在60%以上,图5)。时至今日,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仍主要依赖资本市场(而非存款机构)获得融资。
图5.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规模及占比
数据来源:美联储
三、总结与启示
以私有房屋为主、公共住房为辅的美国住房体系既有其成功之处,也存在明显不足。
一方面,相比欧洲的许多发达国家而言,美国的住房保障覆盖面偏低(图2)。美国的住房援助体系只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主要覆盖超低收入与极低收入人群,绝大部分低收入家庭无法享受政府提供的住房援助。由于房源数量少,申请者等待时间长,该体系无法满足大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另外,由于拨款不足,这一体系还常年面临维护和修缮资金短缺的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发达,住房融资、建设及交易高度市场化,运行效率高,有力支持了私人住房市场的迅速发展。1965~2023年间,美国住宅数量由约6,500万增加至1.46亿单位,人均住宅数由0.33单位增加至0.44单位(图6)。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调查显示,2020年,全美共有1.24亿套非空置住宅,总面积208.7亿平方米,套均面积169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69平方米,位居世界第一。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联邦政府通过提供抵押贷款保险、推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方式,充分利用商业银行、存款机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个人等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长短期资金,帮助购房者获得了长期稳定和较低成本的融资工具,有力支持了美国家庭通过私人住房市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图6.美国住宅单位总数及人均数
数据来源:美国普查局
美国的住房援助体系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近百年的历史沿革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些兼具公平与效率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划分。
由于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对公共住房的需求也千差万别,因此理论上讲,在地方层面管理和运营公共住房更具效率。然而,恰恰由于各地发展水平不一,那些最需要提供公共住房的地区往往是最缺乏财政实力来满足当地公共住房需求的;而且出于政治选票/晋升机会最大化等原因,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把仅惠及极少数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住房供应与管理排在众多政治目标之后,导致公共住房出现供应不足、质量偏差或位置偏远等问题。
因此,从公平角度而言,中央政府的参与和监管是不可或缺的。美国的住房援助体系由联邦政府出资、由地方机构运营、并由联邦机构监督和评估地方机构的运营效率,正是综合考虑了上述因素。
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针对不同住房援助项目建立了多维度的监督与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调整对地方公共住房机构的“奖惩”措施,以防止地方政府“重供应、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避免出现由于房屋位置偏远或质量低劣导致入住率偏低(甚至大量闲置)的现象,确保住房援助项目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这些监督与评价体系为地方政府开展公共住房(保障房)的建设、筹集、分配、运营、维护等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美国的住房援助体系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演变为以私人房源为主、公共住房为辅的格局,其援助方式包括发放“住房券”、提供住房转租援助和提供公共住房三大类。虽然美国的住房援助体系由政府主导,却高度依赖私人住宅市场,政府并非大包大揽。
对于私有房屋市场,政府也并非完全自由放任,而是通过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支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方式,帮助购房者改善融资条件、降低融资成本,间接地支持民众通过私有房屋市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这些做法和制度安排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过程中逐步优化和完善的结果,也非常值得借鉴。
四、组建全国性机构的必要性。
在房地产市场面临重大危机或挑战时,联邦政府多次成立全国性机构来稳定市场,支持购房者或金融机构度过难关。如前所述,这些全国性机构包括屋主贷款公司(1933年)、联邦住房管理局(1934年)、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1938年)、政府资助企业房地美(1970年)、以及联邦住房金融局(2008年)等。
当面临全国性危机时,由于信心普遍受到冲击,危机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地方政府往往难以独立应对,也不一定掌握合适的政策工具。另外,由于各地政府的决策机制和决策效率存在差异,即便地方政府普遍采取应对措施,也很难统一步调,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合力。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可发挥其统筹协调、一呼百应的能力与优势,通过设立具有特定功能和使命的全国性机构,针对现实挑战,有的放矢地出台相关措施,更直接高效地应对危机。
五、集中房源与分散房源。
为缓解低收入人口聚集的问题,美国的住房援助体系已逐渐从集中房源转变为分散房源模式。这一点值得我们参考。例如,在各地建设筹集保障房房源的过程中,不必强求以整栋楼房作为基本筹集(或收储)单位,而应允许吸纳一些零散的房源。
备注:
[1]McCarty,Maggie.Introduction to public housing.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Washington,DC(2014).
[2]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美国普查局。
[3]数据来源: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4]Maggie,McCarty,Libby Perl,and Katie Jones.”Overview of Federal Housing Assistance Programs and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Washington,DC(2019).
[5]Green,Richard K.,and Susan M.Wachter.”The American mortgage in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no.4(2005):93-114.
[6]在1938年成立之初,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是一家完全由财政拨款的政府机构,同时也向私人投资者发行债券筹集资金。1954年,协会改制为由政府持有优先股、私人持有普通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