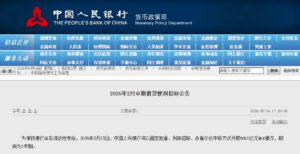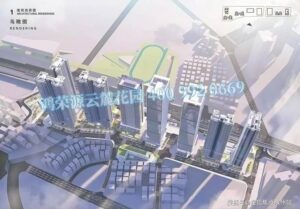关于“她”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蔚婷,编辑:钟毅
2025年4月19日,新周刊副总编辑吴慧与祝羽捷、辽京、李颖迪三位女性创作者在武汉展开了一场有关文学、成长与社会的深度对谈。她们谈写作,谈生活和表达的力量,也谈这个世界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她们以各自的经历印证了一件事:女性创作的边界正在打开。
祝羽捷说,很多女性已经不再按照主流叙事写作,而是回到自己的感受里,把细腻、复杂、难以归类的部分写出来。这种创作姿态,不是反抗什么,而是选择相信自我经验本身就值得书写。
辽京认为,写作是她重新整理世界、重新理解自己的方式。她的小说像一面柔光镜,照出都市生活里的情绪波动,也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
而李颖迪则用非虚构写作记录逃离城市的年轻人,和他们一起寻找意义。她说,那些“逃走”的人,其实是在试图找到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方式。
(图/刀锋时间)
她们的表达没有统一的方向,却共同指向了一种变化:女性创作不再是附加的存在,而是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独立的叙事力量。她们讲述的故事,早已超出“女性经验”的范畴,而是在通过个人视角介入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以下是对谈记录精要。
写作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和发现
吴慧:首先想询问辽京老师,你最初在豆瓣上发表作品,随后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并在近年来创作了《晚婚》《白露春分》等作品。你最初创作的原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想要写这些内容?
辽京:我的创作原动力可能源于某一天、某个时刻的自我觉醒。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生活中,除了现有的工作,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写作。我此前一直从事文字相关的工作,在期刊行业负责处理文字、采访,以及撰写他人期望看到的文章,传达他人想表达的观点。在某个阶段,我想写自己的东西,没有目标、期限,也没有交稿压力,书写自己的故事和情感。至于这些作品最终会呈现怎样的效果,以及会给读者带来什么,都是未知的。
写作的过程就是将这些未知逐渐变为已知,可能将不确定变成更不确定的过程,它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和发现。写作对我自己的的意义,远大于对读者的意义。因为读者有很多选择——走进书店或图书馆,但一个作者一生能创作的作品有限,更多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晚婚》
辽京著
中信出版集团·春潮Nov+,2021-1
吴慧:你认为写作对自身的意义大于对读者的意义。那么,回望过去,你的创作主题和题材是否有变化?有没有一条清晰的脉络?
辽京:在写的过程中,我没有明显的感觉,好像只是随意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如今回望,我的作品似乎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即都市情感、女性心理状态、女性情感问题以及家庭问题,以及更多地关注人在成长过程中面对自我的问题。总体而言,我所写的故事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切口,比较小的故事。
(图/刀锋时间)
吴慧:颖迪呢?你最初写作,比如创作《逃走的人》的初心和原动力是什么?
李颖迪:我大学时主修新闻,毕业后在媒体工作,早期参与过一些重大新闻现场的报道,例如武昌火车站凶杀案等。这些经历更像是工作的一部分。
时间久了,除了更极端的事件以外,我还是更好奇平常的生活,想知道其他人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好奇心让我开始关注“隐居”这一现象,进而了解到在黑龙江鹤岗、河南鹤壁这样的城市,有一群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大城市到这样的地方生活。我就去(这些城市)待了一段时间。
最初是为了观察他人,但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与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新冠期间那种精神状态,人跟人疏离的状态,让我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加入一些“自我”进去。
《逃走的人》
李颖迪著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4-8
从私人写作到“关系”
吴慧:每年我们都会讨论近100本好书,并最终选出刀锋图书奖的榜单。羽捷,你担任推委多年,从你的观察来看,近两三年女性创作是否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变化或趋势?
祝羽捷:我明显感觉到女性的写作,或者是女性的表达越来越多元,也有更多的出版物的出现。这不只是推委的阅读经验或喜好,很重要的一点是,市场在这些年有大量和女性相关的书籍出版。
在我们的小时候,阅读经验没有那么丰富。随着新一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她们对女性叙事的需求,众多原因造成今天有那么多优秀的女性的写作者。
过去她们还在“讨好”叙事的框架,或者是原来的读者的品位,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她们逐渐意识到个体的经验非常值得书写,它是珍贵的,所以大家又返回了自身。
(图/刀锋时间)
吴慧:我的感受也比较明显,可能是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本。作为70后,我们当时读陈染、林白(的作品)——那时被称为“私人写作”(一种写作方式)。在我看来,现在的写作似乎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比如家庭关系的变化和失去。辽京老师在《白露春分》中也展现了这种对关系的细腻描写。你们觉得现在的写作与过去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辽京: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出生在家庭关系里,随后进入学校,进入集体生活。我还写过大学宿舍的故事,这种集体生活中的关系变化极具中国特色。如果一个人独居,可能纠结或“关系”就不会出现。
人的许多成长和经验和故事都是在跟环境碰撞中产生的,并不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就产生了一种宇宙,一定有很多外围的故事,会来自外来的人、一些关系、变化、冲突,或者是温暖。所以每当建构一个故事时,我会首先想,需要一个什么样关系场景——是充满张力、激烈、紧张的关系,还是温和、松驰的关系,会让整个小说呈现不一样的质感。
(图/刀锋时间)
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就是小说的脉络和血流。
祝羽捷:我是陈染和棉棉的读者,我也很喜欢。而且我觉得她们的作品非常酷。
这很有意思。在艺术领域也一样,90年代时,很多女性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身体进行创作,用行为艺术表达观点、进行抗争。身体成为她们的第一战场。因为身体是最接近自我的媒介,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好像失去主体的表达权,所以她们首要夺回身体的表达权和使用权。
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小野洋子。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年代,这种表达显得尤为大胆。现在考古,我也觉得很刺激。有时候我也在想,今天的写作者怎么都那么温和,不敢去挑衅了呢?
小野洋子,《Fly》(1971)。
吴慧:我刚才提到的阅读感受,其实和祝羽捷说的类似。过去我们看的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冒犯性和挑衅性,给人一种独特的意味。但现在的女性写作似乎相对舒缓,颖迪,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李颖迪:我感觉像美国小说家理查德·福特或者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都写关系,我不觉得它是小的题材,好像全世界的作家都在写关系。
我在《逃走的人》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一个人能不能脱离其他人的关系而存在?人和人之间能否真正的达到理解?不是我要去写关系,而是这个东西让我困惑。包括我在尝试写小说,其实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家庭关系很困惑,这个出发点还是很自我的。所以我不觉得它观念的问题。
人能不能脱离其他人而存在?
吴慧:你之前提到去鹤岗时带着困惑,你在那三个月里见识了许多人和故事。离开后,你是否解开了当初的困惑?
李颖迪:其实我关注的起点不是鹤岗,而是隐居生活。我好奇一个人在封闭自我、不与外界接触的状态下会怎样。我内心或许也向往这种状态——不想向世界汇报,只想独自隐居。
之前有个朋友开玩笑说,很厌恶人,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好像离不开人,人有的时候很复杂的,有这样的两面性。
吴慧: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会特别焦虑、特别迷茫,包括我们说的躺平。我想知道三位老师对身边年轻人的这种焦虑、迷茫、躺平现象是怎么样的看法?
辽京:我们从小被灌输一种逻辑: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就会有个好工作、好前程和好家庭,(这种付出)会得到非常明确和及时的回报。
可能回报会慢一点,但它一定会来。可能今天忍受一下领导的压榨,等你成了领导,你就熬出来了。但是现在年轻人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回报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体系里才会实现。
比如说像我们父辈那一代,在工厂这种稳定的单位里,像我爸妈一辈子都没换过工作,他们就干一件事情,所有的这些逻辑链条也许是成立的,因为你真能看一群同事里,有人可能平步青云了,有人一辈子是个小科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像我父母那一代的人,对于同事之间的很多矛盾,他们可能都会忍,一辈子不会撕破脸,因为他们可能要共事几十年。
但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用“长期主义”看待事物,因为老板和同事都可能随时更换,行业和公司也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某些职位可能在未来消失。我们现在都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
所以我觉得躺平,实际上是在飞速旋转和飞速变化的社会里的一种放空。因为你可能再怎么样去卷、去赶,最后发现可能还是赶不上AI。
好像在一个高速旋转的机器里面,随着它去旋转。所以我觉得不是主动想安静下来,而是在这样一个状态里,被动地进行了选择。
我依然觉得所谓的躺平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我在面对当下人际关系、经济,包括情感,各种各样的观念在飞速的变化。既然一切都在变,那我关上房门,就过我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是不是可以不变的?就像吴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写关系,对自我当下感受的尊重、确认和认可,反而是当下年轻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