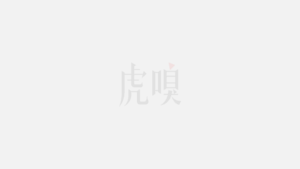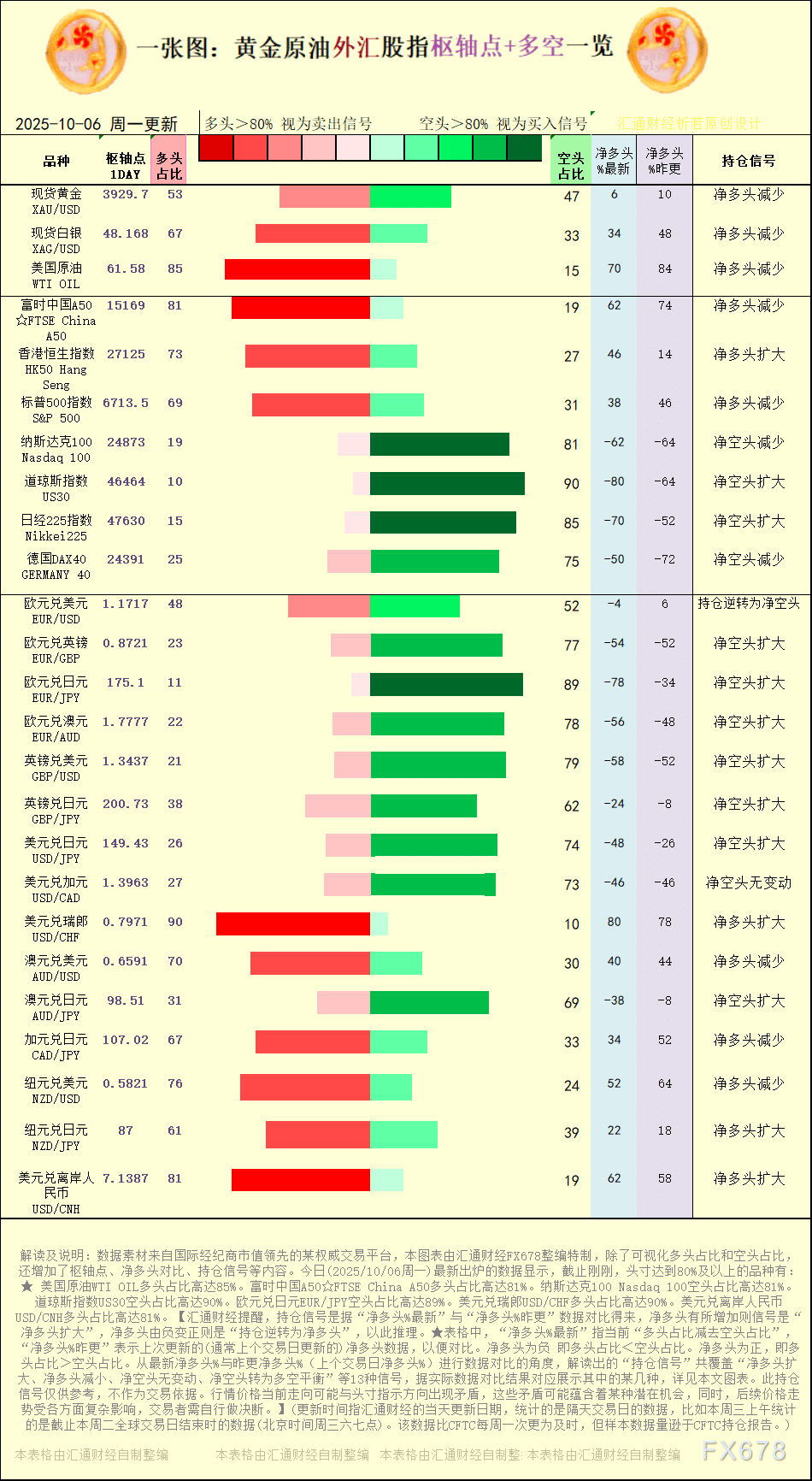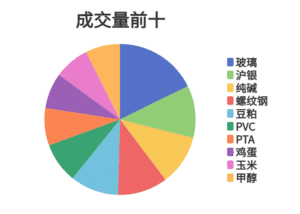突破垄断:广州体制的走私“虫洞”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
没有一国能垄断市场,一切国家主义,都必须放下自己的身段,去适应市场经济,在开放中,让市场经济接纳自己。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全球化,而非国家化。
以“散商”切入全球史
英国政府利用东印度公司从事鸦片贸易,挑动鸦片战争,通过战争,英国达到了控制对华贸易——通商的目的。
接下来,就没有东印度公司什么事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刚好,印度爆发了针对公司——代理政府的大起义,英国政府便趁机将公司取缔,白银时代也就跟着终结了。
白银时代是被英国人用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终结的,其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也是由英国人主导的,一是让用了两百多年的东印度公司破产,完成了它作为历史火车头在白银时代的历史使命,二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加烧了一把英法联军的大火,烧掉圆明园,烧毁了白银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东方成果。
对华贸易,由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从公司垄断的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时代转向“散商”自发的自由贸易时代。
有一本书,聚焦了这个时代的来龙去脉,其书名为《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作者韩洁西是美国人,她通过“三个苏格兰人”在印度和中国的商贸活动来看“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
从三个不同地区,她找到了三位同名“乔治·史密斯”的苏格兰散商,揭示他们在印度和中国广州的商业活动。
他们的活动时间是在乾隆时期,正是这些人的贸易需求,推动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作为全球化贸易体系中一只大不列颠的小虫,他们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自由贸易的虫洞。
以此为切入点,本书作者将其切入到全球史中,使之成为顺着西风带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史密斯先生”。
其研究方法,是以“散商”切入全球史,将“三位史密斯”——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广州的史密斯、孟买的史密斯的个体商贸活动,纳入帝国进程的宏观版图中,从“微观全球史”的视角,通过跨地域与跨文化的通商叙事,以其商业轨迹,串联起印度的马德拉斯、孟买与中国的广州三个往来贸易节点,展现了茶叶、白银、棉布和鸦片的流动如何在印太地区打造跨洋经济网络。
马德拉斯位于南印度,自1640年起,东印度公司于此,设基地,开港口,连接内陆与海上贸易,并为英舰补给,18世纪以后,印度鸦片由此中转,通过海上航线,转运至中国广州。
孟买位于印度西海岸,原为七座岛屿,经填海造陆后,形成天然深水港,东印度公司在此地建立其总部,通过该港,将印度棉花、鸦片输往中国,同时输入来自本国的棉毛纺织品。
而广州,自1757年,清朝“一口通商”后,便成为唯一对外开放口岸,广州作为终端市场,既是茶叶出口的起点,也是鸦片倾销的终点,三者形成“原料—中转—消费”的链条。
以此三地,形成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
其三角关系,实为全球贸易网络的缩影。三者通过商品、资本与权力的交织,塑造了近代亚洲的经济地理格局。
英国东印度公司同十三行合作,共同打造了一种贸易往来和金融互通的“广州体制”,却被“史密斯”们搞砸了。
书中,三位同名苏格兰商人——“史密斯”们,他们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总的来说,是一种不得不依赖,却又必然要颠覆的关系,其依赖是一种制度安排,或曰为“制度性依赖”,而其颠覆则出自自由贸易的本能——挡不住的本能,故其“资本主义”活动,既迎合了东印度公司的资金需求,同时,又挑战了公司的垄断地位,最终推动了大英帝国殖民政策转向。
垄断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一项政策授权,是有其时效性的,其时效性,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虽然没有规定,但一种制度用久了会坏,一项政策过时了也要变,要与时俱进,这当然是硬道理,然而即便垄断如日中天时,走私也会如影随形而至。
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维持垄断,固然是必要的,但维持垄断解决不了公司的资金缺口问题,要垄断茶叶贸易,先要解决维持茶叶贸易的白银流动问题,东印度公司长期面临对华贸易逆差,需大量白银购买中国茶叶,而这“三位史密斯”以其私人资本网络,将印度殖民地白银汇入广州,支撑公司的茶叶采购。
例如,广州史密斯,利用东印度公司的财库系统,帮助客户转移资产,确保公司在广州有充足的白银,用以支付茶叶款项。据统计,1769—1792年间,散商通过东印度公司财库,注入2881万西班牙银元,几乎覆盖了同期茶叶采购的成本2933万银元。
为此,他们采取了高风险信贷,三位史密斯以年利率18%—22%向中国行商提供贷款,虽低于中国法定36%的利率,但因行商资金链脆弱,最终导致大规模违约。例如,中国行商累计欠款达429.6万银元,引发1779年广州金融危机。他们的金融操作,虽可缓解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周转压力,却也加剧了贸易的脆弱性。
作为“散商”,史密斯们绕过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在印度洋开展独立贸易,建立其走私的独立贸易网络,挑战了东印度公司的特权,他们利用印度棉花、鸦片等商品与中国茶叶形成三角贸易,甚至直接参与鸦片走私,削弱了公司的贸易控制权。
走私也要有颗“勇敢的心”
以此,他们天然就成为了亚当·斯密自由贸易思想的信徒。他们头顶着一位思想的巨人,丝毫也不妨碍他们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走私”商人。
其实,“走私”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逐利而动的本能外,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还需有英雄主义的加持,以对抗犹如泰山压顶的制度安排。这时,他们就需要一位巨人,就如同恩格斯所说的,他们处在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而这样一位巨人,早已被历史性的命运召唤出来,为他们打开了一片思想性的天空,但实践性的天空则必须由他们自己去开启。
于是,苏格兰的史密斯们自觉不自觉,就成为了在全球推动自由贸易思潮的实践者,不但以“武器的批判”——“走私”的实践突破垄断,挑战了东印度公司的不可冒犯的特权,而且以“批判的武器”——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促使英国政府于1813年通过《印度贸易垄断废止法》,取消公司特权。
为什么是苏格兰人?事实上,在东印度地区从事贸易的英国人中,苏格兰人是英格兰人的四倍有余,相对于英格兰的中心地位,苏格兰处于大英帝国的边缘,反映着历史上“征服与被征服”的过往恩怨,既然英格兰人主导了英国,那么苏格兰人就向外发展,难以在英格兰人辖下的东印度公司任职,便成为自由贸易的独立“散商”,就如同他们在国内必须反对英格兰人的政治垄断,在国外也要反对英格兰人实施贸易垄断,反垄断成为其本能。
苏格兰人天然就有一颗“勇敢的心”,正是这颗“心”,使他们不但在思想上英雄辈出,如休谟之于哲学,破除了形而上学的因果论、国家观念的契约论,如达尔文之于基督教,破除了创世说,代之以进化论,如亚当·斯密之于经济学,以“看不见的手”超越权力支配经济、以自由主义取代重商主义、以自由贸易破除贸易垄断来确立《国富论》的根基,而且在实践上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之门,以自由贸易四海翻腾,涌现了一代苏格兰的“史密斯”们,其影响近代化的世界历史的进程,应当不亚于英格兰人。
正是那些“史密斯”们,他们不甘于被历史运势边缘化的命运,启动了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的国民财富的双轮,驱动着全球化时代东西方贸易交会的“去中心”,不但要去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中心,还要去了大清朝的十三行这个中心,然而,谈何容易!他们虽然担待了历史的运势,但又如何能逃过与生俱来的“贪婪”二字?表现在白银时代的市场经济里,集中反映为“货币”。
“史密斯”们既握有走私的“货”——茶叶与鸦片,同时又掌握了放高利贷的“币”——从各种渠道的虫洞里集资而来的白银,他们在代表东西方垄断的两个经济体——十三行和东印度公司之间,欲以走私和高利贷形成一个暴利闭环。
而东印度公司之于“史密斯”们,当然有其刚需,即以之填补资金缺口,然,又欲遏其独立贸易,凸显垄断地位,故于公司档案中,多有“史密斯”们越界记录,却又无法制止。眼见其高利贷引爆中印两地商欠危机,公司案头,窃忧窃喜,忧其灾难,恐危及“广州体制”,喜其失足,又颇能以“走私”说事。然而,危机之中,“史密斯”们岂是善与之辈?他们绕开公司,游说政府,欲将其私人贸易,转化为国家政策,影响公司的垄断地位。
公司利益,有别于英国政府的利益诉求,在对中国鸦片贸易以前,英国政府和商人阶层曾经长期忍受贸易逆差,不但向清政府输送白银,而且向公司年复一年地输送着中间利润。
由此可见,“广州体制”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垄断”,不但清政府用十三行搞“一口通商”是“垄断”,英国政府授权东印度公司专营又何尝不是“垄断”?再说,清政府跟东印度公司打交道,又不是只有英国一个,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其性质,同英国的差不多,同样带有“垄断”性,清政府跟它们打交道,早已熟门熟路,磨合出一套规则与潜规则,人称其为“广州体制”。
这样的体制,用了一百多年,都行之有效,若非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贸易的浪潮,“垄断”还会延续,因为一口通商,不光对清朝,对各国东印度公司都有必要。
三千年一巨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除了文明之初国家起源时的农业革命,没有什么革命能比工业革命深入文明的根本,能比工业革命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能比工业革命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无论英国革命,抑或法国革命,就其对文明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而言,都不及突破其底层逻辑的工业革命。
而苏格兰,尤其是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是英国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更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因为这所大学曾经拥有过瓦特与斯密,此二人者,一个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机械化的装置——蒸汽机,一个为工业革命赋予了一种新的文明样式——自由贸易。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所谓“自由贸易”,不过说说而已,只有工业革命爆发的产能才使“自由贸易”真有可能实现。
农业经济,相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人口增长而言,仍未从根本上摆脱短缺经济的局面,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手工业,受制于其基础所提供的有限的原材料和人工本身具有的局限,故其于产能方面难有突破性的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难以超越周期性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陷阱及韩非子铁定的口吻。
由短缺导致的垄断,带有某种必然性,表现为体制性的垄断、资源型的垄断和渠道化的垄断。但有一样,谁也不能垄断,那就是由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日复一日不断增长的产能。
它与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所有垄断都绝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一种垄断,能够垄断工业革命的日益高涨的产能,权力支配经济那是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权力变现,它支配不了工业革命的产能,没有任何一种国家权力及其社会形态,能够完全掌控其产能。
它有可能由于聚会了某种历史的因缘与条件而突然在某一国起源,但其形成与发展不会局限于任何一国,更不会受制于和听命于任何一国,它有自己的王国,亚当·斯密告诉我们,那就是市场,在市场的深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便是它的国王。
没有一国能垄断市场,一切国家主义,都必须放下自己的身段,去适应市场经济,在开放中,让市场经济接纳自己。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全球化,而非国家化,但国家可以在全球化中瓜分市场,这就使得市场经济超越地缘政治,瓜分市场而非兼并国土,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占据首位,并成为新国家主义。
亚当·斯密是它的先知,苏格兰的“史密斯”们则是被先知召唤出来被工业革命催生出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先驱,他们身上洋溢着工业革命的产能,驱动他们以自由贸易突破东西方国家主义的垄断,不但要突破中国的垄断,还要突破英国的垄断。
白银时代“自由的代价”
同样是垄断,清朝十三行比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差得很远。首先,垄断形成的背景与目的就不一样。十三行,是在朝贡思维下,为了应对海外贸易冲击而采取的防御性垄断,其核心目的,是维护“天朝体面”和传统经济秩序,而非经济扩张,被当作“加惠远人”的工具,强调政治维稳而非商业利益最大化。
而东印度公司,则是以扩张性垄断,实施其殖民战略,旨在通过贸易垄断,支持本国商人参与全球竞争,并逐步发展为殖民扩张工具。其垄断权,由英王授予,涵盖军事、司法、外交等,有如分封制下“授民授疆土”以“封邦建国”的诸侯一般。
其次,垄断的组织结构与权力机制也不一样。十三行是松散的官商联合体,以家族商行为主,分散经营,互相压价,虽曾尝试组建公会协调价格,但因缺乏统一财权而失败,其行政职能,需承担稽查税收、担保外商、约束洋人等任务,甚至需为外商走私行为担责,如伍秉鉴就因美商走私被罚16万两白银。
而东印度公司,则是集权化的股份公司,是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与分封制的历史遗产相结合,作为全球最早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建制,采取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有如英国政体,但以盈利为目的,其组织结构,有军队和法庭,如同诸侯一般,对印度殖民,此乃政府与企业共谋,由政府授权,而公司则以殖民掠夺来反哺国家财政,1757—1765年,英国通过公司,从孟加拉掠夺了3700万英镑,占同期英国国库收入的40%。
其三,在政策支持与资本运作方面,清朝基本不管,对于十三行,只管采取压榨性政策,实施重税与捐输,1773—1835年,十三行累计捐银460万两,用于战争、河工及皇室需求,对于债务处理,则奉行双重标准,仅惩罚行商欠外债,对外商欠华债置之不理,致行商资金链断裂,多半因债务破产。
而东印度公司,则在国家军事与金融支持下,推进其资本扩张,故其行为,已不单是市场行为,而是将市场行为转化为国家行为,以国家机器的暴力和统治力碾压市场,只要政府授权,它什么都敢干,贩毒算什么?战争,屠杀,夺人之地,灭人之国,还有什么它不敢干?拿十三行跟它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
它知道,其对手,并非十三行,而是十三行背后的那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的磨合,清政府积累了丰富的东西方贸易的经验,在重商主义方面,以其经济体量及其财源禀赋,不逊色于任何西方国家,更遑论各国东印度公司了。
欧洲列强诸印度公司,英国的,荷兰的,还有其他的,经历了同明朝的多番较量,都被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及其坚韧的弹性所折服,最终无不妥协,终于达成了以中国为主导的东西方贸易的大平衡——“白银时代”,到了清朝,承其大明衣钵,料理诸印度公司,也都基本搞定,在中国顺差的前提下,维持着双赢。
从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到1757年,乾隆时期才“一口通商”,期间,有157年,开了不止一口,康熙帝开海禁,一开,就开了江、浙、闽、粤四口,对外开放,随着通商频繁,纠纷不断,尤其发生了英商洪任辉渡海北上京师状告粤海关事件,清朝以此为由,关闭三口,独留粤海关一口,采取“利出一孔”的措施。
此举,看似闭关锁国,实则不尽然,它在当时,也是与各国东印度公司对口,因为重商主义时代,垄断是贸易的主旋律,真金白银才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东西方几番交手,清朝一点都不落后,将近两百年的贸易顺差,就证明了这一点。
乾隆时,关了三口,仅开一口,但加了一行——十三行,由这一行,代表清朝一口通商,让它与各国东印度公司对接,但它充其量只是被清政府拱过河的一只小卒,并未有任何授权,只能服从于清政府的财政需要,服务于诸印度公司的利益诉求。
这样的制度安排——“广州体制”,不但能减少纠纷,还为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同中国贸易的向导——省心省力,并对双方的贸易行为进行了担保——有依有靠,这无疑给东印度公司递了个迎合其垄断贸易的方便的枕头,一起反对走私,允其一口通商,使其高枕无忧,同时,也以此确保粤海关成为“天子南库”。
清朝以为这样就搞定了,因为在重商主义的世界格局里,东印度公司们不能不满足了,尤其是占了主导地位的英属东印度公司,几乎躺平就能盈利,它两头吃,吃了中国,吃英国,管他贸易顺差与逆差,总之,只要两国还要贸易,那就离不开它。
但是,工业革命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切,其产能喷发已然放之四海,随其产能一起喷发的,还有那些承载其产能的“散商”——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涌现出来的苏格兰的“史密斯”们。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