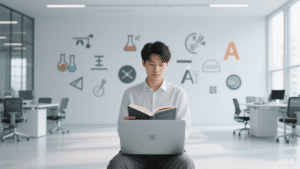越来越同质化的城市,该去村里找灵感
【来源:虎嗅网】
如果要充分讨论城市,我们很难完全绕过乡村。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段志飞,编辑:陆一鸣,题图来自:AI生成
6月初,Award360°年度设计奖展览在北京Ramp坡创意空间举办,展出了2024年度100件最佳设计作品。其中有一本名叫《大南坡:共振村声》的书籍,获得了“年度书籍”设计奖。作为这本书的内容主编,左靖串联起了这场书籍与展览、乡村与城市、人与空间的因和果。
《大南坡:共振村声》书籍封面。(图/受访者提供)
左靖是一名策展人,也是安徽大学的教师,不仅在各地进行乡村调研、策划乡土文化展览、出版地方文化书籍、开设实体空间,还主编了《碧山》系列图书。2007年,左靖开始把“乡村建设”作为自己的志业。此后近20年时间,他几乎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扎根乡村,把“总体性的乡村社会设计”作为努力的方向。
策展人左靖在大南坡村调研。(图/受访者提供)
从2011年的“碧山丰年庆”,到2017年的“碧山工销社”,再到2020年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大南坡村的“美学综合体”,左靖在他的实践版图上,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并陪伴至今。然而,在总结和反思自己这些年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时,他开始对眼下时髦的“艺术乡建”的概念产生了质疑。
“在2021年的一篇访谈中,我就提出,乡村更需要的是设计,而不是艺术。‘艺术乡建’不足以概括我们的工作内容。”左靖在接受《新周刊》记者专访时说,“近些年国内各地都热衷于打造‘文旅’打卡地,在这种大趋势下,许多与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有关的项目,都被内卷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千城一面’和‘千村一面’。我认为,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都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设计。”
在左靖看来,如果没有看到生活在那里的人,没有真正地为他们服务、为他们重建社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而只是讨巧地利用乡村元素搞艺术,或者仅仅为了拉动所谓的文化产业,就把文化当手段、赚钱当目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对当地文化的忽视和不尊重,与真正的文化建设背道而驰。经济指标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也只是“相对价值”,其中环境、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提高,或许比一时的富裕,尤其是破坏当地生态和文化的富裕更重要。
左靖的这种“抵抗叙事”,饱含着文人的悲悯之情和忧伤哲思。两年前,他还在河南信阳策划了首届TBB社区建筑与文化季,以“两个更好”书屋作为社区建筑的实践,计划为社区居民营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同时希望把他多年来在乡村积累的“原则、方法、路径”在城市里进行一次验证。
当聊到年轻人需要一种怎样的城市生活时,左靖拿出了许多与“乡村建设”实践有关的例子,并试图描述一种“游牧于城乡之间”的理想生活。
在大多数人潜意识里习惯将城市与乡村区别看待的当下,左靖认为,过去因为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城乡差异必须改变,未来的新型城乡关系,应该重建城市反哺乡村的传统,从而使两者互补、互助和互惠,促进城乡关系更加紧密。
以下为《新周刊》与左靖的对话。
城乡本无界
《新周刊》:一直以来,你围绕“乡村建设”做了许多实践工作。这次因为“新一代青年城市”的话题欣然接受了采访,是出于什么考量?
左靖:我其实一直挺想谈城市话题的,也曾经做过城市更新项目,但我反对把城市和乡村割裂开来谈。我做的城市更新项目有非常多有关乡村的内容,因为乡村是城市的根脉。此外,在中国,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乡村和城乡接合部。但很多人会觉得,城市就应该是高级的,资源富集理所当然;乡村就应该是淳朴的,甚至是落后的,资源匮乏能够理解。
比如,在大南坡,我们与方所文化合作,开设了一间“方所乡村书店”。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这么偏远的乡村做书店?我想反问的是:为什么不呢?这里的孩子和返乡的青年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阅读空间,他们和城里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文化权利和受教育权利,难道乡村不配有一间好的书店吗?
我们和日本D&DEPARTMENT合作的一家推广“长效设计”和“地方设计”的店铺开在皖南的碧山村。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会在乡村开这样的店,跟当地有什么关系?他们没有兴趣去了解“长效设计”和“地方设计”,习惯性地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对城乡之间设计理念的流动视而不见,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店就应该开在大城市。在他们眼中,乡村似乎是低一等的地方。
推广“长效设计”和“地方设计”难道要分城市和乡村吗?这种认知成见,会影响一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所以我不太想把城市跟乡村分开来谈。
从全球视角来看,其实城市的面积也只占了地球表面的极小部分,大量的人口与产业活动仍然在非城市的地方展开。贾樟柯在20多年前就说过,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只是一个个盆景,而真正的中国在乡村,大意是这样。那我想说,如果讨论城市,却要刻意地绕过乡村,那这种讨论就是不完整的。我相信,《新周刊》会找到我,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吧。
大南坡方所乡村文化书店。(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确实如此。假如说城市是盆景,我们确实应该找一找盆景的根在哪儿——其实就在你刚才说的这些非城市的地方。这种想法是最近才有的吗?
左靖:确实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小时候在县城长大,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去到乡村”完全是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思潮对我的影响。我写诗歌、做民间影像、策划艺术展览、到乡村去,其实都不是在主流上走。我和我的团队希望能够做一些不太一样的,同时又是有价值的、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从2007年开始,我们决心要做“乡村建设”,到今天差不多有18年了。你可以想象,我们从一个对乡村所知甚少的阶段,到慢慢接触到它的现实,被它教育,摔过跟头后又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就会总结一些工作方法、路径和经验,所以很多想法都发生了改变。
碧山村云门塔。(图/受访者提供)
我刚才讲,我不想把乡村和城市分开,这是因为我意识到,之前我也有这样的分别心所导致的误解与偏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平等地看待乡村和城市,每个地方独特的个性和魅力才是这个地方的“绝对价值”,不论它是城市,还是乡村。
《新周刊》:这种感受是从哪里来的?
左靖:举个例子,长效设计的倡导者长冈贤明先生在东京涩谷开办的d47美术馆很有意思。馆内展桌是固定的,每张桌子代表一个都道府县。比如说这张桌子是东京的、那张桌子是鹿儿岛的,桌面的尺寸都是90cm×90cm——完全平等地看待日本的每一个都道府县。长冈先生用这样的展览形式来鼓励地方设计。他认为,每个地方设计力的提升都能够“一公分一公分”地托举整个日本的文化力和竞争力。在这里,你会看到一种无论中心还是边缘、无论发达还是落后,都一视同仁的意识。
碧山书院。(图/受访者提供)
另外,这两年国内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大城市到小地方去,小地方包括四、五线城市,甚至更小的县城和广大的乡村。究其原因,是因为很多美好的事物存在于那些偏远的地方——没有被现代化、工业化席卷的地方。
再则,年轻人在大城市待久了,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现实层面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小地方的生活成本比较低,能够在成本和收入之间找到平衡,换一个地方活着好像也可以;此外,现在中国的交通、物流和通信非常发达,也助长了这种“返乡潮”,催生了新游牧一族(New Nomad)。
我的感受是:很多返乡的人,比如做餐饮、做咖啡、做民宿,对乡村来说,当然都是好事情,但是如果不能带动当地发展,和当地人没有紧密联结,而仅仅只是为了迎合城里来的人,那么在我看来,这样的空间只能短期地依赖一些游客效应,不见得能长久。
反哺之道,功在当下
《新周刊》:城乡之间的流动和变化,跟每个时期的政策,以及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关系。在城市化进入“下半场”的今天,“去到乡村”也是城市对乡村的一种反哺吗?这种反哺是否会成为“主流”?还是说,我们正在经历的“返乡潮”是暂时的?
左靖:我对宏观背景的认识可能并不准确。过去几十年,国家为了发展工业,对城市和乡村实行了不同的政策,确实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是,这样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不好好读书,就会把你送到农村去”,城市成了每个生活在农村里的人都向往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潜意识里都会对城市和乡村有着分别心,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中国古代,城乡可能没有像今天这样截然两分。对于以前的人来说,去更大的地方打拼,然后反哺乡村,是天经地义的。以前徽州的生意人,在扬州、杭州、武汉这样的大码头营生,等他们挣了钱,就会回乡修路、架桥、修宗祠、办义学,救助鳏寡孤独,有着非常好的反哺传统。
现在,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确实到了应该反哺乡村的时候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返乡潮”只是城市资源溢出的表现,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一直提倡的“往乡村导入城市资源”——比如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的阶段。以前是没有引起政策层面足够的重视,所以只能借助民间的力量,看能不能借此做一些事情,不过我们可以期待这种反哺在将来会成为主流。
碧山村村景。(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可以这么理解:过去18年来,你和团队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对于乡村如何接住溢出的城市资源的实践。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实践,你如今的感想是什么?
左靖:还是我前面提到的,要真正看到、服务到当地的人,让他们能够产生内生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媒体说我们做的是“艺术乡建”,但是乡村真的需要艺术吗?有时候我会觉得,那只是来自生活在城市里的艺术家的一种理想主义,一种“精英思维”。现实的问题是,乡村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似乎是被人遗忘的,各种资源都是匮乏的。所以,我们就从“缺什么补什么”的工作路径着手。
大南坡儿童四季美术课——旱厕大改造。(图/受访者提供)
拿儿童美育来说。5年前,我们与木刻艺术家刘庆元一起,在大南坡合作了“儿童美育计划”。在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大南坡小学的校长会带着孩子们去成都、天津和上海等地做展览、做交流。音乐教室落成后,我们邀请歌手小河和五条人乐队当大南坡儿童的首批音乐老师。这几年来,“大南坡儿童美育”成为大南坡的一张名片,很多外地的家长朋友们都很羡慕大南坡的孩子。
大南坡儿童四季美术课成果展布展中。(图/受访者提供)
今年五一,刘庆元带领广州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和合肥一家教育机构在这里合作了“大南坡城乡联动艺术计划”,让城市里的中学生和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共同参加了三天的研学。老师们在乡村与孩子们现场互动,乡村建筑、田园风光、木刻课、怀梆戏、柴火饭、手工烙馍、鸡鸭牛羊,这对于一直生活在城里的孩子们来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两地孩子们在交流过程中,互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认知。
五条人乐队、小河和小朋友们一起排练歌曲《森林里的一棵树》。(图/受访者提供)
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
《新周刊》:大约两年前,你在接受《新周刊》采访的时候,提到过“最理想的生活,是在城乡之间游牧”,其深意是乡村值得一去。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既然是在城乡之间游牧,那我们是不是也离不开城市?
左靖:前面我们一直在说乡村的好,但坦率地说,城市更有优势。比如我前几天去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大银幕上看了成濑巳喜男的电影《情迷意乱》。城市里有太多这样的文化资源供我们享用。如果你是一个对精神生活有着较高要求的人,需要去博物馆、美术馆、电影节、音乐会等,城市会提供这种文化上的便利。
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一个地方的认同,不仅仅因为这里的历史,还在于这里能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并不在乎文化活动是发生在城市还是发生在乡村。
如果在小地方,人们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活,也能喝到以前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喝到的咖啡,那其实在哪儿都一样。况且,乡村有着很多城市里所欠缺的优势,比如新鲜的空气、健康的食物,等等。像现在有很多“数字游民”,主要是因为小地方出现了能够兼容城市和乡村两种生活模式的空间。人们并不是离不开城市。
《新周刊》:现在的城市更新似乎有同质化的倾向。如果把你此前在碧山和大南坡所积累的经验嫁接到城市里来,是不是也能发挥价值?因为实际上城市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艺术和需要被保护的老建筑,等等。
左靖:近20年来,我们以城乡的地方性知识为工作对象,进行跨领域的文化研究与实践。在安徽、贵州、云南、浙江、河南和湖北的城乡工作中,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出版和展览工作,以及实体空间的具体实践,我们逐步确立了城乡工作的基本原则——“服务社区、地域印记和联结城乡”,以及在“城乡的社会设计”中所涵盖的四个领域——“关系生产、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
因循“往乡村导入城市资源,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的路径,强调文化创造力和可持续性,并以培养社区的文化自觉、改善当地的文化环境等作为目标方向,你会发现,这些经验的总结,不独是针对乡村工作的,在城市更新上照样适用。
《新周刊》:你最近有什么正在做的新项目吗?
左靖:去年5月,我们在温州市苍南县矾山镇考察,为当地政府做了一个策划。简单来说,我们为这个有着600年明矾开采历史的矾山镇制定的目标是申遗(去年年底,温州矾矿遗迹及其文化景观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该项目的顶层设计是“生态博物馆”——我一直钟爱的“社区主体性”的概念。同时,我们希望通过事件驱动,持续提升地方活力。
矾山镇三车间的煅烧炉群。(图/受访者提供)
所谓的事件,我一开始的设想是乡村建设双年展,原因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尚未有一个系统性探讨乡村议题的双年展。不过,几个月思考下来,我觉得“乡村建设”这个概念有点狭窄,不足以概括我们目前正在关注的问题,且最近几年,国内的乡村建设似乎越来越被内卷成“文旅”,从事乡村建设的人随之陷入一种“程式化”而无法超越。所以,我放弃了“乡村建设”的概念,把“全球,乡村”作为双年展的主题。
“全球,乡村”这个主题是想探讨,在全球化、资本和政策影响下的乡村应该如何自救?乡村应该借助什么力量获得新生?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人、很多机构的努力,这些努力大都表现为一种“抵抗叙事”。比如说,黄永松的《汉声》系列出版物,抵抗的是传统民间文化的消亡;长冈贤明的“D&DEPARTMENT PROJECT”抵抗的是不负责任的生产与消费;美浓爱乡协进会的“美浓黄蝶祭”抵抗的是当局和公司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北川富朗的“大地艺术祭”抵抗的是空心化、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地方衰败。有意思的是,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及我从事乡村工作20年所受到的影响,正好是以上四例。
福德湾居朱为俊的朱氏明矾世家家庭博物馆。(图/受访者提供)
这些前辈们发起并执着的事业大都持续了20—50年,甚至更久,呈现出一种长期主义倾向,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激励着后来者。目前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在推动中,期待明年春天的呈现。
《新周刊》:“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理想主义?因为毕竟相较于乡村,城市里并不缺少文化生活。
左靖:不瞒你说,“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最大的目的,还是把城市的资源吸引到乡村去。这条路径是一个桥梁,是想让城里人看到,原来在乡村同样能做那么多在城市里做的事情,希望吸引更多城里人到乡村去,作出他们的贡献。
建筑师徐甜甜和左靖在矾山考察煅烧炉片区。(图/受访者提供)
不仅如此,在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的策划下,我们把“大南坡乡村文化”带到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带到了柏林,今年还将在西班牙、比利时和摩洛哥等地巡展,让世界了解中国乡村发生的变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原载于《新周刊》总第686期《第Z城》,原标题为《专访策展人左靖——城市更新,把乡村作为方法》,作者:段志飞,编辑:陆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