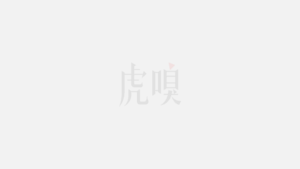阿里集权与分权的底层逻辑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商隐社 (ID:shangyinshecj),作者:浩然
只要讨论组织问题,集权和分权问题就无法绕开。
这几年对于阿里来说极为特殊,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后起之秀拼多多、抖音电商的步步紧逼,阿里先是采取了激进的“1+6+N”组织变革,试图通过大力分权让组织变敏捷,但随着创始团队回归,新管理层又进行了回调,重新进行了集权。
这显示出这家巨头在分权与集权、敏捷与聚焦之间的艰难权衡。
激进变革后的回调
这几年,阿里可以称得上是组织变革最剧烈的互联网公司。
早在2023年3月,阿里宣布启动“1+6+N”组织变革,在阿里集团下设立阿里云、淘天、本地生活、菜鸟、国际数字商业、大文娱等六大业务集团和多家业务公司。每个业务集团、公司都分别成立董事会,实行各业务集团、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
此项变革意在放权给子业务部门,打破“大锅饭”模式,子业务条件成熟时均可独立上市。这在当时被张勇看作是阿里“24年来最大的组织变革”。
2个月后,阿里抛出了一份子板块的“上市时间表”——阿里云在未来12个月分拆独立走向上市,菜鸟、盒马一年半内完成上市,国际数字商业集团启动外部融资。
正当阿里朝着“分权时代”大步流星前进时,却迎来了重大人事调整,在阿里担任了8年CEO、4年董事会主席的张勇退休,巨轮的船舵交给了来自阿里创始团队的蔡崇信和吴泳铭。
甫一换帅,阿里就明确了“用户为先、AI驱动”的战略主线,将资源集中到电商、AI+云,同时收缩外部大量非核心业务及投资。
所以阿里陆续减持了快狗打车、B站、网易云等长期亏损的投资项目,出售银泰百货、高鑫零售等非核心资产。
与此同时,阿里宣布暂缓盒马鲜生IPO,不再推进云智能集团的完全分拆,此后又撤回了菜鸟的赴港上市申请。
而那年年底,已经担任集团CEO、阿里云CEO的吴泳铭又兼任了淘天CEO,实现了“大集权”。
去年至今,阿里再次进行了力度颇大的变革,总体来看更加集权。
去年11月,阿里成立电商事业群,由蒋凡负责,新电商事业群把此前拆分的淘天、国际数字商业集团,以及1688、闲鱼等电商资源重新整合。蒋凡统辖了阿里的国内和海外电商业务。
今年5月份,阿里全面打通内部论坛权限,各个业务的员工时隔两年又在内网重聚,员工也陆续收到了统一的工牌。
6月23日,饿了么和飞猪并入到阿里中国电商事业群,其CEO均向蒋凡汇报。
至此,蒋凡已执掌阿里几乎所有具备消费属性的板块,算得上是阿里的大半壁江山。
6月26日,阿里发布的2025财年年报中更新了合伙人信息,合伙人总数从26人精简至17人,39岁的蒋凡不仅是其中最年轻的合伙人,还接替彭蕾成为阿里合伙人委员会成员。
阿里合伙人委员会相当于阿里的“内阁”,蒋凡与马云、蔡崇信、吴泳铭、邵晓锋这些元老级创始人一起行使选举等事宜,进一步完成了“加冕”。
阿里虽没有明确取消“1+6+N”模式,但已很少提及,近几年的一系列动作更是朝着大集团模式发展。
应该说,这几年对于阿里来说极为特殊,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后起之秀拼多多、抖音电商的步步紧逼,阿里先是采取了激进的“1+6+N”组织变革,试图通过大力分权让组织变敏捷,但随着创始团队回归,新管理层又进行了回调,重新进行了集权。
这显示出这家巨头在分权与集权、敏捷与聚焦之间的艰难权衡。
阿里的历次集权与分权
只要讨论组织问题,集权和分权问题就无法绕开。
在阿里26年的发展中,多次通过权力的集中与分散来提升组织效能。
比如阿里在2004年就把支付宝独立出去,没有将其绑定在淘宝这一个使用场景上,而是分出去满足所有需要支付的场景,让这个本来功能相对单一的工具长成了蚂蚁集团,已然是中国在线交易的基础设施。
还有在2011年,阿里做了一件极为夸张的事:把市场份额占80%的淘宝网拆成三家独立子公司——淘宝、天猫和一淘,分别找了姜鹏、张勇、吴泳铭这三个厉害的领导者带三个团队。
为什么进行如此激烈的变革?
因为当时的阿里对外部环境极其敏感且反应强烈,成为电商霸主的阿里在思考一个问题:电商的未来究竟是B2C,还是淘宝这样的C2C,抑或是通过一个搜索引擎指向无数独立站的B2C?
它无法确定,只能通过一拆三的方式把所有可能都拿来进行试验,三个团队按照对未来的理解往前闯,相互竞争也没关系,目标就是把对手干掉。
后来淘宝、天猫都跑了出来,而一淘没有被市场选择。
到了2013年,面对移动化浪潮的机会和挑战,阿里更是大手笔地将集团拆分为7大事业群,被称为“七剑下天山”,60天后,又继续把7大事业群拆成25个事业部,事业部业务发展由各事业部总裁(总经理)负责。
这算得上是阿里历史上最杂乱无章的时期,既有航旅、天猫、聚划算、B2B这样的垂直事业部,也有数据平台、信息平台等业务共享型事业部。没有固定打法,没有规则,甚至连具体的考核数字也没有。
在互联网从PC端向移动端迁移的关键节点,25个体量小但灵活的作战单元获得了更多的权限,从而免受庞大组织的层层牵绊,每个事业部都有团队专门研究那些刚刚冒出来的新网站、新商业模式,分析是否可以为其所用,或是否会成为其竞争对手。
这次变革使阿里成功迈入移动时代,也产生了菜鸟、钉钉、闲鱼等创新类业务,另外通过不断并购扩张版图,成为一个生态体系。马云也是在这次变革之后卸任了阿里CEO。
一般来说,分权程度越高,越能激发出公司的创业精神。但分权也有弊端,25个部门之间都有墙,每个部门自成一派,都在重复造轮子,一旦进行横向合作就会面临很大难度,每个部门考虑的永远都是部门最优,而非整体最优。
于是就造成了效率的下降和系统的不稳定。
所以在2015年12月,新上任的阿里CEO张勇开启了“大中台,小前台”组织架构变革。
中台就是把给具体业务提供基础技术、数据支持的部门整合起来,将从业务部门获得的数据、方法论、技术等沉淀下来,成为标准化的解决方案,然后给前台的业务部门持续提供支持。
前台部门由于剥离了沉重的技术包袱,轻装上阵,去应对和感知市场变化。
如此,等于是把权力进行了再次集中,因为中台再怎么强大,资源也是有限的,支持谁不支持谁、谁先谁后都需要去申请预算,集团高层会结合各业务线的盈利、人效等指标考虑预算是否合理,以此确定最终的配额。
这对强势部门和人效高的部门比较友好,但对前期投入大产出小的探索性部门则相当不友好,切断中台资源或者迟疑几个月,战机贻误,创新性项目可能就凉了。
此外,中台凝结的是历史经验,而阿里最强项无疑是电商,这使得中台抽象和沉淀的能力更多考虑的是电商相关场景,与电商近的效果会更显著。
从2015年阿里推出中台,到2020年阿里开始分散中台职能到前台,将近5年时间里,中台像一艘巨大的航母支撑着上面无数战斗机的起降,阿里员工从大约3万扩张到超10万,股价从2000多亿美元逼近9000亿美元。
应该说,中台带来的稳定、效率支撑了阿里大扩张时期的发展,使阿里从青春期迈入到了盛年期——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在《企业生命周期》中把企业的生命划分为十大阶段,在企业从孕育期到青春期过程中需要很大的创业精神主导,但到了企业盛年期,就需要稳定、秩序、效率来发挥特定的作用,从探索“做什么”“为什么做”到告诉几万人、十几万人“怎么做”,协调一致,制度严明。
但集权和强大中台的局限性在于,它会抑制破坏性创新的产生。
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十讲》认为,在追求稳定、效率的目标下,为了节约信息成本,组织往往在自己最为熟悉的邻近地域寻找答案,只有在出现问题而无法按已有常规进行下去时才启动“寻求”新答案的机制。所以组织常常在它最需要变革时反而强化了它的固有结构。
像中台其实就是在固有历史经验里寻找答案,确实高效、稳定,节约成本,但却失去了破坏性创新的可能。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688、闲鱼、钉钉、夸克这些创新性业务基本出现在2012年到2016年阿里频繁大裂变期间。
图为阿里2004-2020年重大组织变革策略及产生的创新性业务
(商隐社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整理)
还有直播电商,淘宝早在2016年就推出了,那年抖音才刚上线,直到2020年才切入到直播电商赛道,淘宝本具有先发优势,但在淘宝那里,直播只是作为货架电商的延续和补充,用来丰富淘宝生态,并非破坏性技术。但对于抖音来说,这就是一项破坏性技术。
还有用来阻击拼多多的淘特,在固有的组织结构、做事流程和价值体系里仅仅是作为对原有业务的补充,并未作为一项破坏性技术来培育。
到了2020年,形势所迫,阿里开始打破集权模式,给各大业务松绑,探索更为敏捷的组织形式,比如推动了经营责任制改革,以4大板块分立实现阿里多元化治理。
后来竞争更为激烈,对手攻势如潮,阿里在2023年激进分权,推出“1+6+N”的组织大变革。
这其实是为了呼唤已经缺失的创业精神和敏捷性,但从刚才提到的企业生命周期的十大阶段来看,此时阿里已经在向贵族期转变——账上虽然有大量的流动资金,但企业创新精神微弱,执行下降,更关注形式,企业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将重点放在“如何做”上,而不是“做什么”和“为什么做”上。
而贵族期其实已经错过了通过分权激发组织创业精神、延缓企业衰退的最佳时期,最佳时期是在势头正盛的盛年期,此时组织对于“做什么”和“为什么做”大多迷茫,创业精神已然微弱,而外部竞争激烈,激进的分权反而容易被崛起的对手各个击破。
所以不难理解阿里近几年不断通过集权对组织进行回调,或许就是通过整合探索组织集权与分权的最佳配比。
这有点像2014年纳德拉接手的微软,当时微软已经开始衰落了,越来越不被人看好,但这不是因为微软不挣钱了,相反它非常挣钱。
大多数人不看好微软是因为,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无所作为,PC时代微软有独霸天下的Windows操作系统,有Office软件,但在移动时代,苹果有iOS,谷歌有安卓,亚马逊有AWS,微软啥都没有。
而且当时微软创业精神也已微弱,内部山头林立,公司重要资源依然围绕Windows和Office运转,大家都在Windows上死磕,企业显然也步入了贵族期。
纳德拉接手微软后,没有机械地进行大规模集权或分权,也没有拿出杀手级的产品,而是更灵活地对微软进行了梳理和整合,主要就是战略、文化上进行了集权,而在战术上进行了分权,顶层坚定、执行灵活、强化协同,从而使微软从衰退中走出来。
从来没有唯一解法
企业的集权与分权问题,说到底就是企业追求效率,跟追求布局未来的可持续性之间,存在着矛盾。
怎么理解呢?
具体说来,一家企业必须提高效率才能适应此时此地的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是它的效率越高、对此时此地环境的适应越好,它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就越差,它的长期适应能力也就越差。
任何企业都存在这样一对矛盾,只不过大企业会更突出。
创新有代价,需要面对更多不确定性,投入大量成本,费力开辟成功率很低的第二曲线。
但追求效率也有代价。要实现高效率就要求组织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套一环,成功的企业通常也会利用企业文化来强化这种组织关系,使得员工的行为规范化。
但这也意味着整个生产过程把外界的干扰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信息基本上被这一结构圈住了,固定的参加人员、固定的讨论课题常常排斥新的信息、新的问题。
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对外部市场环境的敏感度下降,追求的是延续性技术,而非破坏性技术。
分还是合,选择效率还是可持续性,什么时候选,持续多久换成另一个,从来没有唯一解法,考验的是一个组织的变革能力以及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