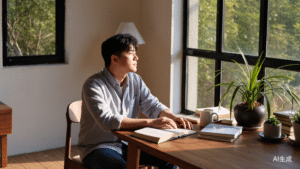美国通胀在路上
【来源:虎嗅网】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重新点燃了学界和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激烈讨论。围绕高关税政策的通胀效应,当前争论主要聚焦于三个核心问题:其一,关税政策的价格传导机制究竟是推升通胀水平还是引发通缩压力?其二,若通胀确实出现反弹,其时间节点如何?其三,关税冲击所引致的物价调整属于一次性水平效应,还是将演化为持续性的通胀过程?
笔者认为,关税政策会先推高美国通胀,未来是否会陷入通缩关键取决于美国经济是否会衰退;关税对物价的影响在五月已开始显现,下半年涨幅将更加明显;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实施拉长式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关税推行方式,将对通胀产生较为明显的上行推力,且价格上升可能不是一次性。
一、通胀先于通缩
市场对高关税政策影响美国物价水平的判断存在分歧。主流观点认为关税上调将通过进口成本传导机制推升通胀水平,而另一观点则认为关税冲击将抑制经济增长并引发通缩压力。
根据传统贸易理论,关税壁垒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相对价格,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胀效应。然而,历史实证证据对此结论的支撑并不充分。
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过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期间,美国通胀率同样未出现显著上升(图1)。理论预期与实际结果的背离反映了通胀形成的复杂机制:关税政策虽然从供给侧产生推涨压力,但当经济活动大幅收缩时,需求侧的通缩力量往往更为强劲。1930年美国实际GDP收缩8.5个百分点,经济陷入大萧条,需求崩塌主导了价格走势。2018年美国经济则呈现不同格局:实际GDP增长率达3.0%,经济基本面相对稳健,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约10%,部分抵消了进口成本上升的影响,因此既未出现显著通胀,也未陷入通缩。
图1:两次高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
注:图中线条“1930年”以1930年1月为起点统计的CPI同比走势,线条“2018年”为以2018年1月为起点统计的CPI同比走势。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
当前经济环境下,关税政策更可能率先触发通胀上行而非直接导致通缩,其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美国经济基本面保持相对健康,消费需求具备韧性,即使关税冲击导致增长放缓,通胀上行也先于经济下行显现。
其次,本轮关税税率大幅提升且覆盖范围广泛,美国短期内缺乏充分的进口替代渠道和自我生产能力,供给约束将加剧价格上涨压力。
第三,美元汇率走势相对疲弱,限制了贸易伙伴通过汇率调整对冲关税成本的空间。
当然,若未来美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并陷入深度衰退,通胀预期仍可能逆转为通缩风险。
二、通胀上行始于五月,下半年涨幅将更加明显
尽管特朗普政府于4月2日正式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但4月份通胀数据并未出现即时反应。当月美国CPI同比涨幅为2.3%,较前月的2.4%略有回落。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美国企业在政策预期驱动下的“抢进口”行为。2025年一季度,美国进口总额同比增长23.3%,贸易逆差达到近30年来的历史高位。根据市场测算,当前商品库存水平大致可维持2~3个月的消费需求。
美国5月CPI同比小幅上涨2.4%,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已初步显现。随着“对等关税”政策的深入实施,企业前期积累的商品库存逐步消耗,而新采购的进口商品面临显著的价格上涨压力,这直接推升消费价格水平。
从CPI分项看,玩具项同比上涨0.2%,结束了2023年7月以来的负增长;大家电项则同比上涨2.2%,结束了2022年9月以来的负增长,这表明受关税影响较直接的品类价格已开始上涨。
微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5月份美国Truflation指数开始呈现上行态势。该指数通过与亚马逊、沃尔玛等主要零售商合作,整合超过30个数据源和1300万个价格监测点,构建覆盖国内商品和服务的日度更新通胀指标,为实时、全面的通胀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过去一年的数据表明,该指数与官方CPI具有较高的拟合度和预测价值。
美国6月CPI同比涨幅上升至2.7%,下半年价格上涨将更加明显。巴克莱预计,承担更高关税的货物将在6月底或7月初到达美国港口,并在7月底的返校季节开始进入商店,届时更广泛的关税相关涨价效应将开始显现。根据堪萨斯联储的调查,企业预期未来六个月产品价格将明显上涨。从历史上看,该指数很好地领先于美国CPI走势,这也预示着下半年美国将迎来更明显的价格上涨(图2)。
图2:企业对通胀预期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和堪萨斯联储。
三、物价上涨可能不是一次性的
在评估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时,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通常认为:这应该只是一次性的价格上涨。但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方式不确定、节奏拖沓,使得通胀上行轨迹可能比理论复杂得多。这种拉长的、渐进式的、高度不确定的关税推行方式,会重塑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如果企业和家庭开始预期未来还会不断调整关税,这种预期可能会带来更持续的通胀压力。
传统经济学理论将关税冲击视为一次性供给侧冲击,预期其对价格水平产生离散的跳跃式调整,即关税实施后进口商品价格立即上升至新均衡水平并保持稳定。这一理论建立在关税政策透明、确定且一次性实施的假设基础上。然而,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和渐进性特征,采用分批次、差别化的税率调整方式,辅以复杂的豁免机制和谈判空间。关税覆盖范围的动态扩展以及税率的阶梯式提升,使政策路径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
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将重塑通胀的动态传导机制。企业层面,面对持续的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在每轮关税调整后都可能转嫁成本,使通胀呈现持续上行特征。消费者层面,家庭部门会形成“未来还将有更多关税”的适应性预期,促使提前购买和囤积行为,在需求侧产生额外价格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预期一旦形成,将具有自我实现的特性。此外,渐进式关税政策迫使企业频繁调整供应链布局,产生额外转换成本和新供应链的磨合成本,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价格上行压力。
四、其他因素也将对通胀产生复杂影响
当前美国通胀形势呈现多重力量交织的复杂格局,其走势还取决于以下因素的相对强度及时序效应。
从通胀上行驱动因素来看,财政政策和移民政策构成主要推力。
财政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已通过“大而美”法案,该法案以减税和重构支出结构为核心,在延续削减个人和企业税负的同时,显著增加国防支出和边境安全资金。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该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导致联邦赤字扩大2.4万亿美元。这一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对通胀水平形成显著支撑。
移民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实施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鉴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目前处于相对均衡状态,劳动力供给的急剧收缩可能引发结构性短缺,推动工资成本上升,并导致核心通胀更加顽固。
从通胀下行制约因素来看,支出削减和经济增长放缓构成主要阻力。
支出削减方面,政府效率部虽然面临领导层变动的组织挑战,但其削减财政支出的政策导向仍可能对总需求产生抑制作用,其在边际上的支出压缩效应需要在下一财年预算中才能确定。
经济增长方面,关税政策、政策不确定性、净移民减少以及联邦雇员削减等因素的叠加效应,已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国今年GDP增速预期下调至1.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期仅为1.6%。经济增长动能的减弱将通过需求侧渠道对通胀产生抑制效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作者:杨子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辑:王延春,责编:张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