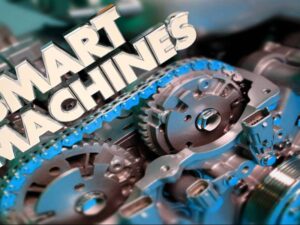在“冷”与“热”之间,观念如何流转?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李佩珊
观·察
“个体在敏锐感知时代潮起潮落的同时,如何在变动中不断铸造自身的“小我”,并将自己的艺术之舟,在时代的洪流中幻化为一艘巨轮,这对今天同样身处剧烈变革中的我们而言,是一次值得反复回望的启示。”
在“冷”与“热”之间,观念如何流转?
文/李佩珊
在文化的深流中,最难察觉的,往往不是风格的变迁,而是观念的转向。语言、形式、风格可以迅速更新,而深层的价值判断——关于艺术的功能、个体的立场、传统的可能性——则往往缓慢、固执,且在代际之间传递得异常复杂。
我们或许正身处这样一个中途时刻:文化不再以明确的“前卫”或“回归”来定义,而是在延续与偏移、引用与再造之间反复震荡。传统不再是被超越的对象,而是必须重新命名、重新调动的资源。个体表达也不再天然被赋予进步意义,而需要在碎片化与过载中重建其逻辑。
近期,《热与冷——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创新与继承》艺术展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凹凸空间举办,《经济观察报》与策展人卢迎华、刘鼎,以这次20世纪80年代艺术现场的回望为契机,对于思想文化观念是如何代际传递与再生产聊了聊。卢迎华现任北京中间美术馆馆长,是活跃于国际的艺术史学者与策展人。刘鼎则是一位兼具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身份的学者型艺术家。
我们试图讨论思想的生成方式,也试图从历史中凝视未来。两位策展人并不试图建构某种确定的理论路径,而是揭示出观念内部的层次感——那些看似已被书写过的历史,那些似乎早已被命名的“潮流”,其实仍在发生,仍在被重新定义。
刘鼎(左一)、卢迎华(中间)在活动现场受访者/供图
|访谈|
经济观察报: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思想解放”的时代,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文化热”。为什么认为“文化热”是统摄整个1980年代的核心范畴?在您看来,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了哪些重要的文化思想潮流(如对真善美的追求、人道主义思潮、西方哲学涌入等)?
刘鼎、卢迎华(以下简称刘、卢):“文化热”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突出的标志。从1978年开始,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的提出,以及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凸显,成为这一时期“解冻”的一些重要征象。自此,人文学界在1980年代扮演了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1980年代也常常被概括为一个“文化”的时代,不同专业领域纷纷形成突破既有格局、并具有冲击力的文化革新力量。
尽管人们往往将“文化热”视为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哲学和史学为代表的现象,并将其作为“85美术新潮”出现的思想前提,但我们认为,它也可以被视为统摄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核心范畴,是20世纪80年代表述自身的关键语汇。它涵盖自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以来,持续涌现出的多种人文思潮。
从20世纪80年代初过渡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和“寻根”思潮,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强调“纯化语言”、主张去意义化的思潮,共同构成了话语涌流的1980年代。这些多样的思潮和艺术取向弥散于这一历史时空之中,既有相互渗透与感染,也存在彼此抵制与基于反思和批判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虽然多集中在理论与思想层面,但其内在的活跃动力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层面的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密切相关。正是这一时期,全社会空前关注现代化建设和文化自觉,使文化议题走向时代前台,思想探讨也因此呈现出更为锐利与多元的面貌。
经济观察报:这场文化热潮是如何席卷了哲学、文学、美术领域,“同频共振”的?当时美术界与哲学、文学领域,比如“美学热”、尼采和萨特思潮等对艺术家的思想有何影响?
刘、卢:在当时的思潮现场中,不同研究领域彼此互动,共同构建起对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意识。具体到艺术领域,这种思潮体现为跨年龄层的多样创作取向与思想路径,它们既各有侧重,又盘根错节。
1978年,理论家从“共同美”的讨论入手,自然地引出了对人性与人道主义的关注。此后,美学家接过“共同美”这一合法旗帜,使新时期的“美学热”展现出全新的理论面貌、理论命题与理论性质,“美学热”由此拉开序幕。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过渡时期,出生于20世纪初(大致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间)的艺术家,在创作中更加强调艺术形式本身的美感与审美价值,展现出对艺术自主性与个体表达空间的关注。他们以“美”为核心,在题材与风格上追求多样化,推动艺术从以往的功能性表达中逐步回归其本体特征。他们以优美的线条、斑斓的色彩、肆意的笔触和自在的抽象形式刻画风景、追求诗情画意;描绘纯真美好的人与淳朴的生活,抒写温馨、感伤的情感,表现朴素、纯净的人性,讴歌人性之美,点燃了“美”这一时代精神的火花。从吴冠中力倡“美”的言行,到印象派风景画的回归,以及对精致线条组合与装饰化造型的探索,再到对现实进行浪漫化处理的诗意表达,都是“美的向往”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
以首都机场壁画为先河,其和谐悦丽的色彩、线条与少女体态美模式——“S”形动态线、螳螂式的秀美造型——迅速风靡,广泛出现在壁画、装饰性绘画和非线性风格的油画与版画之中。
自1983、1984年起,大量西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以“人学”之名被译介入中国,宽泛地将所有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思想混合传播。与此同时,文化哲学的兴起伴随着“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等在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的流行。叔本华“世界是我的意志”的主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自由选择”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等,共同成为张扬“个性”与“人性”的思想依据,进而演化为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伦理。诸如“全能意志”“本体”“绝对精神”“自在之物”等超验哲学范畴一时间成为热议话题。这些观念激发了艺术家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注,并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试图构建一种超越现实的人文图景。孤寂、荒诞、悲剧性、宗教氛围与牺牲精神,成为一批艺术家力图在其作品中展现的主题。
《经济观察报》:展览中如何体现美术创作与思想界(美学、哲学、人类学等)的对话?从思想解放后的美学热、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寻根”到后来的后现代、纯化语言、反文化思潮,这些在展览中如何呈现彼此交织的关系?
刘、卢:“文化热”的思想动向与新时期的现代化改革进程密切相关。完全不同的经验与想象在历史关口并置共存,彼此之间那种粗粝交叠的状态,带来一种令人目眩的快速变动印象。在艺术层面,它体现为一次探索创作自由与个体自由,并为之寻找论据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不同代际艺术家的创作取向,以及同一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面貌,常常呈现出目标一致而表达各异的“一体多面”。展览划分为三个章节,分别为“关于美”“关于热”和“关于冷”,聚焦艺术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藉此呈现并行交织的思想现场如何影响艺术实践。在展陈结构上,我们既在同一主题下展出不同代际艺术家在同时期的作品,也在不同主题中呈现同一位艺术家的多重面向与艺术探索。
此次展览中包含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时任《中国美术报》主编的张蔷先生于1986年绘制了两份表格,一为《绘画群体情况表》,一为《绘画群体成员情况表》,并发至曾被《中国美术报》报道过的艺术群体或个体。《绘画群体情况表》主要询问群体的成立时间、地点、成员人数、组织结构及活动方式,并留有充足空间填写展览记录、发表情况及群体的艺术宗旨。《绘画群体成员情况表》则聚焦于个体艺术家的相关信息。其左半部分涉及个人背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籍贯、加入群体的名称与时间、教育经历、15岁以来的生活轨迹、工作单位及职能、近五年最喜爱的书籍(限五本)、影响最大的著作,以及最崇拜的哲学家与艺术家。右半部分则围绕其创作展开设问,涵盖1985年作品概况及创作意图、代表作的展览与发表、撰文与刊发经历,以及艺术主张和未来的创作设想。
这批保存了三十余年的一手文献,使我们得以切近地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一代年轻艺术人的多元教育背景和文化心理。除成长与就业经历的斑驳差异之外,他们也在“文化热”笼罩下,共享着某种相似的艺术趣味与阅读经验。在这些文献中,被反复提及的哲学家和艺术家既包括尼采、海德格尔、黑格尔、萨特等西方思想史人物,也有孔子、老子等中国文化象征,当然亦不乏明确拒斥外来影响的表达,这本身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情绪的复杂流动。他们多倾向于阅读西方古典或现代主义文学,海明威、博尔赫斯、爱伦堡等名字多次出现在表格中;在艺术偏好上,他们热爱高更、塞尚、蒙克、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史的重要人物。
这些材料不仅揭示了彼时艺术家们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他们在创作中从文学、音乐、哲学等多个维度汲取资源,跨越中西界限,构筑出一幅绚烂的文化色谱,也进一步显影了那个时代的认知边界:有人以直觉分享创作感受,有人深入反思自身的艺术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思考与表达,也正是那个开放年代的文化取向与创作经验的缩影。
《经济观察报》:我们可以看见展览中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艺术家在吸收西方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对个体经验、存在状态的深入关注。其中一些作品以沉静、内省的风格描绘人物状态,表现出对人类境遇的哲思和艺术语言的探索。这种“从呐喊到反思”的精神转向,您认为是受怎样的社会心理和哲学观念驱动?
刘、卢:在20世纪80年代强调人的意识世界与超验性的思想氛围中,超现实主义风格成为这一时期具有普遍性的艺术倾向。1985年,一种颇具趣味的创作现象在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中广泛出现:画面中大量出现背对观众的形象。这些人物面对的是空旷的背景,背景本身往往缺乏具体的观照对象。画面中既没有非此即彼的判断,也无激越奋发的情绪,更无缠绵悱恻的伤感,甚至也不见苦苦的思索;主题似乎消隐,一切都被一种茫然而暧昧的气氛所笼罩。
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呈现出静默、内敛的气质,人物形象多沉浸于思索或孤立状态,画面背景则趋于抽象、空旷。这种创作风格并非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荒诞派等)的启发,是一种回望内在、强调个体经验与存在感的表达方式。这一创作转向,也预示着“新潮美术”的阶段性变化,标志着艺术家在经历了思想热潮之后,开始进入更为分化、个体化的探索路径。
“关于美”的展墙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报》:当理性思考、超现实主义氛围和“反文化”“反艺术”精神涌现时,文化思潮和艺术表达如何发生了“冷”转向?“热”到“冷”的变化是线性演进还是同时并存?如何避免将“热”“冷”简单等同于“前卫”与“保守”的刻板印象?
刘、卢:在我们看来,“热”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气质统领了这一时期,而作为表现形式的“冷”,则是“热”的一个重要面向。1985年10月,美国艺术家劳森伯格自筹资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一些中国艺术家从中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所释放的潜力,以及其对现代主义传统本身的批判性立场。这个展览加速了一部分艺术家在观念更新的延长线上迈向达达式、波普的、去意义的、偶发式和观念性创作的步伐。绘画、雕塑等单一媒介已无法单独承载这类表达诉求,现成品装置、行为和事件等纷纷登场;这一种转向也使艺术的关注点超越了技法与语言的本体维度,转而提出对艺术制度、社会关系乃至提出了超越技法语言等本体特征的要求,艺术必须开始向自身、向体制、向社会发定位的根本性追问。
自1986年起,全国各地相继涌现出不同层次、立场与方式的展览,比如厦门的“厦门达达”、杭州的“池社”、上海的“M艺术群体”、广州的“南方艺术家沙龙”等艺术小组活动,这些都在暗示一股“不可逆的趋势”。这股趋势体现为各种具有达达主义精神的实验,艺术家通过形式或观念上的激烈和极端,在艺术边缘展开探索,挑战各种折衷主义。“新潮美术”也因此迅速走向分化与终结。
1986年是分野明显开始的一年。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艺术界某些“去意义”“去趣味”“去形式”“去终极目标”“去艺术表达中的阶级等级”等诉求结合,推动了一系列带有虚无主义意味的创作;另一方面,艺术学院中从事教学与创作的艺术家,则明确提出“纯化语言”,强调艺术应回归本体,将形式和语言确立为创作的核心价值。伴随“新潮美术”悄然涌动的追求“自律性”与“纯化”的流向,包括古典风、抽象风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85新潮”中以文化问题为观照的异质力量。这一时期对艺术本体的复归,既延续了对艺术在精神领域中独特地位的关切,也体现出对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精神的某种“离异”。
20世纪80年代可视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当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一些早期积累的发展路径与艺术理念在此时期获得新的激发与探索机会,也体现出艺术语言对社会变迁的多元回应。以复兴“美”“传统”“民族”与“现代派”为取向的一类艺术实践,强调人的意识世界与超验思维;而“反文化”“反艺术”的激进表达则构成了另一种路径。这些多元趋势共同构成了当时的价值结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主体对这些路径进行重新启用与创新,进而形成各种激变的可能性。而这些激变往往持续时间有限,被视为“先锋”的实践者,也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转向。
《经济观察报》:展览副标题提到“创新与继承”。一般谈历史常说“继承与创新”,而您特别将“创新”置于前。您是如何理解1980年代艺术创作者在革新与传承之间的平衡的?他们在突破前人束缚的同时,又继承了哪些过去的经验与遗产?
刘、卢:以“新潮美术”为标记的艺术史叙述,往往强调1985年的转折意义。这一年,曾因思想讨论节奏放缓而积蓄的能量重新释放,思潮再度集中活跃,推动全国各地艺术群体的集中涌现。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涌现出近百个以青年艺术家为主的美术群体,各群体的创作与展览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
在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双重逻辑的影响下,艺术被人为地划分为“新潮”与“传统”两大部分,青年人天然地被视为进步与创新的代表。而“新潮”中后期的“冷”调性,相较于前期和中期的“热”,似乎体现出更为深入的探索。隔阂与误解时有发生,甚至几方观点常常相当尖锐、对立,加剧了两者之间的断裂感。
但通过对历史现场的细致考察,我们发现,“热”与“冷”的差异更多地体现为形式层面的区别。多种语言风格与价值取向在彼时交融渗透,构成了更贴近现实的历史图景。“创新”的主体并不局限于青年艺术家,中老年艺术家中同样不乏突出的变法者。他们共同肩负起时代任务,既突破此前的禁忌、勇于创新,又在与既有艺术资源的对话中承担着继承与延续的使命。这也正是我们强调将“创新”置于“继承”之前的深意所在。
《经济观察报》:当时老中青三代对于同一时代命题(如“美”或“文化寻根”),为何展现了有截然不同却内在关联的回应?比如,展览中包括了上海艺术家余友涵与他的学生丁乙的作品,一位20世纪40年代出生、一位20世纪60年代出生,他们在同一时期对“抽象语言”各自做出了不同探索。一位追求赋予形式以人文意义,一位强调形式的纯粹与理性去意义化。这对师生的艺术选择,折射出怎样的代际差异、观念传承和选择分野?
刘、卢:在对20世纪80年代创作现场的探究中,我们发现,不同艺术家面对同一命题的创作,以及同一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之间,往往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这一发现超越了以艺术形式和风格来指认作品的惯性框架,提供了理解这一时期艺术背后多个重叠、交替思想脉动的批判性视角。
向往“自由创造”的艺术界在1980年初,继续将形式探索的“音高”推向“抽象”,进一步突破了“题材决定论”对创作的束缚。与此同时,文艺界对艺术自主性与审美本体的关注日益增强,创作者更加重视艺术形式、语言与个体表达的多样探索,这一趋势在青年艺术群体中尤为突出。这种创作趋势强调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探索艺术的独立价值与多样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此前文艺表达传统的明显区分。
由于各自的人生阅历、艺术经验和思想语境的差异,艺术家们在“抽象”取向中体现出不同的艺术观念与追求,由此在1983年前后形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抽象现场”。在这一时期,尽管在基本层面上达成了有关“抽象”的某种共识,但关于其内涵,以及对“内容”与“意义”的理解和追求,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可见(或不可见)的分歧。
与当时将抽象作为对写实主义和情节性绘画反叛手段的艺术家不同,余友涵认为抽象不仅可以承载内容,也应当具有思想内涵。他的“圆”源自现代抽象艺术的启发,正如蒙德里安的方块那样,意在把握和表现某种关于世界的本质。对他而言,形式探索与文化意义是构成作品的两个必要因素。将文化意义的追求落实到抽象形式之中,正是他与其学生之间的内在差异所在。
包括丁乙在内的学生们曾评价余友涵“有着独立的探索精神,相信自己的判断,也相信自己的直觉,不迎合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趣味,执着地进行‘纯艺术’的尝试,已成为我们学生心目中的榜样”。不过,他们对余友涵的理解中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误读”——或更确切地说,是以一种“去叙事”和“去意义”的心态来解读余友涵当时的抽象实践,并由此选择了各自此后的艺术之路。
在这些学生中,一部分人走向了以“无内容的纯抽象”形式实践为立足点的创作方向;另一部分则发展出以“去意义”为自我设定、具有观念倾向的抽象实践,例如丁乙。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20世纪80年代激荡的文化思辨留给当代中国艺术与社会的最重要遗产是什么?有评论说1980年代形成的文化价值判断如今成了一条“隐形的线索”——您如何解读这句话?
刘、卢:当代艺术在这些年间所经历的激进与迂回,预演了此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形态。在中国当代文化与艺术的演进轨迹中,既存在多元的探索,也经历阶段性的调整,其路径深受时代背景与社会发展节奏的影响。
在有限的社会空间中,历史所积累和形成的经验时而被压制、折叠,时而又被打开、重新激活。在较短的历史周期内,艺术的发展往往伴随着风格的更替、观念的冲突与价值的博弈;而从更长远的维度来看,这些现象体现出中国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回应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的整体逻辑。
离开这一具体情境,我们将难以准确理解战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
《经济观察报》:作为亲历者或研究者,您觉得重访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对当今社会和艺术界有哪些启示?21世纪20年代的我们正处于新的技术与社会变革期,您认为回顾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思想激情和探索精神,能为我们理解当下、想象未来提供什么借鉴?
刘、卢: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关于1980年代的追溯与论述,始终是当代学界持续关注的议题。在当代艺术领域,对于1980年代的理解长期依赖于当时亲历者对“新潮美术”的价值建构,而较少对这些叙述本身进行历史化与理论化的反思。此后关于1980年代的回顾,也呈现出不同立场下的叙述倾向,这一方面丰富了理解的路径,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有必要从多角度出发,历史性地还原那个文化现场的复杂面貌。
通过重访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得以看到时代变迁所掀起的巨浪及其边界。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或多或少都承载着这一代人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气质,同时也背负着时代投射而来的诸多象征性“大问题”。个体在敏锐感知时代潮起潮落的同时,如何在变动中不断铸造自身的“小我”,并将自己的艺术之舟,在时代的洪流中幻化为一艘巨轮,这对今天同样身处剧烈变革中的我们而言,是一次值得反复回望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