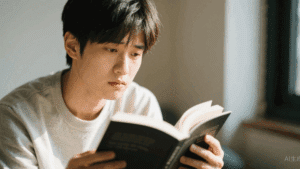“厂二代”观察:中国工厂接班潮
【来源:虎嗅网】
中美关税悬而未决。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华累计加征125%关税,叠加此前芬太尼关税20%,总税率达145%。5月12日,双方在日内瓦的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中美联合下调了115%的加征关税。中国制造在新一轮关税战里命运未卜。
摄影/俞俊春
“我们公司的人已经一个月没活干了。”
时间倒回5月1日,开了20多年外贸公司的姑姑对我说。她的公司几乎全做美国订单,当时都被喊停,只能等局势进一步明朗。“撑到年底看看情况,我倒是可以退休了,但我们员工怎么办?”
那是上海北外滩的五一市集,我在摆摊卖宠物玩具,姑姑带着小狗来探班,说起了如今生意的难处。今年,在原有工厂的基础上,我做了宠物品牌,来市集上赔本赚吆喝,被我妈哂笑之:“你们现在留学回来都去摆摊。”言下之意,书白读了。我读了不少书——中国文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哪样都不是拿来赚钱的专业,却是成为“海归废物”的不二选择。
紧随着“海归废物”这个身份标签在网上火起来的就是“厂二代”。如果前者代表着我这代90后在毕业后的迷茫与落差,那么后者就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延伸到了中国制造业的代际交接上,意味着新一轮的中国工厂接班潮正在发生。
从左到右:邱丁伟,方滨,陈志凯,施小寒
方滨,在工厂工作23年,是车间包装工。平时不上班的时候会看书练字。
陈志凯,当了10年的车间统计员和包装工,爱好打球。
邱丁伟,日前是工作6年的车间包装工,爱好打游戏。
施小寒,工作8年的车间发酵工,爱好喝茶。他说:“身残志不残,凭自己双手,在厂里好好工作,有一份稳定收入养家糊口!”
摄影/俞俊春
今天的中国工厂大多成立于1990年代和2000年代,部分由国企改制而来,部分依托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全球产业链而生。生于浙江宁波——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埠的口岸之一,我所熟悉的工厂更多是外贸工厂,我的父母在2002年就开办了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宠物用品工厂。
我的小时候——千禧年初——那个人人都想挤入全球化浪潮的时代,中外相交甚笃。姑姑有时会带美国客户来宁波,用我奶奶的话来称呼他们就是,从小抽烟的那个是摩尔,身高快两米的那个是电焊客户……摩尔经常给我带小礼物,礼物上刻了我的名字,就像大人要你露一手一样,我回赠了摩尔一幅我画的大熊猫国画,他打开卷轴,开心得很。
摄影/俞俊春
那是友好的记忆,却也有曝露贸易体系不公的时刻。多年以后,我读到安妮·埃尔诺写自己的母亲:“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那一刻,我会想起自己在课上盯着白人老教授几乎静止的嘴唇(被认为是优雅的发音方式),听他讲巴黎和会三巨头的博弈。而我的妈妈或许正看着报价单念叨,老外天天讲人权,一个产品几角几分计较来计较去,怎么提高员工福利?不久前,就有老外在参访时拿手机对着充棉机前的女工傻乐,棉絮落在她身上,像个雪人。
这会让我理解恩格斯为什么放弃继承莱茵河边的工厂而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体系。我没有成为恩格斯,我只是会在晚上抱着一个未竟的写作理想,深深认同着王国维引尼采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隔天就在社交媒体上为品牌写下“小狗生病了,她天天为它抄佛经”的引流文案。
摄影/俞俊春
这是我作为“厂二代”的记忆,也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作为世界工厂的切片,私人记忆写下来,就成了集体经验的一部分。如今面临关税压力,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中国工厂传承之时,也是存亡之际。为此我走访了跨越70后、80后、90后三个代际的厂二代,试图探究在这场接班潮里,为了延续一个企业,他们战胜过什么,又遭受过怎样伟大的失败?
70后:百年企业?希望吧!
摄影/俞俊春
去年,夏总把董事长之位传给了女儿,这一传就传了20年。
夏总70多岁了,腰板倍儿直,发型每天精心打理,见不到一根落下来的发丝。走进她的办公室,就看到佛像前供奉着经书里的七宝——珊瑚、玛瑙、琉璃……今天她心情特别舒畅,因为工厂里的“新路”修好了。年初有位大师来厂里说这大门的方向开得不对,但总不能几十年了另开个门,费时费力的,于是师傅就想了个法子,在花坛处开辟条小径,再摆上门柱,就算改了风水。路修了,财路也宽了。
服装产业是宁波奉化区的支柱产业,夏总的企业由改制而来,她也成了最早下海的民营企业家之一。2000年后,女儿就来了工厂学习业务。当时夏总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中东市场求购一批西服现货。她联系上了那人,人家就说你们有工厂干嘛不去迪拜开店?这人是个掮客,直接开价,50万美元,我帮你在迪拜开店。
那是2003年,夏总花了这钱,派女儿去迪拜做生意。今天她还扼腕道:“后来发现,开店20万美元就够了,那人收了我的钱,瘪三变小开。”所幸,生意实在好,当地贸易商三不五时就来店里进货,直接发到港口运往中东各国,好的时候一天能有十万美元的流水。夏总说:“当时多买黄金就好了,隔壁就是金店,买了堆红宝石、绿宝石,全贬值。”这样的光景持续了十来年,直到叙利亚战争爆发,迪拜的生意收了场。
摄影/俞俊春
小夏总回国后和母亲一起管理工厂,相较于母亲的雷厉风行,小夏总更擅长以理服人。夏总认为她和女儿“很互补”,在八字上她是乙木,女儿是甲木。在女儿经过海外历练、又投资过新能源企业后,夏总扶女儿上马扶了20年,终于把企业交接给了她。
另一位经营烘焙设备的王总,也和小夏总一样是70后厂二代,她与我母亲在同一个女企业家协会里,互相对于对方的评价都是“好学”。王总接手企业很多年了,她的故事没有太多起承转合,只有稳扎稳打。她财务出身,刚接班时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难以服众,她就去参加培训,慢慢学,一年年把产值做上去,2008年遇到金融危机没订单了,她就让大家学新的ERP系统,这些年碰上关税战,外贸订单不稳定,她就设法把品牌搭建起来。我想父母应该很满意她的成绩,她却说:“其实他们还是心疼,让女儿去管理一个机械设备厂,不容易。”
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约3.7年,即使美国、德国、日本拥有相当规模的百年企业,但全球也仅有5%的家族企业能传到第四代。如今夏总的外孙、王总的女儿都已毕业回国,一些中国民营企业来到了培养第三代接班人的时刻,初现迈向百年企业的可能性。提起成为百年企业,那个午后夏总望着窗外的“新路”,笑说:“希望吧。”
80后:我的接班失败史
摄影/俞俊春
我知道姜石(化名)有很多身份,拥有平台百万粉丝的大V是其中一个,但我从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几度接班无果的布料工厂继承者。
姜石的父亲是90年代的高材生,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后,转行做代理将法国的布料卖回中国,赚了第一桶金。贸易做得红火,紧接着他就在家乡办了工厂,织造布料,供货给成衣公司。生意做得早,也做得好,但没做到上市规模。
姜石将这归因于父亲“求稳”的性格,还有“他把精力花在谈女朋友上了。” 姜石18岁时,父母离了婚,此后父亲的妻子越找越年轻,三婚时,老婆比儿子还小几岁。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父亲总想让姜石来接手生意,喊了他三次,姜石哪一次都想逃。
姜石大学毕业后,在被安排进了深圳一家客户的公司,每月拿3800元工资,那时深圳平均房价才4800元每平米。自由自在过了两年后,他爸“开始作妖了”,觉得两年时间到了,儿子这时候该去读MBA了,姜石不从,父亲退一步:“那你就回家干吧。” 姜石无可无不可,这时父亲甚至找来深圳公司的高管同事来劝儿子:“打工是没出路的,你回家做点生意不比这强?我是没你这机会。”
第一次回家上班的半年中,姜石什么杂活都干,也跟着父亲去跑销售。同事都知道他是老板儿子,也知道他什么都不会。他不喜欢在做的事,没有工作积极性,“你叫我干嘛就干嘛,没事的时候就摸鱼。”
这时他看到7-11在上海招创始团队了,刚巧他了解过7-11创始人铃木敏文的生意理念,毛遂自荐过去,那个团队在人数已满的情况下要了他做管培生。这一来,亲戚们炸了锅,一听去便利店上班:“你放着你爸的班不接,非要去超市站柜台!”
那是外企来上海扎堆开公司的年代,姜石干了不到两年,做过收银小弟、店长,升了督导,去了总部做商品采购。这时父亲已经再婚,有了孩子,又来“请” 姜石回去接班了。父亲不会权威地命令他,只会非常客气地询问:“要不你回来帮帮我?”第二次回去接班不久后,父亲被诊断出结肠癌,去了法国治病,姜石不得不接手公司。
姜石口才很好,却说自己那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销售,很受挫。每次他去跑业务,临了业务没跑下来,人家让他捎话问他爸好。有一回跑了好多趟终于跑下来一个小单子,不够开机的,工厂卖了面子才给做了,还被师傅说,以后别接这种小单子了。姜石回想起来:“经验不足,其实给师傅两条烟就完事了。”某天在苏州开往客户工厂的路上,他划过一个念头:我今天在这里出个车祸,就不用去跑这个客户了,今天可以逃过。
等父亲治愈回来,姜石把权力交还给他,主动把自己边缘化。他管起了公司里的垂直媒体杂志,还做了玻璃饭盒的小创业,同时他开始在网上写食品行业的故事,像统一、康师傅老坛酸菜面之战,成了爆款内容。这是2015年,中国风险投资纷纷押注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O2O的高管从社交媒体上认识了姜石,他被邀请加入了一家大厂的创新业务部。
这一待就是五年,吃到大量的互联网红利之后,姜石也套到了一些现金。这五年中,父亲的工厂被拆迁了,索性关掉国内的生产线,专心做起贸易,在东南亚设立了一个简单的加工厂,在贸易战中生意反而做得更大,钱也挣得更多。
他爸换了第三个妻子,老婆很有事业心,他爸却想享受生活了,去年叫儿子回家当顾问:“你每周来三天,工资就按你在大厂的日薪给你开。”
面对这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接班,姜石铁了心说:“我不会来的,公司你不喜欢就关掉。”
他爸为难了:“这么大生意……一年还挣不少钱呢。”
摄影/俞俊春
90后:我爸是最幸福的老板
摄影/俞俊春
Eric来高铁站接我们那天,着急忙慌的,我们跟随眼前这个趿拉着勃肯鞋的人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停车场,保安正在吆喝:“这谁的车!”只见一辆SUV横在过道上,Eric赶紧招呼我们:“快!上车!”这就是“江浙沪奶厂太子爷”——随性、接地气、办事灵活。
他带我们去吃地道的牛杂面,在车上科普起了金华的奶厂发展史。Eric称自己的父亲为“老夏”,他的父母是大学同学,母亲毕业后被分配回了金华,老夏二话不说追了过来,承包了当地香料厂,赚到钱后在金华乳品厂二次改制时将它买了过来。20多年过去了,夏家在全产业链上拥有原粮贸易公司、饲料厂、牧场、牛奶加工厂、景区、酒店……Eric总结道:“牛奶就是这样,生意巨大,毛利巨低,无限接近于银行存款利率。”
90后Eric从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念完食品工程和农业后回国折腾了几个项目,“全干黄了”。第一个是希腊酸奶,买了设备做产品,却没地儿卖。第二个是咖啡馆,店面是他家的,空着也是空着,他还在小红书上晒起了今日盈亏,后来咖啡馆门口开始停车收费,彻底没生意了,他给粉丝留下一句:“不装了,我回家接班了。” 第三个是景区牧场,他和老夏去中国台湾、日本考察,设想开放牧场让游客来玩,在这里你认同我,去超市就会买我的牛奶,妥妥的一二三产业大融合。开干后,才发现投入太大了,“我又不是卖红酒,根本不能指望卖货来补贴。”
摄影/俞俊春
有那么三年,Eric一路折腾一路躺平。开咖啡馆和建旅游牧场那会儿,他“喝酒喝到金华350个代驾都认识他”,喝到第三年的时候,他喊代驾,人家说我拉过你好几次了。“喝了酒就爱吹水”,某天朋友就说你们喝的牛奶掺水吗,Eric的表演时刻到了,他在朋友的镜头里一通输出,顺带发上网,火了。自此,他就在网上给大家科普些牛奶工艺和知识,恰逢小红书推“厂二代”的流量,他说:“你在小红书搜牛奶,前三页必有我的大头。”
“我天生适合做账号。”看起来Eric爱出风头,表现欲强。其实,他想得挺深。他认为今天了解一个人最快的方法就是贴标签,而“厂二代”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身份标签。中文互联网上民营企业家第一波流量是从炫富中得来的,现在炫富失效了,大家喜欢看富人倒霉。所以跟厂二代相关的内容,往往伴随着接班的心酸与落差,反转了大家对富人的印象。
在乳品行业,过去老夏依托大品牌做代工,这几年却面临产能缩减的局面。刚好这两年超市做自有品牌,盒马、奥乐齐顺着流量都找了过来,Eric填补了这部分的产能和销售。在Eric看来,过去中国工厂是因为劳动力过剩完成了原始积累。但今天,“现代商贸业和金融服务业疯狂收割过剩产能,如果我后端没有形成销售能力,老夏会被剥削死。”此外,如今的消费趋势讲究个性化定制,品类越做越碎,与工厂的效率是相悖的,这就倒逼工厂去做柔性供应链。在很多工厂还没意识到这种商业上的隔层断代时,Eric和老夏已经完成了交接。在自家牧场,他感慨:“老夏应该是行业里最幸福的一个老板,因为儿子接得很顺。”
摄影/俞俊春
那天,我们从牧场走到牛奶加工车间。往常在牛奶盒子上印着4.0优质乳蛋白的娟姗牛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们轮番走进挤奶工作间,被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四根管子吸住乳头,牛奶汩汩流进容器里,管子自动松开了,它们的乳头被喷上了益母草,远远看去鲜红的,一群牛走了,换下一群。它们耳朵上别着黄色的标示牌,可以看出它是哪年出生的第几头牛。这个S级现代牧场里,奶牛在方寸之间忙着吃草、忙着被挤奶、忙着走向死亡。
摄影/俞俊春
加工车间是一幅高度自动化的场景,在无菌环境里,牛奶厂预处理的管路如现代工业的粗壮血管生长在厂房之中,罐装机像印钞机一样唰唰印着纸盒,后道包装车间里的工人则重复着把传送带上歪掉的空瓶扶正,这里24小时轮班,在车间与车间的过道里,摆着工人们的搪瓷杯,让人瞥见了这个乳品厂在上世纪的历史地位——年产值占金华四分之一工业GDP,60后金华人家里一定有亲戚在这厂里上班……
工厂的变迁见证了时代的向前,Eric接了班,这个工厂或许会再往前走几十年,虽然他觉得能把牛奶厂的事干好“挺拽的”,但也好奇自己当年要是学了新闻摄影,现在是不是就在上海刷着老夏的卡干记者,“那也挺酷的。”他盘算着:“我们这代人能早点退休吧,很难想象干到60多岁……我还想办摄影展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生活月刊,作者:生活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