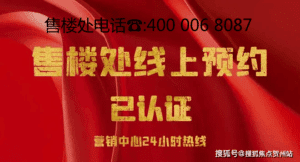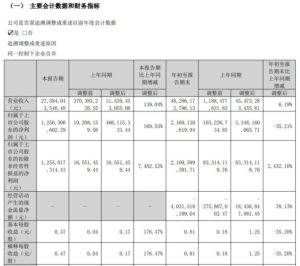想装空调的大学生,真的吃不了苦?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陈倚,编辑:L,题图来自:AI生成
你的夏天还好吗?
眼下正值酷暑,空调房几乎成了所有人的救命稻草。可一脚踏出门外,汹涌的热浪瞬间就会将人裹挟,仿佛置身巨大的火炉之中。此前,东北更是迎来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地表温度最高甚至达65℃以上。这种持续高温的天气,直接使东三省的线下空调销售额同比狂增几百倍。
气候变化,在高温红色预警频发的夏季,一些传统意义上并不算“火炉”的地区,大学宿舍还未普及空调。此前有新闻报道,一些学生们热到睡不着,只能在楼道、操场打地铺。
时间倒回二三十年前,特别对于大学校园而言,空调还是奢侈品。蒲扇、凉席、竹床,才是许多人对炎夏的共同记忆。尤其是在重庆、武汉、福州、长沙、广州这些现在赫赫有名的“火炉城市”上大学,熬过夏天就像是一种“生存体验”。
70后、80后,甚至是90后,熬过了宿舍没有空调的酷暑,也见证了城市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飞跃。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夏季气温也在逐年升高,不少人感叹“以前的夏天没这么热”。宿舍空调的有无,直接决定了学生们的生活舒适度。
对此,有一种论调常常出现:当年的大学生没有空调也能完成学业,今天的年轻人怎么就吃不了苦?
但是,时代的进步,本应带来更舒适的生活,当空调不再是奢侈品,而是炎热季节保证生活基本质量的必需品,高温就不是必须硬扛的苦。
我们尽可以回顾那些苦中作乐的夏天,但不意味着要让更年轻的人们,在时代进步中没苦硬吃。
人丹、清凉油与湿毛巾,是对抗暑热的“神器”
达摩流浪者,1993年~1997年在重庆上大学
1990年代,我第一次离开江苏平原,坐了两天两夜绿皮火车硬座,去多山的重庆上大学。
重庆的食物比夏天更早震撼了我。学校食堂几乎每道菜都放花椒,连炒青菜都不例外。起初,我总得把花椒一粒粒挑出来才吃。但一年后,我已经习惯了这味道,甚至爱上了花椒。
1994年,在嘉陵江边自制火锅。(图/被访者供图)
那时,只有教学楼、图书馆、食堂有吊扇,宿舍里连风扇都没有。每晚十点半断电,我们就开窗睡,摇着折扇。有时候太热,晚上睡觉前,我就用湿毛巾把床擦一遍,然后躺上去。
大三开学不久,听说一个外地新生因为暑热去世了。那周气温持续在39、40摄氏度,学校宣布停课一周,辅导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人丹和清凉油。男生宿舍走廊里,都是些只穿裤头的男生走去水房冲凉。
条件虽然苦,可是大家都是一样热的,别无选择。当时了解天气靠听同学收音机里的重庆经济台、交通台。除了听电台这种娱乐方式,爱音乐的同学还会用随身听,听齐秦、迈克尔·杰克逊、黑豹的磁带。
1995年,宿舍,桌上是收音机。(图/被访者供图)
刚上大学那会,我们只有周日是不上课的,后来才渐渐改成周六、日不上课。周六晚上,学校会同时开两场舞会,一场在食堂,一场在学生活动中心,入场费2毛钱。没课时,我们还会去校外的录像厅看录像,5毛钱一次。厅里有风扇,带空调的极少。三四十人挤在一起,竟也不觉太热,习惯了。
人生第一次吹空调是在一个暑假,我没回家,用A4纸写了“家教”两字上街摆摊。一位老先生想给他读初中的调皮孙子找住家家教,包吃住一个月400块,这相当于我一学期学费。
想着反正暑假也不回家,我就坐上他们家的“拓儿车”去他家看看(重庆人管奥拓叫拓儿车),当时重庆路上的私家车很少。路上,孙子跟爷爷说,如果给自己房间里安一台空调,他就不天天往外跑出去玩了。几天后,一台四千多块的格力空调就装好了。
我和小孩睡一屋,晚上一开空调,就到了清凉世界。住到第二周某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地上躺着个人,细看是孩子爸爸,原来他昨晚拖了凉席过来蹭空调。
三十年前,人的精神上很愉悦,压力小,时间多。虽然钱不多,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学校在沙坪坝区,周末会爬爬山或者去嘉陵江,江边有小孩玩耍,有人钓鱼,有人谈恋爱。
1996年,嘉陵江边。(图/被访者供图)
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吃火锅,是给舍友过生日。我们借了煤油炉,去菜市场买花椒、荤素菜,拎着炉子、热水瓶、锅碗瓢盆,走了半个多小时到嘉陵江边,煮起了火锅。
等到回学校,宿舍楼的门已经关了,于是我们在夜色中翻了进去。
大学时的夏天,有种青春永不落幕的感觉
Tina,2001年~2005年在武汉上大学
80年代的武汉,多数人还住在平房。每到傍晚,家家户户就把竹床、桌椅搬到门口纳凉。小孩在竹床上玩耍,大人在旁边吃西瓜,晚上聚在一起看电视。不少人甚至会整夜睡在外面,手里摇着蒲扇。
我家对面是江堤。小学的夏天,我每天晚上跟爷爷奶奶去江堤,凉席一铺,躺下就能看到星星,找课本上的北斗七星。有时候也和小伙伴在江边追小蜻蜓。
姑妈用绵绸给我做了几件无袖连衣裙,夏天就靠这两三件换洗,热了吹风扇、吃冰棍、喝妈妈熬的绿豆汤。我以前暑假还在大姑妈家天台上睡觉,躺在竹床上,盖块薄毛巾,点盘蚊香。清晨醒来,身上沾着露水。
90年代初,我家装了第一台空调,放在父母卧室里,基本只在晚上睡觉时开。等我上中学时,街上渐渐变了样:灰尘多了,车多了,工地多了,楼房多了,路灯也多了。天上的星星,似乎也没从前那么亮了。
大一入学,军训整整一个月,每天在烈日下暴晒,大家的衣领上都是白色的汗渍。从宿舍到训练场的路又长又晒,两旁树荫稀疏,我们还得拎着从开水房打的热水。
紫菘公寓开水房前。(图/被访者供图)
大学教室有空调,宿舍却没有。宿舍有个吊扇,每人还自备一个小风扇,夹在床头或床尾。天热了就会打开小风扇,常常听着风扇的呼声就入睡了。
武汉的夏天像蒸桑拿,只是站着不动,汗都会往下淌。而且早晚温差小,白天三十八九摄氏度,晚上也有三十摄氏度。暑假多数同学离校,我有个在报社实习的室友会留下。最热的夜晚,她就抱着凉席枕头去宿舍楼顶天台睡。天台中间有个铁皮水箱,旁边的位置得靠抢,去晚了就没了。宿舍闷热难耐,但天台上确实凉快不少。
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空调,再回想没有空调的日子,总觉得难熬。但如果从小没空调,那么它的出现,哪怕一点点改善室温,都让人倍感舒适。
现在回想,大学时的夏天,有种青春永不落幕的感觉。而如今的夏天,却仿佛只是年复一年的重复。
拍摄于2025年6月,华中科技大学西操场旁边,大四学生在摆摊卖书。(图/被访者供图)
只要风扇开着,夏天就没那么难熬
黄先生,2004年~2008年在福州上大学
厦门的夏季常有台风,台风真正登陆可能就几个小时,但登陆前风会越来越大,学校因此停课是常事。
等台风过境,天一亮,推开窗,外面树倒了一片,广告牌吹得到处都是。小学生们常常盼望着不用上学的日子,也期待着涨潮后跳进夏天的海里。
台风正面登陆厦门后,小区停车场的景象。(图/被访者供图)
我上中学后,城市建设飞快。1997年,我家从平房搬进了楼房,也第一次装上了空调。我和父母的房间各一台进口空调,这些空调到现在还在用。
父母那辈人节俭,只有热得实在受不了才会开空调。像我这一代,只要在屋里,不管是玩电脑还是写作业,白天也常开着。
福州的夏天和我老家厦门的夏天一样漫长。厦门靠海,湿度更大,福州则相对干燥些,但户外温度往往更高。像我这种怕热的人,4月份就换上短袖,一直穿到11月份。
我读大学那会儿,99%的大学宿舍是没有空调的。印象中最早给学生宿舍安装空调的是厦门大学,当时我们可羡慕了。那时的大学都是开放的,暑假我回家,进厦大打球,就可以看到学生宿舍楼外的空调外机。
大学宿舍。(图/被访者供图)
我学的是艺术专业,喜欢带着台傻瓜相机在福州市中心的老街区,像东街口这些地方闲逛拍照。我之前拍过厦门大学门口那条学生街,后来学校改建外墙,整条街拆掉了。这些老照片珍贵,倒不是拍的技术多好,而是它们定格了一代人共同的、再也回不来的记忆。
那时大学生活也简单些,经济和精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在宿舍,我用台式电脑上网,逛逛运动或本地生活的论坛。下课了就跟同学踢球,热了就光着膀子回宿舍,拿湿毛巾擦擦身子。实在热得不行,就去冲个凉。
记忆中,只要风扇开着,好像就没那么难熬。感觉现在的夏天,整体更热了。
小时候在海滨公园,喝着夏天标配汽水。(图/被访者供图)
记忆中的盛夏,带着平淡的美好
一席之地,2003年~2007年在长沙上大学
记忆中,二十年前的长沙没现在这么热。那时人口五六百万,如今翻了一倍不止,城市楼更密了,车也更多了。
2007年,贺龙体育中心。(图/被访者供图)
读大学时,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也不会在意天气的温度变化。热了就冲进宿舍阳台的洗漱间,拧开水龙头冲个凉水澡。周末要是热得实在受不了,就去附近有空调的网吧“包夜”,一晚七八块钱。
我不打游戏,爱上网看资讯,常逛天涯社区和新华网城市论坛,还在学校论坛当摄影版的版主。这个版块主要分享一些大师的摄影作品。除了睡觉,我基本都在线,在宿舍借室友的电脑维护版块,给好帖子加精、置顶,把灌水帖沉下去。
没课时,我总爱去“堕落街”。这条街很有名,夹在师大和湖大之间的桃子湖旁边,吃饭、唱歌、理发、精品店、网吧、奶茶店一应俱全,是附近大学生的消费中心。
我常去街上的“博爱音像”买磁带,正版一盒起步价十块钱,但里面最多的还是打口带,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可以把许多专辑封面都摸一遍。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买下店里所有的唱片,可惜如今这条街已不复存在。
大学时期听歌的卡带机。(图/被访者供图)
回想起来,那时大学宿舍没空调,我也没觉得多难熬。甚至毕业后的头三五年,我租的房子也没装空调。最便宜的是刚毕业时租的一楼杂物间,三百多块一个月。那屋子矮得抬手就能碰到天花板。春天一到,墙壁和地面都返潮,这种潮湿在夏天又变成了“优势”。
二十出头时年轻,对环境适应力强,也更能忍。长沙七、八月阳光毒辣,但视野通透,能见度高。
毕业后,我仍常带着相机泡在街头和湘江边。起初,我拍的大多是非主流视角,比如电线杆、芦苇叶、指示牌、楼梯间这些,后来有意识地开始记录那些即将消失的棚户区,赶在它们被拆掉前留下影像。我总不知疲倦,一拍就是一天。
长沙街头(很多照片洗坏了)。(图/被访者供图)
那时的长沙街头,报刊亭随处可见,在大学城还有专营过期刊物的。六月出的杂志,过两个月就能十块钱买三本了,我现在还收藏了很多,比如《新周刊》《城市画报》《我爱摇滚乐》。
搬家时整理出的旧杂志。(图/被访者供图)
总之,记忆中的盛夏,带着平淡的美好。我曾经荒废过一段时光,也感受过青春。伴随着相机里的五彩斑斓和耳机中的悦动音符,岁月就这样流淌着。
和舍友踱步的日子里,忽略了热浪
老鱼,2003年~2007年在广州上大学
电商刚兴起那几年,我在广州上大学。
大二时,我开了淘宝店。每天下课,走二十几分钟去校门口,坐公交到岗顶的电脑城拿货,蹲在档口打包MP3、U盘、蓝牙音箱这些数码产品。为了省点车钱,我就顶着太阳,拖着装满货的麻袋走到邮局发货。那个时候,广州大部分巴士有空调,少部分没空调的票价会便宜一些。
暑假,我还会把一些货搬到家里,打包好后,让我妈用自行车带到邮局发走,一个暑假能挣个两三千块。我家的两台空调是1995年买的,三千多一台。那时夏天似乎没现在热,但大家都心疼电费,偶尔能开空调就很满足。有时为了省电,一家人会挤在一个房间打地铺。
夏天,我妈会做酸梅汁,青梅泡盐后,加水冻成冰块,或者拿冰棍的模具做一些绿豆冰棍。学校饭堂也有夏季消暑食物,海带绿豆汤,一大碗一块钱;黄振龙的椰汁、火麻仁、龟苓膏比较贵,我偶尔才买。
学校宿舍没有热水器,洗澡只能去每层的公共卫生间打一桶热水,再回来兑一桶凉水洗。入夏后,我们也常洗冷水澡,每个人会准备一个几十块的小电风扇在床上,挂着蚊帐,倒也没人喊热。
我们大一大二住在五山公寓,宿舍离教室很远,走路要四五十分钟。有一段是土路,夏天风一吹,尘土就会混着汗水贴在脸上。过了那段路后,就有树荫了,大家常在树荫下有说有笑地走,也不觉得多热。
从教学楼回五山公寓时经常走的路,两边大树繁茂,夏天似乎也没那么热。有的路种满紫荆树,四五月时花开得正盛,像是走在画里,舍友指着它的叶子说,这也叫屁股树。(图/被访者供图)
晚饭后凉快些,我和舍友会去学校里的报刊亭逛逛,《新周刊》《城市画报》《三联生活周刊》,都是我常买的杂志,再慢悠悠走回宿舍。打开阳台门和走廊门,穿堂风一过还挺凉快的,大家会到处串门。哪怕宿舍没空调,现在回想,也只觉得美好。洗完澡,偶尔会去教室自习,那里有空调。
我至今还常想起那几年的夏天,我和舍友赶课走得飞快,生怕迟到。下课后不赶时间了,就慢悠悠踱回宿舍。四五月紫荆花开得正盛,我们边走边聊,也不觉得热,像走在画中。
紫荆树下的画面,在我的梦里还重现过好几回。
炎热的烦恼好像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占据多少位置,可能是因为当时我顾不上那些,只顾着在上课和赚生活费的路上狂奔吧。毕业后,我似乎再无一刻停歇,也再也没有那样的心境和机会,能在校园的紫荆树下或草坪上漫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陈倚,编辑: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