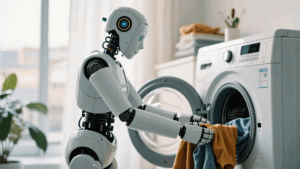日本的战后反思,为何不如德国深刻
【来源:虎嗅网】
中国和韩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亚的最主要受害国,在日本认罪的问题上,他们常常拿德国与之进行比较,并提出如下的问题:为什么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对自己的过去彻底反省?日本金泽大学专攻社会思想史和比较文学的仲正昌树教授在其著作《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二〇〇五年光文社第四次印刷的文库本)中,从“战后责任”“国家形态”“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四个方面,概述了德国和日本战后思想的演变。虽然这两个战败国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相似的历程,但在关键点上仍存在显著差异。仲正分析了这些差异,较为令人满意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仲正昌树著《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封面
一
仲正昌树认为,德国对其在纳粹时代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并实施了各种战后补偿政策,这种积极努力“克服过去”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日本由于在战争责任上态度暧昧,依然无法获得中国和韩国的信任——这种观点在日本国内时常被提及。
将德国作为“克服过去”的理想模式的主要是那些专门研究德国历史、德国思想、德国文学、德国政治等领域的自由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强调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非人性后,介绍战后德国为防止再次犯下这样的错误而做出的真诚且系统性的努力,从而突显出日本(政府)在对邻国的“侵略”问题上试图回避“道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于这些左派的德国模式论,右派也会提出“反驳”的观点:其一是日本没有像纳粹那样实施计划性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其二是德国的道歉并非出于纯粹的道德,而是在国际局势中权衡自身国家利益后,展开的战略性外交。日本著名的尼采专家、“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运动的核心人物西尾干二既肯定德国文化方面的“古老优良传统”,同时也强调其政治方面的现实主义“狡猾性”。
仲正认为自由主义左派的僵化态度是狭隘的,也不认为右派人士坚称的“德国不能成为日本战后责任论的模范”有什么道理,他提出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方式:作为“清算过去”的参考,日本学习德国一直以来的做法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德国比日本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更真诚地反省了过去的错误,而是因为日本和德国在被追究战后责任的内涵上有所不同,战后所处的情境也有很大差异。
仲正认为,德国之所以“真诚地”反省过去的错误,是出于一种被迫无奈:德国处于欧洲东西冷战的前线,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在与其他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时几乎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不同于德国,日本之所以敢“我行我素”的原因,仲正也做了分析:尽管日本也参与了东亚冷战,但与中国、韩国、越南不同,日本没有经历国家分裂或直接军事对峙。美国在东亚未建立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而是通过单独的安全保障条约与各国合作,因此无需明确日本在“同盟”中的定位,也无需创建日本与周边国家和解的框架。
那么,德国就没有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了吗?仲正认为,如果德国在特定环境下,能够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在“清算过去”方面获得比日本更高的评价,那么这种选择模式从结果上来看是合理的。
即使这些选择可能只是在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只要取得了一定成果,那么研究每个关键时刻背后的“德国式思维”便具有重要意义。这其实是作为德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仲正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以“清算过去”为中心,尝试比较德国和日本在过去六十年间的“战后思想”。此外,他也特别希望通过与德国进行对比,尽可能具体地阐释日本一直对“自身过去”的态度暧昧不清的原因。
二
一九四五年由联合国为德国的军事审判制定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的第六条,以及为日本的审判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的第五条,规定了三种应受审判的罪行:“反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战争罪”(war crimes)和“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但日本的战犯并没有根据具体罪名被判定有罪或无罪,而是被“综合地”追究责任。在判决书中也并没有使用“反人道罪”这个词。因此,日本是否犯下了“反人道罪”,对外没有明确的结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二页,后半部分为宪章第五条的内容(来源:imtfe.law.virginia.edu)
与德国被明确追究“反人道罪”并进行国家赔偿的措施相比,对日本类似罪行的责任追究和赔偿未得到实施。日本政府在相关审判中常以明治宪法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为依据,认为国家行为合法,无法追责,法院也认可这一观点。
然而,“反人道罪”在国际法中具有强制性,不应受到国家主权和“禁止事后法”原则的限制。仲正认为,日本法律界对这一罪名的接受度较低,这导致保守派知识分子认为日本与德国在战争罪行的追究上有本质不同。这种看法虽然片面,但德国因“反人道罪”而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表明这种外部“强加”也带来了积极的后果。
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战争责任上的不同看法,无论从左翼还是右翼的角度批判,在仲正看来都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来清楚地说明:德国就像是一个因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行而被彻底追究的原大恶人,最终对善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日本则像是一个罪行相对不那么明显的原小恶人,只受到部分追责,因此在善恶标准上形成了不彻底的认知。
仲正认为,德国和日本在探讨普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讨论对于两国的政治文化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德国,实存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为讨论国民战争责任奠定了基本框架。
一九四六年,他在海德堡大学开设了关于“罪责问题”(Schuldfrage)的讲座,主张反对“集体罪责”概念,强调每个个体应独立思考自己的责任,并提出刑事、政治、道德和形而上的罪责区分。雅斯贝尔斯认为,惩罚战争罪犯、赔偿受害者和进行道德反省应分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
仲正认为,日本缺乏像雅斯贝尔斯一样为辩论提供清晰思路的思想家。仲正还提到,一九八五年,时任德国总统的冯·魏茨泽克(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在德国战败四十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著名演讲《荒野四十年》,呼吁德国人正视纳粹罪行,特别是大屠杀,强调德国的加害者责任,并呼吁与邻国和解,倡导和平、民主和人权。“荒野四十年”的说法源自《旧约》,指的是摩西和以色列民族未能忠实遵守上帝的戒律,导致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前在荒野中漂泊了四十年。
仲正认为,雅斯贝尔斯和魏茨泽克在将法律与政治罪责的解决与个人内省分开处理时,展现了一种既基于基督教神学背景又非常务实的策略。尽管有深谙德国情况的日本左派人士认为,这种务实背后可能隐藏着德国式的“狡猾”,但仲正认为这种“狡猾”正是日本应当学习的地方。
三
仲正特别对战后日本的“一亿总忏悔”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日本在战后缺乏类似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家,没有将战争责任问题区分为不同层面进行详细讨论。例如,国家领导人、普通士兵以及一般国民各自应承担多少责任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探讨。
相反,日本的战争责任讨论被简化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图式:要么是全体国民有罪,要么只有甲级战犯有罪。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个人责任被模糊化,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经在德国所担忧的那样。
“一亿总忏悔”这一说法源自一九四五年日本皇室成员东久迩稔彦在记者会上发表的讲话,他强调日本战败是因为全体国民的“道义颓废”所致,而这种“总忏悔”更多是反思为何战败,并未涉及对他国的侵略罪行。这种内向、封闭的责任讨论只集中在国民内部,忽视了对亚洲受害者的忏悔和反思。
1945年8月30日,日本《每日新闻》围绕着东久迩稔彦“一亿总忏悔”的主张对其进行了报道(来源:mainichi.jp)
仲正认为,日本的“战争责任”讨论从一开始就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未能清晰区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政府为了维护天皇制,回避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讨论,最终导致责任问题模糊化。战后初期的“一亿总忏悔”论被批评为掩盖当权者责任的策略,强化了“普通国民=受害者”的观念,而未能深入探讨一般国民作为加害者的角色。
德国的情况却是:从支持公开宣扬反犹主义的希特勒上台,到开启纳粹大屠杀的过程,全体“国民”都应承担政治责任。为反犹太主义的纳粹国家而战是一场悲剧,绝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强行将其视为荣誉,无疑是在间接地认可纳粹思想,而这个纳粹国家早已灭亡。
在仲正看来,日本战后之所以对战争反思得不彻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作为国家核心的“天皇制”仍然存在,并且反对天皇制的声音不多,从而导致了一个独特的“战争责任”论。虽然政府和军阀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被忽视,但“为天皇而死是高贵行为”的武士道伦理仍然存在。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盟军最高司令部为了顺利统治日本,将天皇从战犯名单中去除,间接支持了这种伦理观。这导致了一个特有的战争责任论,即政府和军方首脑是加害者,而天皇和一般国民则是战争的受害者。
四
日本与其东亚邻国没有直接接壤,由于特殊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反日情绪未能通过市民运动广泛传播。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强调一般国民的受害者属性时,几乎没有受到“外部”的反对。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酵,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对日本未能承认加害责任的批评声日益强烈。
这种外部压力促使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逐渐从关注本国国民的受害转向反思对周边国家的侵害。尽管如此,如何在战争责任的语境中定位“一般日本国民”仍未达成共识。尽管左派逐渐加强了对慰安妇和强制征用劳工等历史问题的关注,但对国民政治责任的明确定位,仍未像德国那样得到系统性的讨论和承认。对于日本来说,由于在战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认知上从一开始就模糊不清,因此即便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其历史观也没有明显的改变。
在德国,关于普通国民在纳粹大屠杀中的责任问题曾多次引发讨论,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九六年由美国政治学者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提出的“戈德哈根之争”(Goldhagen-Debatte)。戈德哈根在其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纳粹大屠杀》中提出,大屠杀的“真正原因”并非仅限于希特勒及其亲信的思想,而是深植于普通德国人中的反犹太主义,这种情绪从十九世纪起就已渗透到德国文化中,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迅速蔓延。
在日本,虽然偶尔有关于一般国民“自愿参与体制”问题的讨论,但与戈德哈根之争中“反犹太主义与最终解决方案的关系”相比,缺乏同样级别的焦点,因此未形成系统性的广泛争论。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殖民化,以及九一八事变等历史事件中,一般国民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使得对国民加害行为的历史性研究变得复杂。
尽管近年来围绕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期间的狂热、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对朝鲜人的虐杀等问题的研究日益活跃,但仍未形成揭示国民在东亚侵略中的自愿参与程度的整体讨论框架。这种缺失部分源于日本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但要解决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战后问题,深入讨论是必要的。
仲正指出:“如果只是不断重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面对西欧列强的威胁时,自身也被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亡灵附身’这样程式化的抽象论述,恐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五
日本和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都背负了负面身份,但两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德国的第三帝国彻底解体,形成了全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日本虽然天皇的政治作用有所缩小,但天皇制仍然得以维持,新宪法明确了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因此,日本在战后并没有像德国那样经历国家形态的全面重构,而是在天皇制下进行体制转变,德国的新国家形态与大日本帝国的延续性引人深思。
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展出的《日本国宪法》复制品(来源:archives.go.jp)
日本宪法学者宫泽俊义为了解释战后日本宪法的合法性,提出了“八月革命说”,认为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接受《波茨坦公告》时发生了“革命”,主权由天皇转移给了国民。然而,这一理论的现实性和逻辑性受到质疑,因为日本并未经历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推翻君主制的革命过程,国民也未有实质性的主权转变的感受。
同时,战后关于“国体”本质的讨论也在进行。公共法学家佐佐木惣一认为:新宪法的颁布导致了政治形态上的“国体”变更,但他强调文化层面的“国体”并未受到根本性影响。相对地,哲学家和辻哲郎则主张,政治上的“国体”只是明治维新后形成的短暂历史现象,而日本文化传统的“国体”并未动摇。
这种文化论“国体”观回应了战后日本的模糊状态,尽管法律上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家”已不存在,但天皇仍是文化共同体的象征。
仲正认为,战败使日本失去了作为殖民地的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冲绳也被置于美军的直接统治之下。在战后残存的日本领土中,重新出现了一个接近“民族国家”状态的局面。尽管考虑到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这种“民族国家”并非百分之百纯粹,但以日语为母语、共享文化和“国体”观念的人们得以重新凝聚在一起,几乎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的身份认同反而得到了加强。而这个凝聚了较高文化纯度的“国民”的象征角色,恰恰由战前一直担任“国·家”家长的天皇来扮演。
六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日本,随着“冷战”体系的解体,小泽一郎等保守派政治家提出了“正常国家论”,也被称为“普通国家论”,意在推动日本成为一个在安全保障政策上更具主动性的国家,弱化宪法第九条的限制。然而,这一论调主要停留在口头上,未引发实质性讨论。此外,日本很少就国民身份认同与宪法的关系展开深入讨论,这与德国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进入九十年代后,日本思想界开始讨论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及单一民族神话等问题,涉及冲绳、阿伊努、在日韩国/朝鲜人等议题。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讨论通常未能与宪法框架相关联,也未能引发深刻的哲学性探讨。日本的大多数人默认“日本民族”是一个稳定不变的集合体,未意识到宪法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社会学家宫台真司批判明治以来的日本民族主义,提出以自由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但具体内涵尚未明晰,仍停留在批判层面。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德国在“历史学家之争”和“再统一之争”中,围绕历史与国民身份认同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性探讨。日本则主要围绕教科书的叙述方式展开争论,尤其是在一九九七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后,引发了关于爱国教育和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广泛争议。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思想界虽在民族主义等问题上展开讨论,但大多局限于介绍西欧论点或特定历史事件的解释。
作为德国文学研究者的西尾干二等人批评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自虐史观”,提倡建立“自由主义史观”,删除教科书中涉及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内容,试图呈现日本近代史的积极一面。这一运动引发了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曲解,可能导致战前民族主义的复活。尽管双方的争论激烈,但并未发展到涉及国民身份认同的深刻讨论。
总体而言,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争议反映了对国民身份认同的表面化关注,缺乏深刻的哲学性探讨。与德国不同,日本在宪法爱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之争方面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对立,也未能通过教科书叙述方式的争议真正推动深层次的历史观对立。
七
在《战败后论》中,加藤典洋指出,战后日本未能摆脱“人格分裂”状态,改宪派与护宪派在对美独立性与依赖性上的矛盾,导致日本既无法清晰道歉,也无法在国际上展现自主性。加藤建议,左、右双方应为日本战死者及亚洲战死者哀悼,但此提议的具体含义不明,引发争议。哲学家高桥哲哉批评加藤此举可能合理化民族主义,并认为通过“耻辱的记忆”复兴国家意识不可取。
在二〇〇〇年的《二十一世纪宣言》中,几位学者批判了日本的“寄生虫民族主义”,呼吁建立既不依赖美国也不回归传统民族国家的新战略,但这一战略的身份认同仍不明确。仲正认为,日本修宪派与护宪派之间的矛盾使得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清晰立场。
加藤在其随后的著作中进一步探讨了日本战后思想的“扭曲”,但未提供解决方案,最终提出只有认识到战前与战后的“断裂”,才能看清与“战争死者”的联系。加藤和高桥的讨论转向共同体意识,而非明确的国民身份认同。仲正认为,这种模糊性使得日本的身份认同问题始终无法清晰表达,左、右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均显得模糊不清。
仲正认为,德国和日本在战后政治思想上存在相似之处,均经历了从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但两国的关键差异在于:德国受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影响,成为“冷战”前线,并面对明确的现代性问题;而日本作为一个不完全认同“西方”的国家,其对现代性的批判显得模糊,常常认为与自己无关。
德国的历史背景使其对现代性的批判更具清晰性,而日本则因思想上的模糊性,难以形成统一的“现代/后现代”知识体系。尽管两国涉及相似主题,但德国的辩论通常更具体、更具现实意义。相比之下,日本在战后没有明确区分战前与战后的变化,这使得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至今难以清晰界定。
仲正指出,日本的思想模糊性既为其带来了某些灵活性,也限制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因此需要更深入地自觉认识这种双重性,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是我迄今读到的关于战后日本与德国思想比较的最具深度的著作。正是在这种相互比较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为什么日本在战后没有像德国一样对战争进行彻底反思。
(《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仲正昌树著,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二五年版)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5年8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李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