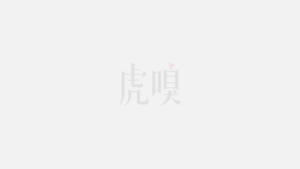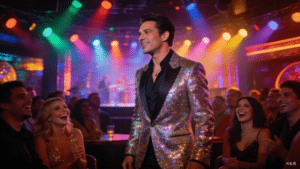85后,打造估值百亿企业,比肩马斯克Neuralink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 (ID:zhenghedao),作者:微澜
在全球脑机接口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人中,强脑科技创始人韩璧丞是值得关注的一位。
这位哈佛大学博士生,在移动互联网热潮席卷全球之际,选择了一条当时还鲜有人知的“硬科技”赛道,其创立的公司强脑科技也成为全球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领军企业,成功入选胡润研究院《2024全球独角兽榜》。
2025年年初,随着“杭州六小龙”的爆火,韩璧丞和强脑科技也进入到大众视野当中。作为六小龙中最神秘的公司,人们无疑对其有着诸多好奇。
也就在前段时间,正和岛案例探访携50余位企业家一同前往强脑科技,拆解了强脑科技的发展历程,并与强脑科技创始人韩璧丞及一众高管进行了深度交流。
从2015年创立强脑科技到成为“杭州六小龙”、估值百亿的独角兽企业,韩璧丞和强脑科技用了10年时间。直到今天,韩璧丞不仅在脑机接口行业上演了一段精彩的创业故事,也在持续改写着数千万残疾人的命运。
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和强脑科技正在创造历史。
决定研究“大脑”的哈佛博士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韩璧丞创业前的故事,那一定是“一个别人家孩子”的故事。
1987年,韩璧丞出生,从小韩璧丞就对生物医学有着浓厚兴趣,尤其是科技研发,在高中时拿过全国生物竞赛一等奖。
而这正是韩璧丞与脑机接口产生交集的起点。
在进入大学后,韩璧丞在本科期间先后加入四五个不同的国家实验室,参与了很多科研项目。本科积累下的大量实践经验与论文专利让韩璧丞获得了去西雅图医疗设备研究中心工作的机会。
2011年,韩璧丞正式加入了美国西雅图Fred Hutchinson研究中心,专注于药物研发和神经科学研究。
巧合的是,在Fred Hutchinson研究中心的隔壁就是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琳达·巴克博士的实验室,这也激起了韩璧丞对其研究成果的好奇,究竟什么样的科研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在时不时地串门后,韩璧丞弄清楚了琳达·巴克能获奖的原因,她研究的课题是动物或人到底怎么产生嗅觉,为什么能闻到味道,随后她破解了人体能闻到气味的秘密——人的鼻子里面有1000多个受体神经,花香等气味能激活不同的受体神经,传送电信号给大脑,让大脑产生不同的嗅觉。
当时诺贝尔颁奖词中还特别感谢琳达·巴克终于帮人类搞清楚:为什么人在春天闻到紫丁香的气味后,在冬天见不到紫丁香的时候,还能回想起它的气味。
这也让韩璧丞大受震撼,进一步激发了其对脑机接口的兴趣——既然嗅觉、味觉可以被解析、编辑,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未来可能通过对相关神经进行调节,只喝矿泉水照样可以喝出纯正的茅台味儿。
于是,为了进一步补强相关的专业知识,在2014年9月,韩璧丞入学哈佛,在入学第一时间,他就办了哈佛和MIT两个学生证。而在读博第一年时间,他不仅大部分时间在哈佛、MIT来回上课,还经常组织同学聚会开Party,而这也不是单纯享乐,而是为了结识脑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大牛,提前搭建创业班底。
韩璧丞在哈佛大学附近租了一个独栋房屋,并在2015年创办了BrainCo(强脑科技),这栋房屋就成了强脑最早的办公室,创始团队住二楼,一楼用于办公,地下室则用来做实验。
就这样,这位仅二十多岁的学霸,正式踏上了他所追求和热爱的创业路途,此后十年光阴都埋头于其中。
万亿蓝海起波澜
“脑机接口领域可能诞生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企业,在系统上根本地解决很多大脑相关的疾病。”正如马斯克在Neuralink最近一次融资的BP里面写道。
回顾脑机接口的发展,作为一项诞生百余年的技术,脑机接口产业有着无穷的潜力,到今天可能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1924年,德国精神科医生汉斯·伯格公开了在人类头盖骨上测量的电波图像,并将此图像命名为脑电图,从此人类脑部活动的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到了1943年,研究人员沃伦·麦卡洛克和沃尔特·皮茨共同发表文章,介绍了一项关于大脑基本单位“神经元”的新探索,将其中的生物原理简化为数学的本质概念,从而推动了神经科学的重要进展。
沃伦和沃尔特的方法关键在于抽象化,即通过剔除真实大脑中变幻莫测的电化学过程,将神经元简化为相对简单的信号交换。
某种意义上,这个发现相当于神经科学领域的原子裂变,它揭示了在整个大脑中重复出现的根本模式,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大脑可以被看作由基本单位“神经元”组成的大型网络,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通过将复杂的行为分布于网络中,我们可以快速高效地完成大量任务,并且可以不断学习新的任务。
作为一个由800亿~1000亿个神经元构成的巨大网络,人类大脑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已知宇宙中的任何其他事物,但其构造又极其优雅。
相比于汽车或手机由清晰区分的零件组装而成,大脑的所有神经元是一个个互相连接的微小单元,可在电化学传输中精细聚焦,尽管整个大脑中的神经元行为受到类似概念的支配,但神经元可以形成不同的网络,其排列和位置各不相同,可以应对各类挑战,如视觉、听觉、运动,甚至进行抽象思考。
而这也正为当下最火热的AI智能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神经网络研究,又叫深度学习)。
某种程度上,脑机接口和AI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底层逻辑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同时又像一条路分出来的岔口,最终它们也将在终点交汇。
2012年随着辛顿团队发表的关于神经网络的论文、英伟达的GPU超强并行计算能力和李飞飞团队打造的ImageNet数据集分别补足了深度学习的算法、算力、数据上的短板,此后人工智能迎来了产业化、狂飙猛进的时代。
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脑机接口技术却始终以一种稳定、缓慢、有序的速度前进:
1969年,第一只猴子通过食物反馈,成功学会了控制大脑神经元来触发仪表盘的指针转动;
1978年,第一例用于视力恢复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被成功植入人体;
1988年,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第一次被成功运用控制实物;
1998年,首例可用于运动模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被植入人体;
2014年,首例非侵入式脑-脑接口实验成功。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将两位研究员的大脑相连接,通过网络传输脑电信号,一位研究员的脑电信号可以直接控制另一位研究员的手部动作。
截至2014年,脑机接口技术还像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其发展成长给人无尽遐想,又让人陷入无尽等待。
也就在这一年,更大的机遇出现了。
在2014年6月的巴西世界杯开幕式上,一位28岁的高位瘫痪少年,在脑控机械战甲的帮助下顺利开球,这是脑机接口技术首次在全球舞台亮相。
更多的人才、资本和技术将目光也放在了这个领域。2016年马斯克正式创立Neuralink,进军脑机接口领域,再度引爆行业。
截至目前,脑机接口有三条技术路线,分别为:
侵入式,侵入式路线提供了非常高质量的信号,但需要手术植入,且监管门槛最高;
半侵入式,包括皮层电图、电极贴附硬膜等方式,手术创伤小;
非侵入式,通过穿戴设备采集脑电波信号。
马斯克的Neuralink选择的路径为侵入式路线。因为侵入式路线需要做开颅手术给大脑植入芯片,所以侵入式技术路线风险大,监管和伦理要求严格,更针对失明、帕金森症或者重度瘫痪等几类重症患者。
与马斯克不同的是,韩璧丞在创立强脑科技之初,选择了一条与之截然不同的道路——非侵入式路线。
但相同的是,在马斯克带领Neuralink成为侵入式路线的领军者时,韩璧丞也带着强脑科技在非侵入式技术上不断创造历史。
“疯狂洗头”,他做出了一只“手”
时间再回到2015年,在看过二十多个开颅案例后,韩璧丞就决定了要走非侵入式路线。
非侵入式要采集脑电-优化算法-强化大脑学习认知-最终是神经控物;也更易形成商业闭环:通过更大范围的落地产品应用,可以反哺底层技术研究。
不过技术壁垒也真实存在,如何进行高效的脑电采集,成为摆在韩璧丞面前第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由于人类的脑电信号非常微弱,相当于一节5号电池的一百万分之一,这意味着对脑电的检测难度不亚于收听50公里外一只蚊子在海浪边扇动翅膀的声音。
因此,为了研究大脑,韩璧丞需要佩戴一个非常复杂的脑电设备,并且它还需要抹脑电膏。而在涂抹导电膏前,要先洗头清理头皮上的油脂,之后才能戴上脑电帽,采集信号,做完实验后需要再洗一次头,一天起码洗四次。
这使得韩璧丞在哈佛的第一年洗了800多次头。
复杂的脑电设备,让韩璧丞意识到如果脑机接口要落地到实际的产品应用中,绝不可能要求用户一年洗几百次头,强脑科技必须要“消灭”导电膏,提升传感器采集信号精度。
也正是这个想法,韩璧丞遭遇了第一次重挫。
在创业第一年,韩璧丞想要做一套不用抹“导电膏”就能用的传感器和高精度便携化脑电仪器,结果连做三块集成电路板,都以失败告终。
到最后钱要烧完了,团队也走光了,只剩下他和一位技术负责人。就连技术负责人跟他提议:要不咱俩分一下设备,就此散伙?
脑机接口的梦想在当时显得如此虚无缥缈,难以实现。但韩璧丞想了半天,还是不甘心,最后咬牙自己再投一笔钱,又在外面找了一笔钱重整旗鼓。
此后,整个创业进程就相对顺利许多,2016年马斯克进军脑机接口行业后,大量的风险资本涌入这一行业,韩璧丞也就不用再担心融资的问题,甚至在后来,强脑还成为了脑机接口领域全球唯二完成超3亿美元融资的企业(另一家为马斯克的Neuralink)。
而在解决信号采集问题的同时,强脑也在研发着自己的第一款产品,智能仿生手。
之所以从“手”切入,还有一个插曲:
在创立强脑不久后,团队来了一个MIT的实习生,他当时做实验时把自己的右手给炸没了。
韩璧丞就在想,既然已经在研究脑机接口,那么有没有可能帮他做一个可以用神经控制的假肢。
最终韩璧丞团队帮助他打造了一个仿生手,尽管产品简单粗糙,但他却特别喜欢,每天都拿到学校给人到处展示。
在2016年1月的CES(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强脑展示了脑控智能手原型,引起了轰动。
到了2017年,强脑研发的新式电极材料——固体凝胶实现量产,攻克了脑电信号难以大规模精准采集的难点,使便携式脑电设备的单电极精确度达到专业级水平。
第一道难关终于解决了,但对于韩璧丞和强脑来说,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问题。
脑机接口的难点之一还在于,其作为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涉及到电极材料、电子工程、深度算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系统。
以强脑科技当时正在研发的智能仿生手为例,这个产品对制造精密度要求非常高,但美国本土很难找到合适的企业进行合作打样和测试。
为此在2017年,韩璧丞还专门回国考察了智能仿生手涉及的供应链。
当时每次回国,都有全国各地政府的招商人员找上门来。但只有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的考察团,是唯一一个前往美国拜访强脑的团队。
2018年年初,韩璧丞跟杭州考察团聊了3、4个小时,期间,考察团跟韩璧丞讨论了大量关于脑机接口的专业问题,甚至还提到了脑科学领域一些知名教授最前沿的研究。
这也让韩璧丞感受到了他们的诚意,很快就做出决定,回到杭州创业。
为此,杭州政府不仅为强脑科技提供了场地和资金支持,还在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保障、企业成长指导等多个方面给予了强脑团队支持。
也就是在2018年搬到杭州之后,强脑科技的智能仿生手产品研发与量产大大提速。强脑每在设计上做一次迭代,就能很快找到合作伙伴通过非常规的创新模式,快速完成打样和测试,极大地提升了开发效率:
2019年1月,强脑智能仿生手获得2019年CES创新发明奖;
2019年12月,它又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百大最佳发明,成为首款款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智能仿生手;
2020年,这款能够随“意念”活动的智能仿生手实现量产,成为全球首款实现直觉神经控制的量产智能义肢;
2022年,它获得美国FDA上市批准,打入美国市场。
此外,强脑科技还陆续推出了智能仿生腿、脑机智能安睡仪、脑机接口注意力训练系统、脑机社交沟通训练系统等多类别、多场景的脑机接口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2022年,强脑科技实现了高精度脑电设备10万台量产,从实验室级别的小批量生产跨越到规模化制造,这意味着强脑科技解决了脑机接口设备的精密度、一致性和成本控制等一系列工程难题。
每台设备都能稳定捕捉微伏级别的脑电信号,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在看到生产线上整齐排列的设备后,韩璧丞突然意识到他们不再只是做研究,而是真正在改变整个行业,让脑机接口从“小众科技”走向大众应用。
更伟大的梦想
从2015年创立到今天,强脑科技走过了自己的第一个10年,这10年里,强脑解决了从无到有,再从有到多、到强的一个过程。
正如前文讲到的,强脑科技是脑机接口领域全球唯二完成超3亿美元融资的企业,而在资本市场的高价值背后,是强脑用技术建立起的护城河,截至目前,强脑科技在脑机接口领域专利申请660余项,专利授权420余项,其中核心发明专利授权近230项,在全球脑机接口中也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韩璧丞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十年如一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很多时候科技没有所谓真正的秘诀和壁垒,技术只是一层窗户纸,关键是有没有一群人,愿意花十年的时间,走到窗户面前,把那层窗户纸捅破。”韩璧丞说道。
要开发最好的脑机接口,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长期主义的技术攻坚路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韩璧丞和强脑科技在三个方向上做了持续投入和突破:
第一是核心技术的打磨。
非侵入式脑电信号采集硬件正持续优化,在提升信号质量的同时兼顾佩戴舒适性;算法层面,神经信号解码的准确性也在不断提高。同时,具备触觉反馈能力的智能仿生手系统正在深入研发,使使用者在控制义肢的同时能够感知外部物体的触感、力度和材质,从而进一步拉近人机之间的感知距离,让用户真正“感觉到”自己正在操作的世界。
第二是脑部疾病领域的深入探索。
脑机接口技术正被持续应用于更多神经系统相关场景,包括注意力问题、孤独症、睡眠障碍等已落方向的迭代优化;与此同时,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等退行性脑部疾病的前沿研究也在开展,探索早期筛查、神经干预和功能训练等多层次解决方案。
第三是国际化战略。
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进合作,已在东南亚、中东、北美等地区推动脑机接口产品的本地化适配与验证。国际化布局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着眼于与全球伙伴共同构建开放、普惠、以人为本的脑机科技创新生态。
在韩璧丞看来,强脑科技未来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继续探索更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以及将创新出来的脑机接口产品普及给更多有需要的患者。
“未来5到10年内我们希望能够帮助100万肢体残疾人恢复日常生活、从家里面走出来,帮助1000万患有自闭症、多动症、老年痴呆和失眠等疾病的人康复,这是我们的使命愿景。”
对韩璧丞来说,当自己每看到一个因为强脑科技的技术而重返社会的人,就能更加确定,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真实和猛烈的影响”:
“当一个很多年没法拥抱亲人的小女孩,用我们的假肢第一次抱住母亲;当原本被困在家的残疾人,能像常人一样工作生活;当我们让亚残运会运动员用神经假肢点燃主火炬——这些时刻都在告诉我,我们不只是在研发一项技术,而是在帮助真实的人重获自由和尊严。”
想来这大概也正是科技的最大价值所在——让生命拥有更多可能性,让每一个人都能以一种更加平等(平权)的姿态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文章的最后,再分享一个韩璧丞经常跟别人讲的一个故事:
“在我回国创业时,搬到杭州人工智能小镇的办公室里干了半年活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办公室大楼前面的那条小路的路牌上,写着四个字——钱学森路。
而在看到路牌的一瞬间,我的感受是:来这里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宿命。我特别爱用这件事来鼓励同事,即使我们永远无法拥有钱老的睿智与能力,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为中国做一些事情。”
祝福韩璧丞,祝福强脑科技。
(感谢岛邻服务运营部的大力支持,权益交付与场景中心叶大若的沟通对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