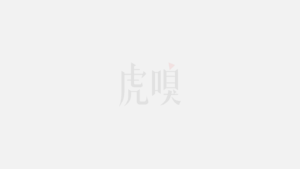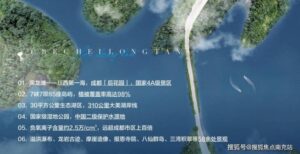职场断亲,年轻人的低电生存
【来源:虎嗅网】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职场正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偌大的办公室里,每天见面的同事,却鲜少面对面交流,甚至不知道彼此姓名。
格子间中,每个人像轨道中独立的小球,被制度和绩效推着向前,只在必要的节点短暂碰撞。一些年轻人发现,过去的“同事即半个亲戚”的现象已经消散。断亲,作为新一代打工人们的“节能模式”,正在成为当代职场的底色。
职场断亲一代
早晨八点进入公司大楼的一瞬,李莉低头,发现自己已经习惯性地握上拳头,紧闭双唇。
在北京这家金融类国企工作五年以来,李莉发现自己在职场变得越来越内向和封闭。她记得自己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时的样子,目明心亮、热忱外向。那时的她没有想到,如今的自己,为了不卷入过多漩涡,会在职场选择“断亲”,不再在工作中投入过多情绪。
当下,过去“同事即半个亲戚”的职场氛围正在消散。断亲,成了当代打工人的新底色。
据《半月谈》一文表述,所谓“断亲”,是指在工作中减少与职场的情感联结,阻断非必要的亲密关系。比如,能线上沟通就绝不打电话;给自己贴上“职场i人”的人设;不参加公司饭局,公事公办,不聊八卦等。
耳机一戴,谁都不爱。早晨九点半,杨林到了办公室。推开公司玻璃门的那刻,她发现同事和自己一样,拿着外卖回到工位,插上耳机,刷短视频、看剧,和外界隔离开来。
在她工位的对面,新来的实习生嘴唇动了动,似乎想打声招呼,但看到杨林已经戴着耳机,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转而发来一条微信:“杨姐,早。”
“能发消息,绝不说话”,已成为当代职场人的新社交礼仪。在一家私企单位市场部工作的许朗对此深有体会。
在公司,许朗时常感受到,线上的狂欢与线下的绝对静默,形成一种诡异的氛围。在公司几百人的大群里,同事经常在群里附和“收到!”“点赞!”“恭喜!”等词汇,各种表情包刷得飞快。但在实际的办公空间中,职场人之间经常避免眼神接触,如果狭路相逢,也会下意识躲开。
1997年出生于新疆的张依依,也感受到了自己工作以来的变化。2024年,刚毕业的她通过层层笔试和面试,从一百多人脱颖而出,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一家北京的国企。
那时,张依依立下壮志: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十年后在这里升职,坐上办公室最里面的位置。
刚入行的她热情洋溢。她总愿意主动提出建议,陪同事加班,力求自己经手的工作完美无瑕。但在一次次被同事背刺,反复遭遇领导的阴阳怪气后,张依依学会了闭嘴。
一次,领导给刚入职5个月的张依依布置任务,要求一周之内做好企业的宣传手册。她在办公室熬了几个大夜,终于把宣传手册赶出来了。但上级领导还是阴阳怪气地挑刺儿:“看得出来你用心了啊,但还是不行。”
几番分析下来,张依依觉得领导的不满,很可能是由于自己之前表达了过多意见,被觉得不好管教。她渐渐明白,她的热情在职场并非加分项。
图丨张依依拍摄秋天主题的素材,她力求完美
不久后,她学会了用职场的“标准话术”与人交往:用“玫瑰花”“抱拳”“厉害”等国企常用的表情包,在群内交流,每一句话后都加上“嗯”“哈”“呢”,以显示自己的客气。
表面上,她仿佛成了职场“老江湖”,实际上,她已不再想在工作外多说一句真心话。
智联招聘在2024年发布的《中国白领满意度指数调研》显示,76.8%的受访者坦言对职场社交心存困扰;其中,23.4%选择“能躲则躲”,26.9%则戴上面具强行“营业”。
当在职场消费过多人情精力,年轻人选择断亲来划定界限。
职场的变化并非一朝一夕。有专家学者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铁饭碗”单位仍保留着浓厚的集体主义氛围,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化加速,“单位人”逐渐转向“打工人”,情感逐步退场。在互联网与移动办公普及后,工作的边界进一步模糊,但并没有让职场同事之间关系更紧密,反而加剧了疏离。
“你不知道什么话题是安全的,”一位刚毕业就入职大厂的职场人在社交媒体上坦言,“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说。”
在某档综艺节目上,前著名经纪人杨天真说,“在工作中要有渣男心态,不必太在意领导和同事的评价,这样在工作中才能举重若轻。”
早年工作中,杨天真曾以公关危机处理能力强,被同事认为是一个心机很重,手段很多的人。她试图向同事解释自己并非如此。但杨天真越解释,同事对她的误会就越深。
这种对“言多必失”的恐惧,催生了一种高度程式化、去人格化的职场。它充满了“家人们”“小伙伴”“拉齐”“赋能”这类表面上温暖的集体词汇,但背后的情感温度却趋近于零。
Z世代的节能模式
“工作就是工作,别的交情我真的再也不想经营了。”杨林发现,当自己与职场关系过于亲密时,任务也会越来越重。以往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也会慢慢堆积到自己的身上。
2023年,23岁的杨林进入一家文化行业的私企。刚入职场,同事开口求助,她几乎来者不拒。行政忙不过来,她就提着拖把在走廊上来回一起拖;领导喊一声,她顺手把茶具洗得锃亮;同事临近下班还在为文案焦头烂额,她主动留下来校对。
在她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次踏进职场,她觉得自己应该努力证明“有用”,才不至于被忽视。她甚至会去刻意维护关系:午休时拉着同事去楼下奶茶店,节日时主动为大家团购零食,群里发消息总是第一个回应。在周末,她还约同事一起去玩密室逃脱,唱KTV。
她想把“同事”经营成朋友,像在校园里那样,建立一种“集体”的感觉。
那时的杨林还不知道,自己对职场抱有的情感预期,和当下的环境有些脱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职工大多数生活在“单位制”之中,吃饭、住房、子女入学都与单位紧密绑定,个人与集体难分彼此。但在今天,年轻人面对的是企业流动性高,劳动合同短期化的职场环境。个体与组织之间,是随时可能解除的雇佣关系。
很快,杨林发现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工作,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记得一次会议上,她帮同事补充了一句遗漏的数据,事后却被经常一起去KTV唱歌的那位同事抱怨“抢了风头”。还有一次,她替人修改PPT到深夜,第二天却连一句“谢谢”都没有等来。更让她困惑的是,那些曾经和她一起去奶茶店的同事,下班后转身就组了新的饭局,没再叫上她。
图丨杨林和同事经常组局的顶楼酒吧
经历多次同事“背刺”后,杨林逐渐意识到,职场并不是校园,这里讲求效率,每个人都在计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
杨林也渐渐学会了算计。午饭不再刻意邀约同事,群消息只回工作相关的内容,下班后直接关掉电脑走人。她也说不清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其实也挺好,”杨林后来对朋友说,“这样更省力,也不会受伤。”
进入国企工作时,张依依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属。应聘阶段,单位不仅报销了往返路费,面试当天甚至有一大排领导来面试,张依依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这里会是自己大展宏图的地方。
入职后,新人培训完善,每位新员工还配备了两名助教老师。刚开始,同一批进来的新人感情很好,常常结伴上下班,哪怕有人加班到很晚,大家也会等着一起拼车回家。外向直爽的张依依更是如鱼得水,下班后话题随意、氛围轻松,她很享受这种热闹。
然而,她没有想到,自己直来直去的性格,在讲究“和气、平衡”的国企文化里,并不讨喜。
入职培训时,领导交给她一个企业宣传片。为了尽善尽美,她花了三天时间拍摄、剪辑。可领导却评价她“做事太慢”。张依依忍不住当场解释理由,却没想到这句话在领导眼中成了“不听话”的标记。
张依依长相甜美,性格活泼,在职场还保持着喜欢化妆的习惯。一个月后,她被选去表演舞蹈。她以为这是认可,却因此引来其他部门的闲言碎语。有人甚至向她领导“提醒”,让张依依这个“显眼包”低调点;张依依当时很困惑:“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在工作任务中,她也频频被批评:后来,她才意识到,或许是自己在职场里太过较真,把个人性格过多带入了工作。在入职5个月后,转正前夕,她选择了离开。
图丨压力大的张依依独自去KTV解压
那些最初把同事当家人的年轻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单位制”逐渐消解、用工关系不断流动的今天,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不再是昔日那种稳定的互赖,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自己投入过多私人情感,往往只会模糊边界、加重责任,未必能换来相应的回报。
清华大学教授甘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八个字形容如今高校中的年轻人,“疲惫、焦虑、未老先衰”。
甘阳很明显感受到近10年来大学生精神风貌的变化。在刚进校园前,学生们的眼睛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但只要几年后,他们的眼神就开始黯淡无光。
这种“未老先衰”的氛围也延续到职场环境中。2025年,海外社交平台上兴起一个热词:“Z世代凝视”。它描绘的是职场中的年轻一代在面对前辈或上级时,所呈现出的那种目光空洞、表情凝滞、反应卡顿的状态。
面对网络热谈,Z世代为自己正名:他们并非刻意疏离或消极对抗,而是不愿再为社交假面透支情绪。
在感受到职场的过度消耗与情绪劳动的无效后,Z世代选择以“节能模式”面对职场。
社交媒体上,一些年轻人觉得这是自己对职场现实的一种妥协。正如埃塞俄比亚的一句古老谚语所说:“当一个遮天蔽日的地主走过你的田地,聪明的农夫会深深鞠躬——然后偷偷放屁。”
这种“偷偷放屁”的生存策略,如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所表述的“小反抗”:消极怠工、假装顺从、装傻、阳奉阴违等等……这是Z世代对外部职场高压最小成本的回应。
断亲之后
“现在大家交心越来越少了。”某互联网大厂的部门总监林枫这样描述他的团队。
林枫今年36岁,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了十余年。他的职业履历几乎与互联网行业的起落同步:从2015年最初的创业公司写代码熬通宵,到2019年被大厂招揽负责一个核心业务线。他见证了互联网发展初期的“狼性文化”,也经历了后期的行业收缩。
作为技术出身的管理者,他记得,早些年团队成员常常加班到深夜,大家一起在会议室头脑风暴,白板上写满五颜六色的标注。
但随着这几年远程办公普及、团队核心成员更换后,同事在视频会议中多数时间保持沉默,打开摄像头的人寥寥无几。
一次新产品脑暴会的场景令他记忆犹新。会议链接里,十几个摄像头齐刷刷关闭,视频聊天框里一片空白。当被要求发表意见时,大多数人只是打开麦克风,简短地说“没意见”或“挺好的”。
在林枫看来,目前团队成员的职场“断亲”规避了大部分的人际关系,但也成功避开了团队创新的可能。林枫觉得,当员工们只愿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公司“分外之事”缄口不言,那么公司中的集体智慧终将枯竭。
另一大代价是协同成本的上升。林枫每天工作8个小时,但有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花费在线上的协调沟通上。产品页面修改,需要在前端、后端、设计、测试的多个群里分别艾特相关人员,等待回复,再反复确认。“如果大家坐在一起,五分钟就能当面说清的事,现在需要线上拉扯一整天。”林枫抱怨道,任何流程上的纰漏都可能阻碍项目的推进,而项目延迟林枫负主要责任。
对员工而言,“职场断亲”是一种职场生存策略,但可能付出的是心理代价。
一位网名为“阿茶”的银行职员描述了她的一天:“上班就像上台演戏,扮演一个情绪稳定、永远礼貌的机器人。下班后摘下面具,常常会觉得更累,因为一整天都在‘演’,已经没有能量做真实的自己了。”
这种“功能健全、情感缺席”的状态,是许多“断亲”职场人的共同写照。工作占据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却未能带来有意义的社会连接。
早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便提出了大城市人的“囊泡化”现象。在他看来,城市人将个体从复杂的外界中自我隔绝开来,从而为自己保留一片内在自由空间,以应对都市生活中的重压。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城市人们发展出愈发封闭和迟钝的“囊泡化”人格,将自己边缘于环境之外。
而在当下,“职场断亲”并非一代人的性格突变,而是个体在时代结构性变化下的适应性反应。在动荡的生存背景下,“打工人”的首要目标从“寻求发展”变为“确保安全”。与同事保持距离,意味着减少犯错的风险,可以避免陷入人情与利益纠葛,但这同时也边缘化了自己。
张依依对此深有体会。“断亲”之后,她明显感到自己成了“职场边缘人”。一次在办公室,她起身起来活动的功夫,无意中瞥见了办公室中四个平级的同事,偷偷瞒着她建了一个三人小群,同事经常在小群里吐槽领导,分享生活琐碎、育儿经验等等。
在线上,张依依被三位同事物理隔离,在线下,面对同事的日常分享,她也插不上话。张依依仍渴望和同事们好好相处。可这种渴望越真切,落差也就越刺痛。
*应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作者:郑彩琳,编辑:罗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