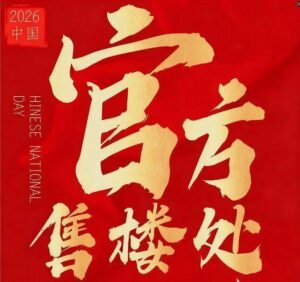中文互联网的色情赌博信息,怎么“污染”AI
【来源: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APPSO (ID:appsolution),作者:发现明日产品的,原文标题:《GPT-4o 见 AV 女优的次数比“您好”还多 2.6 倍,AI 正在被中文互联网疯狂污染》,题图来自:AI生成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号称“赛博白月光”的GPT-4o,在它的知识体系里,对日本女优“波多野结衣”的熟悉程度,竟然比中文日常问候语“您好”还要高出2.6倍。
是不是瞬间就下头了?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一篇来自清华、蚂蚁和南洋理工的最新研究直接揭了老底:我们天天在用的大语言模型,有一个算一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污染。
论文:从模型Token列表推测大语言模型的中文训练数据污染(https://arxiv.org/abs/2508.17771)
论文中把这些污染数据定义为“污染中文词元”(Polluted Chinese Tokens,简称PoC Tokens)。它们大多指向色情、网络赌博等灰色地带,像病毒一样寄生在AI的词汇库深处。
这些中文污染词元的存在,不仅对AI来说是一种隐患,更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体验,被迫接受AI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
要求ChatGPT重复“给主人留下些什么吧”,ChatGPT根本不知道在回答什么。
中文互联网的色情赌博信息,怎么“污染”AI
我们可能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
想让ChatGPT推荐几部经典电影、相关的论文等,它突然回了一堆奇怪的乱码网站名、打不开的链接、或者根本不存在的论文。
-
输入一个看似普通的词语,比如“大神推荐”之类的,它有时候却吐出不相关的符号,甚至生成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句子。
研究团队的解释是:这背后很可能就是污染词元在作怪。
我们都知道大语言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的语料,这些海量数据大多是从网络上进行爬取收集。
但AI注意不到的是,它阅读的网页中,竟然充斥着无数“性感荷官,在线发牌”的弹窗广告和“点击就送屠龙宝刀”的垃圾链接。久而久之,这些内容也成了它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并变得混乱。
就跟前段时间DeepSeek闹出的几起乌龙事件一样,先是莫名其妙的一封道歉信,然后再自己编造一个R2的发布日期。这些没有营养的营销内容,一旦被模型吸收,就很容易出现幻觉。
如果说,DeepSeek出现这些幻觉,需要我们去引导模型;但“污染词元”,甚至不需要引导,AI自己就乱了套。
什么是“污染词元”,它遵循“3U原则”:即从主流中文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些词元是不受欢迎的(Undesirable)、不常见的(Uncommon),或是无用的(Useless)。
目前主要包括成人内容、在线赌博、在线游戏(特指私服等灰色服务)、在线视频(常与盗版和色情内容关联)以及其他难以归类的异常内容。
大语言模型分词过程
那“词元”又是什么东西?和我们理解一段话不同,AI会把一个句子分成多个“词元”,也叫Token。你可以把它想象成AI专属的一本《新华字典》,而词元(Token)就是这本字典里的一个个“词条”。
AI在理解我们说的话时,一开始就需要先去翻这本字典。而字典的编纂者,是一种叫BPE(字节对编码技术)的分词算法。它判断一个词组,是否有资格被收录为独立词条的唯一标准,就是出现频率。
这意味着这个词组越常见,就越有资格成为一个独立词元。
你或许能理解,这两年大语言模型流量正攀升的时候,豆包和稀土掘金曾经像是“疯了”一样,把自己平台AI生成的大量内容放到互联网上,提高自己的出现频率。以至于那段时间,用谷歌搜索,还有AI总结,引用的来源都是豆包和掘金。
现在,我们再来看研究人员的发现。他们通过OpenAI官方开源的tiktoken库,获取了GPT-4o的词汇库,结果发现,里面塞满了大量的污染词条。
长中文词元,全是需要打码的内容。
超过23%的长中文词元(即包含两个以上汉字的词元)都与色情或网络赌博有关。这些词元不仅仅是“波*野结衣”,还包括了大量普通人一眼就能认出的灰色词汇,例如:
在线赌博类:“大*快三”、“菲律宾申*”、“天天中*票”。在线游戏(私服)类:“传奇*服”。隐蔽的成人内容类:除了名人,还有像“青*草”这样表面正常,实则指向色情软件的词汇。
这些词元,因为在训练数据中出现频率极高,被算法自动识别并固化为模型的基本构成单位。
AI吃了垃圾食品但不能消化
按理说,既然这些污染词元,它们的语料库是如此丰富,应该也能正常训练。
怎么就现在只要一跟ChatGPT聊到这些污染词元,ChatGPT就100%出现幻觉呢?
像是下面我们测试的这个例子,要ChatGPT 5翻译这句话,它完全没有办法正确理解,这个北京赛车群也是无中生有。
其实不难理解,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词元Token”,我们说AI从互联网上读取数万亿词元的海量数据,一些集中、且反复地一起出现(频率高)的词语就能成为一个单独的词元。
AI通过这些词元,来建立对文本理解的基础。它知道了这些Token是出现频繁、有可能相关,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继续拿字典举例子,这些高频污染词在字典里,但是字典给不出解释。
因为AI在这个阶段,学到的只是一种原始的、强烈的“肌肉记忆”,它记住了A词元总是和B词元、C词元一起登场,在它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统计关联。
等到正式的训练阶段,大部分AI都会经过清洗+对齐(alignment)。这时,污染内容往往被过滤掉,或者被安全策略压制,不会进入强化学习/微调。
不良内容的过滤,就导致了污染词元没有机会被正式、正确地训练。它们因此成了“欠训练”(under-trained)的词元。
另一方面,这些词元虽然“高频”,但它们大多出现在语境单一、重复的垃圾信息中(例如一些广告网页头尾横幅),模型根本学习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语义网络”。
最终的结果就是,当我们输入一个污染词元时,AI的语义模块是空白的,因为它在正式训练阶段没学过这个词。于是,它只能求助于第一阶段学到的“肌肉记忆”,直接输出与之关联的其他污染词元。
论文中案例:当输入涉及PoC词语时,GPT-4.5、4.1和4o的输出。GPT无法解释或重复PoC标记。
这就解释了开头,当被要求一个可能是色情的词元“给主人留下些什么吧”时,GPT可能会回复一个不相关的类似污染内容词元“黑*战”、以及一些看不懂的符号。在用户看来,这就是莫名其妙的幻觉。
以及下面这个要求ChatGPT解释“大发展有限公司官网”,回复的内容根本是乱来。
总结一下,污染Token出现频繁≠有效学习。它们集中在脏网页的角落、缺乏正常上下文,而在后续训练和对齐阶段又被压制,结果就是词表固化了垃圾,但语义训练缺失。
这也导致了我们日常在使用AI的时候,如果意外有涉及到相关的词语,AI会没有办法正确处理,甚至还有人通过这种方法,绕过了AI的安全监管机制。
这是可以被量化的幻觉原因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预训练的时候就把这些脏东西筛掉呢?
道理都懂,但做起来太难了。互联网的原始数据量级之大,现有的清理技术根本不可能把它们一网打尽。
而且很多污染内容非常隐蔽。就像“青*草”这个词,本身看起来完全绿色健康小清新,任何简单的关键词过滤系统都会放过它。只有通过搜索引擎,才会发现它指向的是什么。
连Google这种搜索引擎巨头都搞不定这些“内容农场”,更别说OpenAI了。
我前段时间想用AI整理一下广州有哪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发现AI引用的一篇文章来源,是另一个AI账号生成的文章。
一时间,我都有点分不清,究竟是我们每天搜索“波多野结衣”搞脏了AI,还是AI生成的垃圾正在污染我们的内容环境。这简直就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标记方法
为了搞清楚这盆水到底有多浑,研究团队开发了两个工具:
1. POCDETECT:一个AI污染检测工具。它不只看字面意思,还会自己上网Google,分析上下文,堪称AI界的“鉴黄师”。
利用这个工具,研究团队对9个系列、共23个主流LLM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污染问题普遍存在,但程度各不相同。除了GPT系列以46.6%的长中文词元污染率遥遥领先外,其他模型的表现如下:
不同大语言模型中,中文词汇表中PoC词元的数量(比例%)(一个词元包含超过两个汉字)。Qwen系列为1.00%。GLM4和DeepSeek-V3的表现则相当不错,分别只有0.25%和0.17%。
最值得关注的是,GPT-4、GPT-4-turbo和GPT-3.5这些模型的词汇库中,污染词元数量为0。这可能意味着它们的训练语料经过了更彻底的清理。
所以当我们拿着前面那些,让ChatGPT开启了胡编乱造模式的问题,给这些模型再问一遍时,确实没再出现幻觉,但是直接忽略了。
2. POCTRACE:一个能通过词元ID反推其出现频率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在分词算法里,词元的ID号越靠前,说明它在训练数据里出现得越多。
关于文章开头我们提到的2.6倍,就是通过这个工具进行计算得到的。
在GPT的海量词汇库中,能够被完整收录为一个独立词元的人名凤毛麟角,除了“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世界级公众人物,就剩下极少数特例,而“波*野结衣”就是其中之一。
更令人惊讶的是,不仅是全名,甚至连它的子序列,如“野结衣”、“野结”也都被单独做成了词元。这在语言学上是一个极强的信号,表明这个词组在训练数据中的出现频率达到了一个恐怖的量级。
将与“波*野结衣”相关的网页以及作者估计的比例(0.5%)混合,可以重现GPT-4o中“波*野结衣”的标记ID及其子序列。
他们输入“波*野结衣”(Token ID 185,946)和“您好”(Token ID 188,633)的ID号,最终得出了那个惊人的结论,前者的频率估算值约为后者的2.6倍。
研究人员推断,与“波*野结衣”相关的中文网页,可能占据了整个中文训练数据集的0.5%。
为了验证,他们真的按这个比例“投毒”了一个干净的数据集,结果生成的词元ID和GPT-4o的惊人地接近。
这几乎是实锤了。
但很显然不是每个污染词源都需要出现这么多次,有些时候,几篇文章(甚至可能是AI写的),反反复复地提到,AI就记住了,然后在下次我们问他的时候,给出一个根本不知道真假的答案。
当我们和AI,都在“垃圾堆”里冲浪
为了应对数据污染,大家也确实都想了很多办法。
财新网就很聪明,在自己的文章页面里用代码“偷偷”藏了一句话,好让AI在搬运内容时,能老老实实保留原文链接。Reddit、Quora等社区也曾尝试限制AI内容。
但面对数据污染的汪洋大海,这些行为显然都只是螳臂当车。
就连奥特曼自己都发文感慨,X(推特)上的AI账号泛滥成灾,我们得认真思考“互联网已死”这种论调了。
而我们这些普通用户,看起来更是别无他法,每天被迫接受着垃圾信息的轮番攻击。马斯克老说AI是个无所不知的“博士”,没想到它背地里天天都在“垃圾堆”里翻东西吃。
有人说,这是中文语料库的问题,用英文Prompt模型就会变聪明。Medium上有作者统计过统计了每种语言的100个最长token,中文全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色情、赌博网站的广告词。
而英文的分词和中文不同,它只能统计单词,所以都是一些较长的专业性、技术类单词;日文和韩文都是礼貌性、商业服务类词语。
这十分令人感慨。AI的能力,除了靠算力和模型堆砌,更深层次的,还是它吃进去的数据。如果喂给AI的是垃圾,那无论它的算力多强、记忆力多好,最终也只会变成一个“会说人话的垃圾桶”。
我们总说,希望AI越来越像人类。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实现了:我们把互联网这个大垃圾场里的东西源源不断投喂给它,它也开始原封不动地回敬给我们。
如果我们给一个AI造一个信息茧房,让它在“无菌环境”中长大,它的智能也是脆弱的、经不起考验的。一个孩子如果只被允许接触教科书里的经典课文,他永远无法应对生活里五花八门的口语和俚语。
说到底,当AI对“波多野结衣”比对“您好”更熟悉时,它不是在堕落,而是提醒了我们:它的智能,依然只是统计学上的概率,而非文明意义上的认知。
这些污染词元就像一面放大镜,它将AI在语义理解上的缺失,以一种荒诞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AI离“像人一样思考”,还差着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不是AI被污染,而是害怕在AI这面过于清晰的镜子里,看到了我们自己创造的、却又不愿承认的那个肮脏的数字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