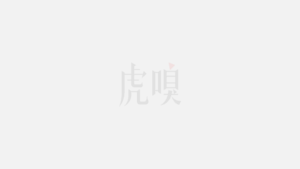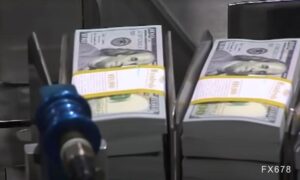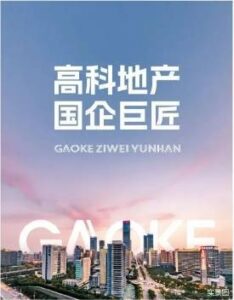美国中产“坠落”
【来源:虎嗅网】
“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
这句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励志鸡汤,不仅是无数中国家庭信奉的“成功学”圣经;事实上,也是支撑一代又一代人奋斗不息的“美国梦”内核。
然而,历史进程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让这句承诺在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同步破产。
在我们身边,“中产破产”、“消费降级”,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而就在大洋彼岸,曾经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美国中产阶级,也在从安稳滑向危机的深渊。
中产阶级,这个本该与安全感、体面生活和上升希望紧密相连的词汇,开始与“濒危物种”画上等号,是时候正视一个严峻的现实了:支撑现代社会运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嬗变;而命运青睐有准备的人。
下面,我们将结合《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深度报道,以及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其著作《再见,平庸时代》(Average Is Over)中的前瞻性分析,深入探讨这场全球性的中产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的35岁职场危机,还是科罗拉多州被裁员的微软前高管,以及在布鲁克林靠美甲贴片节省开支的时尚博主,类似的故事不是个人命运的波折,也不是哪个国家的特色,而是时代浪潮下,无数中产家庭命运的共同缩影。
一、从安稳到危机:美国中产的“坠落”实录
“这是一个信心降温的夏天。”
《华尔街日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开篇便为美国中产的处境定下了悲观的基调。曾经,他们是经济乐观情绪的主要贡献者,但如今,他们的信心指数却与低收入群体一道,跌入了谷底。
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层——年收入约在5.3万至16.1万美元的家庭,对经济与未来的态度,在短短数月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晨间咨询(Morning Consult)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利尔(John Leer)形容这种转变“如同坠下悬崖”。这种坠落感不是个例,而是众多鲜活案例共同谱写的现实悲歌。
案例一:消费降级的时尚博主
30岁的玛丽亚德莉兹·圣地亚哥(Mariadeliz Santiago),是布鲁克林的一位美妆时尚博主,年入6万美元。这个收入水平,在许多人看来足以过上光鲜亮丽的生活。然而,经济的寒气同样吹到了她的身上。由于品牌方削减广告预算,她的付费合作项目规模正在缩水。
“感觉你对当下发生的一切几乎无能为力,”她说。为了省钱,她正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消费降级”:不再去美甲沙龙,改用美甲贴片;每周数次的外出就餐,锐减到每月一两次;甚至连早已预订好的、花费3000美元的波多黎各演唱会之旅,也被迫取消。
她的经历是无数美国中产消费行为的缩影。从沃尔玛购物车里越来越少的非必需品,到折扣零售商达乐公司(Dollar General)涌入的更多中层家庭;从IHOP餐厅里顾客开始选择更便宜的菜品、减少饮料消费,到科尔氏(Kohl’s)百货里人们纷纷转向更廉价的服饰……
这场自上而下的消费紧缩,勾勒出美国中产阶层日益紧绷的财务状况。
案例二:被房贷与失业困扰的资深员工
如果说消费降级是中产阶层抵御经济寒冬的“软着陆”,那么失业和房价则构成了更致命的“硬冲击”。
56岁的杰里·埃施(Jerry Esch)在微软工作了20年,年薪高达20万美元,是标准的高薪中产。然而,今年夏天,他被裁员了。如今,他每天的目标是申请五份工作,同时还要应对不断上涨的房贷、税收和保险成本。他焦虑地发现,工资的涨幅远远跟不上“荒谬”的房价。
他的女婿,35岁的奥斯汀·奥德尔(Austin Odle)同样面临失业的困境。尽管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上一份工作的年薪也达到12万美元,但他依然觉得“没有安全感”。在被裁员前,他差一点就能还清家里累积的7万美元债务。
“我以为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仍然感觉自己没有喘息空间。” 奥斯汀的这句话,道出了无数中产阶层的心声。他们遵循着“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传统路径,却发现通往安稳富足的阶梯,正变得越来越陡峭,甚至随时可能断裂。
“美国梦”的褪色:努力不再是成功的保证
这场信心危机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信念动摇。《华尔街日报》的另一项民调显示,近70%的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美国梦已经不再成立。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悲观情绪跨越了党派、性别、年龄和学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者,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蓝领工人,绝大多数人都对未来持负面看法。
“我有些难过,”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马奥尼(Neale Mahoney)说,“我们国家的一大超能力就是永不枯竭的乐观主义……它是创业精神和非凡成就的燃料。” 而现在,这股燃料似乎正在耗尽。
从前,人们相信,即便自己这代人过得辛苦,下一代的生活也一定会更好。但如今,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此缺乏信心。他们看到的是,子女们买房、创业,甚至仅仅是成为一名全职父母,都比自己当年要困难得多。
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感,正演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即便是那些财务状况尚可的家庭,也同样被未来的不确定性所笼罩。
亚特兰大的克里斯托弗·基舍尔(Christopher Kishel)夫妇,年收入高达35万美元,却因为高昂的房价和房贷利率,不得不暂停了换大房、生二胎的计划。“你可能过得舒适,但却达不到你想要的状态。”
这种“舒适但不放松”的状态,精准地描绘了中产阶层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他们尚未坠落谷底,却也清晰地看到了天花板。向上的通道日益狭窄,向下的风险却无处不在。
这正是全球中产阶层焦虑的共同根源。
二、“中产破产”:一场遥相呼应的中国式困境
如果说美国中产的困境是一场缓慢的“温水煮青蛙”,那么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中产破产”一词,则更像一场雷霆,炸响了我国中产阶层心中积蓄已久的焦虑。
中产破产,看似夸张,其实它并不完全是指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破产,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破产感”。它描绘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良好的教育背景,是社会公认的“人生赢家”。
然而,在高昂的房价、沉重的教育成本、脆弱的职业前景和不可预知的未来风险面前,他们所谓的“体面生活”,如同一座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随时可能坍塌。
中式中产的“三座大山”
与美国中产相比,中国的“新中产”虽然没有经历过漫长的阶层固化历史,但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却背负起了同样沉重、甚至更为独特的压力。
1. 房产:财富的压舱石,还是人生的绞索?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是中国家庭财富积累的核心引擎。拥有一套或几套房产,是定义中产阶层最简单粗暴、也最有效的标准。然而,当房价涨幅远超收入增长,当“六个钱包”才能凑齐一套房的首付,房产的意义就变得复杂起来。
房子,曾经是财富的象征,如今是沉重的枷锁。每月数千甚至数万的房贷,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无数中产家庭的头顶,让他们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生病,不敢有任何“任性”的念头。一旦遭遇裁员或收入下降,房贷就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教育:赢在起跑线的“军备竞赛”。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在中国中产家庭中根深蒂固。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他们不惜重金购买学区房,报读各种昂贵的辅导班、兴趣班,甚至早早规划好了海外留学的道路。
这场围绕教育展开的“军备竞赛”,不仅耗尽了家庭的大部分收入和精力,更制造了无穷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对阶层滑落的恐惧。他们深知,自己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教育,让下一代能够继续留在这个阶层,甚至实现向上的跨越。
3. 职业:35岁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
“35岁被优化”,曾经是那么的荒诞不经,如今已经见怪不怪;对于曾经引以为傲的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中产来说,简直成为了必然的命运。
技术的快速迭代、商业模式的不断颠覆,让曾经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变得不再可靠、脆弱不堪。
许多人发现,自己多年的经验和积累,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更年轻、成本更低的劳动力所取代。这种职业上的不安全感,叠加对未来的普遍悲观预期,共同构成了“中产破产”感的核心。
从“美国梦”到“中国结”
对比中美两国中产的困境,我们能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是圣地亚哥的消费降级,还是埃施的失业焦虑,亦或是基舍尔夫妇“舒适但不满足”的感叹,都能在中国的中产群体中找到无数共鸣。
这种相似超越了国情和制度,因为,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所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是一场结构性的、由技术驱动的社会大洗牌。
经济学家泰勒·考恩,被誉为“无所不知的男人”,曾经提供过一个深刻的、理解这场危机的分析框架。
三、再见,平庸时代:技术浪潮下的“大分化”
泰勒·考恩在他的著作《再见,平庸时代》(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中,提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的观点:我们正在告别一个“平均”的时代,进入一个“大分化”的时代。
他认为,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将从根本上重塑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结构。过去,技术进步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大量新的、处于中等技能水平的岗位,从而支撑起庞大的中产阶层。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
智能机器正在“掏空”中间层
考恩的核心论点是,智能机器最擅长替代的,正是那些遵循明确规则、可重复性强的“中等技能”工作。这包括了大量的文书、行政、初级分析、甚至部分编程和设计工作——而这些,恰恰是过去几十年中产阶层赖以生存的岗位。
未来,劳动力市场将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顶层:与智能机器协同工作的人。 这部分人拥有顶级的创造力、战略思维、复杂沟通能力和与机器协作的能力。他们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来放大自己的产出,从而获得极高的回报。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新贵”,是财富金字塔的顶端。
底层:为智能机器服务或从事机器无法完成的工作的人。 这部分人主要从事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务性工作,如护理、手工劳动、情感陪伴等。这些工作的薪酬水平将长期受到压制。
而被“掏空”的,正是中间地带。那些曾经依靠一份稳定、体面的白领工作就能维持中产生活的人,将发现自己的岗位要么被自动化,要么薪资停滞不前。
他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努力向上攀登,成为能够驾驭机器的顶层精英;要么向下沉沦,与低技能劳动者竞争有限的岗位。
这完美地解释了我们在《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看到的现象:高收入者持续消费高端跑鞋和头等舱机票,而中低收入者则在折扣店里寻找价值。经济的分化,最终体现为社会阶层的断裂。
未来成功的关键:成为“不可替代者”
在考恩描绘的未来图景中,“平庸”将不再是一种安全的生存状态。要想在“大分化”的时代立足,个体必须努力成为“不可替代者”。他提出了几种关键特质:
-
与智能机器互补的技能: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简单地掌握一项技能,而是具备与人工智能协作、利用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我们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
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律性: 在一个日益复杂和分散的工作环境中,能够自我驱动、信守承诺、注重细节的品质将变得极其珍贵。
-
营销和沟通能力: 无论你的想法或产品多么出色,将其有效地传达给他人、并说服他们为此买单的能力,都至关重要。这是一种机器难以替代的、基于人性的软技能。
考恩的理论虽然描绘了一个略显残酷的未来,但它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它警醒我们,“努力工作”的定义已经改变。
过去,努力工作可能意味着在一家公司兢兢业业、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而未来,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不断地自我革新、跨界学习,努力让自己成为那个无法被轻易复制和替代的人。
四、敢问路在何方:在不确定时代中重新进化
面对席卷而来的时代浪潮,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无法独善其身。哀叹和焦虑无济于事,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深入理解这场变革的本质,并积极寻求应对之策。
对个人而言,需要从“求稳定”转变为“求进化”:
1. 拥抱终身学习,构建“T型”知识结构:
在单一技能迅速贬值的时代,我们需要在保持一个领域深度(“T”的垂直一竖)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T”的水平一横)。
这种跨界的能力,是产生创新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基础。主动去学习编程、数据分析、心理学等与机器协作密切相关的知识,将成为一种必需。
2. 投资“软技能”,强化人性优势:
创造力、同理心、领导力、团队协作和复杂沟通能力,是人工智能短期内难以企及的领域。这些基于人性的“软技能”,将是我们区别于机器的核心竞争力。花时间去阅读、去交流、去实践,刻意锻炼这些能力,比单纯追求一份高薪工作更为重要。
3. 重塑财富观念,降低风险敞口: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传统的“高杠杆”生活方式(如背负巨额房贷)风险极高。我们需要建立更加稳健和多元化的财务结构,增加被动收入来源,减少不必要的负债。学会理性和审慎地消费,将安全感更多地建立在自身的成长和能力之上,而非外部的物质符号。
4. 建立强大的社会连接,打造小共同体:
无论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一起找工作的翁婿,还是我们身边相互扶持的朋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抵御生活风险的重要缓冲。这不仅是情感上的慰藉,更意味着信息、机会和资源的共享。
最后:告别幻想,直面现实
中产阶层的衰落,以及“努力工作就能成功”这一信念的动摇,是这个时代最令人不安、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宏大叙事。它不是某个国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一场由技术革命驱动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结构重塑。
泰勒·考恩所说的“平庸时代的终结”,并非宣告世界末日,而是提醒我们:过去那种按部就班、追求安稳的发展路径已经难以为继。未来属于那些能够拥抱变化、持续学习、并能与智能机器共舞的“进化者”。
对于每一个身处时代洪流中的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告别对传统成功范式的幻想,放弃对“稳定”的执念,并以一种更加清醒、更加坚韧的姿态,直面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大分化”时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懂经,作者:也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