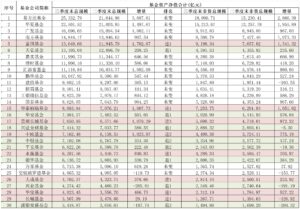从英国名校毕业后,我在市场调查里干着最脏的活
【来源:虎嗅网】
朋友说,我快把英国的各种工作都“体验”一遍了。是的,在伦敦辗转漂泊的日子里,我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怀着一个天真的念头——也许在英国就能够用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养活自己,并支持自己的艺术事业——我决定在这待两年看看。
这就是“我在英国打100份工”系列的由来。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份工,或许是最特殊的一份。它让我这个LSE毕业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潜入”伦敦的千家万户,窥见这座城市最真实的生活;也让我过去学的所有理论,在现实面前接受最残酷和荒诞的检验。
从LSE社会学系毕业之后,我没想到我在英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这样的:背着沉甸甸的电脑和资料,挨家挨户地按门铃,讲一段滚瓜烂熟的开场白,被拒绝,搓一把脸,再敲下一扇门。
Market Research Interviewer(市场调查采访员),这是我的岗位的正式名称。三个单词分开都看得懂,合起来却令人摸不着头脑。它的描述倒是很理想化:你将负责企业或政府的调查项目,采访当地住户。不过,它还有另一个名字:cold calling,意味着向没有预期准备的陌生人发起“类推销”的沟通。
然而,我当时对此毫无概念,以为这份工作能恰好供我发挥专业技能。面试时我提到,在做社会学研究时,我最享受的环节就是做采访,因为我对了解别人的故事和看法很感兴趣。
彼时我没想到,原来我干的活真的只有“采访”这一环节。读研的时候,作为一个researcher,研究者,我需要对一项研究的全部环节负责,从提出研究问题、文献综述、设计方法,到招募访谈、分析数据乃至撰写论文。但在这家大公司,调查的每个环节都被精密切分给专人来做,我们的劳动成果也从自身剥离。作为最基层的“田野”(field)部门的工作者,我只负责拿着设计好的采访稿,敲门,提问,上传数据。至于这些数据最终如何被使用、得出什么结论,统统与我无关。
我才明白,现代社会分工已将一切工作流水线化了,市场调查和车间生产没有根本区别。而我的工作,则是这条流水线上最廉价的一环:按200次门铃,可能只有10个人接受采访。我们要咽下无数次被拒绝后的沮丧、被kpi驱赶的焦虑、只身一人面对挫折的孤独,最终得到的,是一纸没有底薪、只给佣金的零工合同。
不过,尽管被异化得如此深刻,这份工作并非全无好处。正如我的trainer Rizwan说的那样,它最好的一点是能让你了解伦敦形形色色的人。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让我蠢蠢欲动,甚至能将心灵上的重压和遭受过的冷眼一时抛之脑后。它给了我一张通行证,允许我光明正大地潜入伦敦的各个角落,窥见这个城市千奇百怪的众生相。
一、“我的孩子已经五岁了,任何小事都会影响他们的未来”
我接到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为英国广播电台(radio)收集用户反馈的研究。我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反应是,现在还有人听电台?比起有些过气的调查方式,这课题过几年就能进博物馆了。而我的任务便是说服地址列表上的住户参与采访,了解他们的基本职业和家庭信息,然后请求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记录每天的电台收听情况。
第二周,我拿到新的地址就心里一咯噔: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市政公寓的地址。Rizwan之前说过,他最不走运的时候,就是在这些公寓里工作——只有3个人接受了采访。这些房屋叫做Council flat, 大部分是政府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出租给生活困难的人们居住的。
我正是在地址列表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栋council flat里面认识了Leyla。这是一个三合院布局的“小区”,院子里栽种着一棵巨大的樱花树。时值春末,樱花落了一地,走进去像踏上了一张柔软的粉色地毯。左手边的楼还在装修中,固定在墙外的脚手架还未拆除,像是打入楼房的钢钉。孩子们就在这些比他们高一个头的脚手架上攀爬、跳跃、追逐,冲进楼里,不知轻重的脚步要把楼梯都震碎。
整棵树相当宏伟,但花已经落得差不多了。
楼梯间散落着一些快餐盒,闲置的健身器材和装修木板。借着一侧窗户的阳光,能看到天花板上墙皮掉落,霉菌蔓延,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烟味。
在三小时里爬了8层楼却只找到1位受访者后,我几乎是万念俱灰地敲响了角落里的门。
一个戴着粉色浴帽的黑人女孩拉开一道门缝。我照例用那句“你听广播电台吗?”作为开场白。她说不听。我心中叹气,一般来说,不听广播电台的人更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因为她语气温柔,我还是追加了一句:“不听也没关系,您的意见同样重要。只需要10分钟?”
“sure,没问题!”她爽快地答应了,“要不你进来采访吧?”
我很感激她邀请我进去她家,还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厨房很乱,你别介意呀,我刚给小孩做了晚饭,还没收拾。” 她家没有客厅,我们就在厨房采访,一些炒鸡蛋剩在平底锅里。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灶台上光着脚走,时不时抓一把玉米片吃。她把手机调到TikTok让小孩拿着,送到另一个房间。
采访中我了解到,她22岁,没有上过大学,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两个小孩。问卷上的一些很基础的问题,在这里都显得困难:比如使用互联网的程度。她说,这里信号非常糟糕,没有装Wi-Fi——Wi-Fi太贵了。
我又确认了一遍,她确实完全不听电台。我不禁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呢?”
于是,她说出了标题的那句话。
“你也看到了,我的小孩已经四五岁啦,已经到了生活中最细微的小事都能决定未来的时期——决定他们未来想做什么工作,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会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如果有什么新东西,我都会去了解,无论他们有没有帮助……”
我心里一沉。我一边喃喃地附和着,心中不免泛起一阵苦涩。这样熟悉的话,在异国他乡的一位比我年轻两岁的母亲嘴里听到,我又被命运的回旋镖击中了。小时候我也经常听父母说,细节决定成败,一个小习惯改变孩子的一生……但是,说到底,这些看似头头是道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人生中又起到多少作用?又有多少只是一针安慰剂,给予我们掌握命运的幻觉?
我多想跟她说,你拼了命想了解所有的信息、所有的细节,又有什么用呢?他们的未来早已写好了,当他们在脚手架上攀爬、抱着手机刷抖音时已经写下了,你要记住多少细节,才能改变他们的未来?
那时,过去一年在LSE课堂上学到的所有理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所谓“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文化习性”(habitus)的广度和普适性。课堂上我们曾讨论上层社会如何通过口音、品味、教养等一套具象化的密码完成资本传承,确保后代畅通无阻的未来。但我仍难以想象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一幅怎样的光景。他们度过了孤独但物质丰富的富二代童年吗?还是接受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但至少我知道,应该不是只见过窗边的樱花树,刷着算法推荐的短视频的童年生涯。
三合院的其中一栋楼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她说,You’re very kind to me. I’m really grateful. 这是我能说的真心话。出于无法向她揭示这残酷骗局的愧疚心理,我补充道,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家长。
她听到后好像很开心,笑着说,很少从我的朋友那里听到这样的评价,他们总是说我不太负责。
是的,当时我心里算了一下,她生孩子的时候可能才刚成年。不知道这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尽管心情很沉重,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当我背上沉甸甸的背包离开时,我仍然悄悄祈祷:Leyla是个善良的人,希望她能教育出同样善良的孩子,命运会垂怜她。
二、伦敦折叠:当我开始给社会“分级”
这份工作确实让我认识到了伦敦各式各样的人。不仅如此,在不同区域进行采访的难易程度也反映了不同街区的贫富差距。为期一天的导师Rizwan告诉我,要像侦探一样,通过观察房屋外观——花园植物的修建情况、垃圾桶整洁度等——来判断屋主的生活状态,进而调整我们的游说策略。
在联排别墅街区,我的成功率比在政府救济房高出近一倍。一位中东的工程师在接受采访时还会好奇,为什么在他们这个区域经常有人来上门采访,我们公司是怎么确定采访名单的。在温布利附近的中产印度家庭里,一位父亲兴奋地表示,我知道你们公司,我做过很多采访研究啦!
带花园的联排别墅。
第一周上班时,一位和蔼的老太太体贴地邀请我到她家坐坐。访谈中,我了解到她是一位负责特殊教育的教师,专门解决孩子的学习障碍等问题。她也是第一个关心我工作是否艰难的人,“你干这个活多久啦?……每个年轻人起步都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你今天也有好运气吧!”
只要提起伦敦,人们想到的是伦敦西区彩虹般的房子,秀气的花园,还有惬意的下午茶。但就像世界上所有大城市一样,伦敦也有它的城中村。两百磅月租的政府救济房,没人会将它印刷在明信片上。
这里的住户大部分都是少数族裔,也就是我们BAME(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要么就是领救济金的白人。在这里做采访,要面对的是警惕和戒备,是猫眼透过的光线骤然消失的几秒,和门后锁舌扣紧的声音。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些调查是干什么的,仅仅询问一下是否听电台,却得到粗暴的回答,“不要到我家里,我不需要任何产品!”或者是跛脚的老年妇女下来应门没好气地说,“我是听电台,但是你们这些公司只会偷窃我的信息,想无时无刻监视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
有时,将调查问卷上看似简单的问题问出口好像都有些冒犯。年龄、婚姻状况、职业状况,几个标签就能把一个人在社会阶级的坐标系中确定下来。在他们无法看到的电脑屏幕上,他们被归为社会分离的最底层——失业、靠救济金生活。一位独居多年的老爷爷告诉我,他已经十年没有出国旅游了。“如果有钱,”他苦笑说,“我会马上离开这个国家!”
council flat顶层的景色。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论证一个《寄生虫》似的困境,不是要证明生活优渥的人就比穷困的人更有同情心。事实上,council flat里所有愿意为我开门的人,都展现了巨大的善意。采访成功率背后的差异,是一套冰冷的逻辑:一方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安全感,因此更能对外界保持开放态度,也更有空间和余力保持好奇。而另一方在持续的生存压力下,时刻紧绷神经,下意识地将陌生人的敲门当成潜在威胁。“光是活着可能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我明白,警惕和拒绝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
我目睹的一切,可能只是进一步印证了一些我们早已熟知的道理,即阶级鸿沟难以跨越,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金字塔顶端才能过上“好”生活。
然而,在这个经济下行时期、阶级固化的叙事框架以外,伦敦总会向你展示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这里总有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甚至不上牌桌的人,以诙谐的方式给予我们一些启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为保护隐私,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色柳丁BlueTangerine,作者:爽总,编辑:V,图片: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