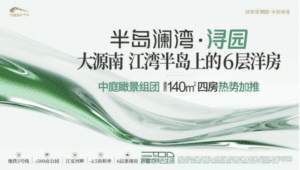选择“卒婚”的夫妻:离家不离婚,各自生活不打扰
【来源:虎嗅网】
今年33岁的圈圈觉得,楼下那个年轻男孩可能暗恋她。
两个人曾一起因为公寓大楼门打不开而被关在大厅,误了上班时间,还是男生骑着电动车送她去地铁站。此后,两人天天遇到,男生天天提出送她,她天天拒绝。
后来圈圈才知道,男生一直以为自己是单亲妈妈,因为上下班坐电梯经过圈圈家,见过她家门口有很多小朋友的鞋,却没有男人的鞋。
大部分时间,圈圈也的确过着单亲妈妈的生活,但她拒绝了一切来自异性的暧昧,因为法律意义上,圈圈已婚,有丈夫,两人已经分居两个城市近一年,是“卒婚”的状态。
卒婚,是从日本兴起的婚姻新形态,意为“从婚姻中毕业”。双方保留婚姻名义,但各自生活,不再扮演传统观念中的理想夫妻。
这一模式也出现在中国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中,用以应对低质量的婚姻。
《“夫妻互动与婚姻关系”调查结果报告》显示,婚龄在10到15年的参与者的婚姻稳定性和质量都处于最低水平,例如缺少性生活、几乎不接吻,沟通也局限在简单的事务性交流。
“我们的婚姻是被生活中细碎的小事打败的,比如拉开后不推回去的抽屉、抹布一样挂在衣架上的衣服、马桶上的尿渍……”一位和丈夫分居两年的网友说,“我们彼此小心翼翼,疲惫不堪。终于忍到达成默契,连架都没吵,有一天他没有回家,然后就一直没回来。”
一个沾了尿渍的马桶圈,就能把婚姻逼进死角。当压力即将爆表,分居成为理想的压力阀。日本作家杉山由美子在《推荐卒婚》中提到:“长寿时代的婚姻,不是忍耐的马拉松,而是自我救赎的接力赛。”
选择卒婚的夫妻,渴望从琐碎生活中获得喘息,重新考量爱与责任。而那些空间和思考,也把婚姻,和婚姻定义的生活、情感、责任乃至财产,带向了不同的地方。
一、离家之后,像逃出笼子的鸟那样自由
子文也33岁了,和丈夫、公婆一家住在一起,还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女儿。今年4月,她下定决心给丈夫发了一条消息。
“我想搬出去住,给彼此一点空间。”
“好的。”
这不是要挟、不是气话,更不是恐吓。只在微信沟通一个来回,子文和丈夫李明轩就达成了分居的共识。
在杭州萧山,子文有一个婚前置下的小公寓,原本一直空着,决定卒婚后,她开始按自己的心意打理。
子文刷遍了网上的装修风格,最终选定了“容乱率”最高的中古风。先给自己买了一张温润的木质大床,再买些铁艺的书桌和茶几,放一盏红色的台灯,还有咖啡机和留声机……子文已经想好那些空闲的下午如何度过:听着莫扎特的老唱片,喝一杯自己弄的咖啡。
她像松鼠那样一点点搬运自己的东西,塞进小公寓。一个月后,小家布置完成,子文一个人住进去。她躺在queen size的大床上,突然觉得自己飞起来,像只逃出了笼子的小鸟,尽管这只小鸟是从140平米的大房子,飞进了一间70平的小公寓。
子文布置完的新家
圈圈的离开则没有这么轻松。此前,圈圈和丈夫方块一起生活在永康,生活流程通常就是带两个小孩起床、去公婆的工厂上班、下班陪孩子玩,等孩子上楼和爷爷奶奶玩时,就关上门和方块小声地吵架。
方块是个温和的人,但有些懒,把家务推给母亲,又把自家工厂所有的工作交给老婆。他可以玩着手机,一天只翻几个身,洗澡时也把一只手伸出淋浴头外继续刷短视频。
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2024年的冬天,某次因为经济问题的常规争吵时,他竟大声吼了圈圈。圈圈气得血气上涌,心里反倒理智起来,当即做出离开的决定。
幸好她也在杭州有房。圈圈告诉父母,自己跟丈夫吵架了;又告诉公婆,孩子将来要去杭州上学,需要提前适应环境。随后,她便收拾了行李,坐上前往杭州的高铁。
窗外的树光秃秃,圈圈心里冰冰凉。“要离婚!”她当时心里这样喊。
不过,夫妻之间复杂的财务关系、孩子的抚养问题摆在眼前,以及可预见的两家父母的反对。圈圈也知道,这件事急不来。她决定先享受“单身生活”。
“杭州的空气都是甜的。”圈圈开玩笑说。
在物理上远离了丈夫和丈夫家人每天都在念叨的工厂债务后,她可以找老友喝酒、聚餐,一个人去看电影。大到找工作,小到晚上吃什么,她自己决定所有事。
在独处时光中,子文和圈圈感觉自己剥离了家庭责任,摆脱了妻子、母亲、儿媳这些身份,短暂地成为了自己。重新掌握主动权后,她们调侃自己仿佛是在“报复性生活”。
在永康连绿萝也不养的圈圈,在杭州家里养了一大堆植物,霸王蕨、龟背竹、麒麟瓜椒草、鱼骨仙人掌、龙鳞,高低错落摆满客厅和阳台,屋子仿佛热带雨林。
圈圈家里美丽的植物们
离家的理由不光是逃离,也包括主动寻求自我。
社交媒体上,有些夫妻选择卒婚是因为工作城市不同,两人都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投奔对方,但离婚又要面对财产和抚养权分割等种种问题,跟家人朋友都不好交代,索性保持现有关系,“从婚姻中毕业”。
2004年,日本《断舍离》的作者山下英子提出了“卒婚”的模式。她曾在女性杂志做过调查,发现大家最想“断舍离”的竟是自己的丈夫。
山下英子对此深有同感。她曾在老家丈夫的诊所当会计,后来为了写作事业,她独自前往东京打拼。“断舍离”丈夫之后,她仍与丈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互不干涉生活,偶尔见面,互相支持。
“卒婚”已经在日本流行开来,201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约有30%的夫妻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目的是“在婚姻中重获自由”。
二、被逼进死角的婚姻
对子文来说,自由意味着她终于可以砸东西了。
每年的七八月,她都会没缘由地暴怒,但此前,她没有砸东西的“资格”。有一次,与婆婆发生口角,子文把手上的锅往台面放,稍重了点。婆婆说:“你不要砸我们家的东西。”
但在这个夏天,她可以把情绪无所顾忌地发泄出来。在自己的小公寓里,有时候情绪突然涌上来,她会把手上的东西狠狠砸掉,脾气发泄完,再平静地把一地狼藉收拾干净。
独居中的子文
子文也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诊断她这种夏日暴怒症状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
2020年夏天,子文的女儿出生,随后她经历了一个极其压抑的产后恢复期。天气一热,就会唤起当时的情绪。
那时候,婆婆会突然闯进她的房间,指责她懒惰,也会在她乳腺炎后责怪她吃退烧药,影响孙女喝奶。而丈夫总是站在一旁闷不做声,仿佛一个外人。
子文知道,自己才是那个外人。她只身住进丈夫的家,学着丈夫那样忍受婆婆的强势,她没有自己的桌子,连在厕所台面上放一瓶乳液都要问婆婆:“我能放这儿吗?”
子文闯进了丈夫李明轩的原生家庭,才发现对方和恋爱时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李明轩是一个程序员,会骄傲地向子文介绍自己写出的系统,子文爱上了他。这个他,节俭、老实、懂得多。但回到家里,丈夫变成了另一个人,唯唯诺诺、妈宝、从不和妻女站在一边。
当爱被消磨,伴侣的习惯逐渐变得不可忍受。
子文开始讨厌他的节俭,讨厌他不舍得扔撕烂的快递包装袋,也讨厌他为节省几块钱商场停车费而把车停到几百米外,还讨厌他每天早上起来抢各个APP积分时满足的笑脸。她不希望丈夫只把精力放在省钱上,安于自己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和算不上多的工资。甚至,丈夫这笔工资也全用来还房贷,养育女儿和其他所有家用都由子文掏。
爱情不见了,子文开始觉得每次亲热都变得十分难熬。她曾严肃地告诉丈夫:“我对这样的人,实在提不起性欲。”话静悄悄落在空气里。李明轩不回答、不改变。在子文一次次的拒绝后,这对中年夫妻也已近两年不再有性生活。
他们成了一对没有爱、没有性、没有钱、没有体贴和陪伴的夫妻。交流永远只有一个来回,一个人提出要求,另一个人说:“好的”“哦”“知道了”。子文不死心,抓着李明轩吵架,而他只会安静地坐在床尾。子文一拳打在棉花上,越来越像一个疯女人。
子文不能真的躲进阁楼变成疯女人,她选择走出去,实现“精神上的离婚”。
搬出去三个月后,李明轩给她发微信:要不然我们离婚吧。子文回:“你可以去起诉我,否则我不会离婚。”子文想得清楚,她无法承担离婚的风险,她怕女儿的抚养权会被工作稳定的丈夫抢走。她需要合法婚姻保护女儿的利益。
李明轩的离婚请求也更像一次情绪发泄。
三天后,他又发来信息:“我不想离婚,我们再想想。”
三、在婚姻间隙里,划出一片个人空间
对中年夫妻来说,离婚往往是有代价的。
比如“在市场低点卖掉共同拥有的房子不划算”“各自背一笔贷款太辛苦”“财产被动分割可能导致公司估值受影响”等等。太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得不考虑财产、孩子的抚养、父母的赡养以及各种外界评价。
圈圈也决定不离婚了。她没办法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两个孩子,更不能忍受把两个孩子分开抚养。在享受了几个月的单身生活后,她把一儿一女接到杭州,儿子就近上幼儿园。女儿太小,只好把婆婆一起接来带娃。方块接手了工厂工作,会定期打来两个孩子的生活费。
在中国,“卒婚”更像是离婚之外的保守选择。虽有零星尝试,但没有法律和习俗可依。
盈开律师事务所律师祝怡解释,这其中存在诸多法律风险。
首先哪怕夫妻双方在事实上结束了婚姻关系,但法律上仍是夫妻,需要履行诸如彼此忠诚等义务。即便两人商议保持开放关系、约定财产分配。但如果一方提起诉讼,仍然可以通过证据认为对方是过错方,要求财产重新分配,付出的财产也可能被追回。婚姻关系中也不能分割监护权,也很难追究一方争夺藏匿孩子的责任。
“钱和孩子,婚姻的两大核心,都是风险。”祝怡说。
但总有人坚持婚后独居,即便是冒着法律风险。
今年36岁的西子就是如此。她的第一段婚姻也是分居时间居多,丈夫在南方工作,她受不了没有暖气的冬天,跑回西安和父母住在一起。难得的夫妻同住时间里也常常争吵。西子怕热、丈夫怕冷,他们每晚都要抢夺空调温度的控制权,吵到一人去沙发上睡。最后,四年的婚姻以丈夫出轨而告终,她带着儿子回到西安独住。
第二段婚姻,她依然坚持分居。“一个人住真是太爽了。”西子说,她洗完澡可以不急着穿衣服,想把空调开到几度都不用考虑另一个人怕冷怕热。大段独处的时间,她就用来看书、在聊天室谈天说地,也和现任丈夫在微信聊天,听他汇报这一天的事迹。
西子偶尔去丈夫家里,从不留宿。在那个家里,床头随意摆着烟灰缸,衣服随手扔在沙发上,电脑键盘的“wasd”四个键磨得锃亮——丈夫有时会通宵打游戏。西子知道,他一个人住也格外自在。
丈夫每周来一两次,按照西子的要求,洗完澡才来,尽量不抽烟。即便这样的频次,两人也曾因为马桶圈大吵过。丈夫后来表示自己一定坐着尿,不会在马桶上留下尿渍。
马桶圈一直是干净的,爱情也新鲜了。
西子甚至不再要求丈夫忠诚。她一度对性事不感兴趣,便允许丈夫在外有女友,唯一的要求是,得让她知情。丈夫也做到了,允许她翻手机,聊天记录和消费记录全部透明。
西子在关中平原,却摸索出一套摩梭人的生活方式。女人住在自己的家里,“走婚来的男人不需要永远在、永远爱我,我只需要你在我身边的时候爱着我。”
四、卒婚后的伴侣,变回了一个“好人”
妻子和母亲都去了杭州,方块被独自留在永康,他不得不自己动手做家务。接手了工厂的工作后,一大堆债务直接摆在他面前,他才终于体会到妻子曾经的焦头烂额。
失去妻子的危机感突然涌上来,方块再次道歉,甚至主动提出:两人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治疗他们的婚姻。
“你老婆受了很多委屈。”心理医生告诉方块。
隔着两个城市的距离,圈圈和方块儿的交流变多了,两人的聊天内容终于不局限于“孩子”这个唯一的话题。圈圈在杭州见到的很多事儿,都忍不住想与方块分享。小孩教育的话题,他们也会一起去翻书。
在恋爱前,两人一度是朋友,现在,婚姻的空档里重新生出了友情。周末,方块会来杭州,主动规划带孩子出游,还主动干家务、拖地、给植物浇水、尝试着做一家四口的饭。
《普通心理学综述》的一份研究显示,影响中年人婚姻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是:工具性目标。即伴侣能不能共同分担家务、一起管理家庭财务、承担抚养孩子等责任。
工具性目标的实现后,别的目标终于有机会渐渐浮现。
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曾提出“流动的爱”,意为爱情不再局限于狭义的夫妻之间的浪漫爱情,而流动成为一种更温暖的能量。圈圈和方块的爱情在友情中又流动起来。曾经总在吵架中不了了之的性生活也回来了。两个人已经半年没有再吵架。
子文则确信,被消磨完的爱情不可能重生。她专心享受独居生活。每周三天陪伴女儿,抽空做自媒体分享生活,房间里那株天堂鸟越长越高。
她曾想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好妻子,所以总在忍。顺应那个家的习惯,与婆婆发生矛盾也不想让丈夫夹在中间难做,丈夫拿不出家用她就主动承担。现在她想开了,不再被“好妻子”绑架,她只做她自己。
子文和女儿在香港街头游玩
丈夫李明轩仅仅成为了她育儿的合作伙伴,“你不会跟同事要求情绪价值吧?”
在这个过程中,她再度发现李明轩的优点,对她父母客气孝顺、会为丈母娘体检跑上跑下、会主动做家务、对孩子也好。
七月是女儿的生日,李明轩早早来陪女儿和女儿的小客人们。
“冰箱里有喝的自己拿。”子文和他打完招呼,便回厨房做生日大餐。客厅里,李明轩专心陪女儿下围棋。晚些时候,客人们来了,大家摆开飞行棋,一个大人几个小孩,玩得咋咋呼呼很是热闹。
子文安静地看着这些。“只要不来跟我谈感情,一切都很好,”她给丈夫下了定义:“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对我孩子很好的外人。”
她从婚姻中毕业了。
(未标注图片来自受访者,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作者:洋平,编辑:三金、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