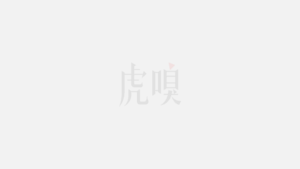历史上的他们,让今天的故宫更鲜活
【来源:虎嗅网】
20多年前,对于故宫博物院历史的研究很少,仅有《故宫沧桑》《紫禁城的黎明》等几本薄薄的小册子。《故宫尘梦录》是故宫前辈吴瀛的著作,正是这本书,让章宏伟与这段历史结下不解之缘。他自告奋勇接下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从此他进入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复杂悠长的历史之中。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的。明清两代,有二十四位皇帝在这里统治中国,创造了帝制时代最后的荣光,也吞咽了衰落带来的种种苦果。”章宏伟将笔触触达1924年10月——北京暑热退去,秋风乍起的时刻,一场烈度更强的风席卷了古都,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11月5日下午5点,天光开始暗下来,“溥仪及他的后妃,后面跟随宫女太监多人,最后是绍英等四人,最后面是摄政王,步行由御花园而出”。
1925年10月15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同人摄影。(图/由被访者提供)
随后,主要宫殿和场所被留守故宫的国民军士兵和警察贴上了封条,加了锁。最后的封建王朝,遗留的“辫子”被彻底剪短。
故宫的历史性时刻开始倍速出现,无论大小,都让我们得以重返“现场”。
段祺瑞召开国务会议议决办法五条,为日后故宫博物院名正言顺地诞生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点查清宫物品,“天字第一号物品”竟是“二层木踏凳”,这仅仅是因为踏入天字号乾清宫殿门时首先点查的便是此物;当“故宫博物院”的牌匾被悬挂于神武门门楼之上时,故宫内早已人头攒动;第一次向市民打开大门的故宫,收费标准是“券价每张大洋壹圆”,开院当天及第二天半价优惠。
对于1925年10月10日那天的盛况,章宏伟在书中评价道:“驱逐溥仪出宫、建立故宫博物院,将紫禁城这座昔日皇帝居住的禁区变为人民自由参观的场所:一座国家博物馆。”
1925—1949年,这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故宫博物院的记忆,被章宏伟从历史深处一点一滴地打捞出来。他通过研究李煜瀛、庄蕴宽、赵尔巽、江瀚、王士珍、易培基、马衡这7位掌门人的事迹,将一座国家博物院风雨飘摇、命运多舛的历程呈现于世间。
建立一座国家博物院
历史专业出身的章宏伟喜欢做考据文章,“不愿意拿到一些材料就说话”,他下了最多功夫研究的人是李煜瀛这位故宫博物院的开拓者。章宏伟感慨,人们对于李煜瀛的名字已经很陌生了,哪怕是故宫博物院,也仅仅是把他的名字放在历任领导的行列而已,但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他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需要善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应运而生,李煜瀛被聘为委员长。1925年9月29日,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临时理事会成立后,因为没有选举董事长、理事长,李煜瀛以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主持故宫博物院,李煜瀛当时的地位可想而知。然而,关于李煜瀛的资料却寥寥无几。
从内右门出宫。(图/由被访者提供)
章宏伟得知,中国台湾地区有人专门为李煜瀛写了一本传记,只有不到5万字;有本年谱,也只有不到5万字。此时,上海图书馆已经做了民国时期的报刊数据库,“我每天坚持去查看数据库、复制资料,一天最多能复制2万字”。经年累月地进行多方考据、资料整理后,章宏伟编出了李煜瀛年谱(未公开发表),约500万字,书稿打印本一共装订了27册。
在《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章宏伟给7位掌门人每人一句概括语,其中,他用“拨云见日的开拓者”来形容李煜瀛。
在清宫物品点查过程中,李煜瀛等人考虑到故宫“关于历史文化者甚巨”,只有把这项“革命事业”转化为“社会事业”,方不致“受政潮之波动”的影响。这种理念很大程度上源于李煜瀛早年的留法经历,他在巴黎见到曾经的“狼宫”在法国大革命后,被改造为罗浮博物院。于是,李煜瀛首倡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不许溥仪复宫,保护国宝安全。他还手书“故宫博物院”几个大字,在成立典礼当天,这块匾额被高悬于神武门之上。
100年前,悬挂着这块匾额的神武门被定格在方寸之中,而今,这张历史照片被印在《故宫掌门人1925—1949》附赠的藏书票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则印着李煜瀛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时的讲话:“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
这是李煜瀛建设故宫博物院一贯的理念。事实上,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李煜瀛等人就效仿西方的管理方法,为建立现代博物馆的基本原则和体制而奋斗。1925年9月29日,李煜瀛召集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设“古物”“图书”两馆,采取董事会监管制和理事会管理制……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构建了中国现代博物馆的雏形,同时也是当时推翻帝制的革命力量的象征,蒋复璁如此评价:“在十六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未到达之前,这个故宫博物院象征着革命力量已经到达了北平。”从这个意义上看,章宏伟认为,李煜瀛功在首位。
让被遮蔽的历史,从烟尘中走出来
“这7位掌门人中,原本有两位不在此列,他们是庄蕴宽和江瀚。”章宏伟说,原因很简单,其他5位之所以被称为掌门人,是因为他们都是政府正式任命的,而庄蕴宽和江瀚并非政府任命,严格来说,他们只能算作“准掌门人”。
不过,经过深思熟虑,章宏伟还是把他们二人放到了与其他人相同的地位之上。在章宏伟的笔下,庄蕴宽作为过渡性人物,他是“岿然不动的守护者”。“三一八”惨案后,李煜瀛遭通缉,新委员长卢永祥未到职,被推为副委员长的庄蕴宽受命于危难之间,出面维持故宫博物院院务。他先拒直鲁联军进驻故宫,后即便因中风无法出门,在奉军张宗昌令部下夜闯故宫“借宿”时,亦迅速命护宫人员严加把守抵制奉军进入。
江瀚亦是一位“临危受命的担当者”。在故宫保管委员会解体后,故宫博物院再次陷入院务停顿、无人负责的状态。1926年10月13日,在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数人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这一不等国务院指示便自行组织起来的维持会,最主要的职责便是应对故宫博物院无人负责的局面。当时已70岁高龄的江瀚挑起了维持故宫院务的重担。在北平危急存亡之际,江瀚为保护故宫文物建言献策,虽然他坚持就地保护的观点与文物南迁的计划相左,但从初衷来看,两者的目的却是一致的——保护故宫。
1925年10月10日,遵义门内挤满了参观的人群。(图/由被访者提供)
如果说庄蕴宽和江瀚是过渡性人物,因而不为人所知,那么作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的易培基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就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了。与故宫相关的人与事,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讲,是天生的“流量圣体”,往往有点风吹草动就引人关注,同时也会有人按图索骥。2011年5月轰动一时的“故宫失窃案”,便让不少人联想到民国时期的一桩“悬案”——“故宫盗宝案”。易培基正是因为此案而身败名裂,他执掌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也从此被遮蔽了,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易培基’这个名字只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出现过”。
1929年2月,易培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但因在南京职务繁忙,他直到1931年3月才到北平故宫履职。
1929年3月,故宫博物院组织继续清点尚未查核的清宫物品,点查三成后,随即就制定了提取库藏文物制度。同时,故宫博物院还延请专家学者成立各种专门的审查委员会,不仅对故宫的收藏进行审核与鉴定,还将分散文物集中存放,严格周密的文物保管制度被逐渐建立起来。
然而,在文物保管上建章立制的易培基,却背上了监守自盗的恶名。这都源于易培基上任后重提处分故宫物品的旧事。1927年,故宫博物院制定了《处分物品保管款项规则》,决定处理一批宫内物品。但这一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被张作霖下令缓办。1929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处分本院所存无关文化历史之物品方案”,易培基到任后,处分物品公开出售。
此举导致易培基被控盗卖国宝,遭到举报后,南京监察院派来的监察员周利生、高鲁经过调查,向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提交了对易培基的弹劾。弹劾中说:“关于盗卖古物一层,虽未查有确切证据,而出售金器一项,殊有违背法令之嫌。”不久,北平《快报》的几名记者联合检举易培基,原因是故宫博物院在出售金器时价格低,还处理了具有历史价值的金八仙碗。1933年,易培基为自己申辩,指出金八仙碗是残品,普通金店就有销售,处分物品账目也清清楚楚。他的申辩得到了临时监委会的支持,认为检举纯属无稽之谈。
1934年10月13日,易培基、李宗侗、萧瑜等9人再以盗卖古物被提起公诉,11月29日,易培基案开审。案件升级为“故宫盗宝案”。3年后,易培基等3人又被提起公诉,起诉书中指控易培基以赝品调换书画、铜器、铜佛、玉佛等物品。
他们认为乾隆及以后的文物多已品定,不应再有赝品,况且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还经专家点查鉴定过,如果现存古物中有赝品或数量上有短缺,就是被故宫博物院主管文物的人以假换真或盗走。而当时正是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兼任古物馆馆长一职,易培基被认为“犯罪嫌疑实为重大”,但检方也没有他盗卖、盗换文物的真凭实据。不久,时局急转直下,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纷纷迁往武汉或重庆,已无心处理这一桩官司了。
直到1948年1月9日,南京四开小报《南京人报》刊登了一条短讯,标题是“易培基案不予受理”,一桩横跨十几年的案子就此匆匆收场,不明不白。而该案的当事人易培基早在1937年就离开了人世,终年仅58岁。
“他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而且为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章宏伟说,正是由于易培基在任时首次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还调整了故宫博物院的职能机构、整修宫殿建筑、增辟陈列展室、创办《故宫周刊》、筹建警卫队和护卫队等,故宫博物院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时期。
视国宝为生命,文物与民族命运连在一起
如果说最初章宏伟给予最多关注的是李煜瀛和易培基,那么现在他觉得,更应该关注马衡。马衡是横跨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代掌门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章宏伟提到:“马衡没有高学历,却做了北京大学教授,这是时代造就的。我接下来可能会专门为马衡写本书。”
青年时期的马衡更像一个豪门励志故事的男主角,他家道中落,与上海巨富叶澄衷的女儿结婚并进入上流社会,“年薪6000银元,还外加分红”。但书生本色的马衡从来不流连于声色犬马,而是醉心于研究学问。1917年对于马衡而言是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节点——年初,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6月,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改为国史编纂处。这都为没有高学历但潜心做学问的马衡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遇。
1917年8月,37岁的马衡应蔡元培之邀北上,任职国史编纂处,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讲师兼教体育。1924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他又参加了点查故宫物品的工作,后来担任古物馆副馆长,“可以说,故宫博物院一成立,马衡就是核心人物”。
章宏伟说,此前他在编辑《故宫尘梦录》的时候就有判断,作者吴瀛心中对马衡“有股气”,“他认为是马衡把易培基从院长的位置上‘顶’了下来”。也因此,在编辑的过程中,章宏伟把过于主观的文字删减了很多。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大量阅读故宫所存档案并参阅时人笔记、报刊等资料后,章宏伟描摹出了马衡的基本性格底色,不张扬、谨慎,甚至唯恐出纰漏,显得有点谨小慎微。
“我觉得马衡接任院长没有可纠结的,当时国民政府从故宫博物院内部提拔新院长,第一个人选应当是张继(常任理事兼文献馆馆长),第二个就是马衡。”章宏伟认为,马衡的性格是适合掌管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他负责任、兢兢业业干事的风格能够帮助扫除“故宫盗宝案”留下的阴云。他是纯粹的学者,从不参加派系之争,并与“易培基案”毫无瓜葛。
1933年,马衡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事实上,在他任上也曾发生失窃案,但他的性格注定了他更善于在危局中周旋。
1934年,“双十节”特别开放期内,咸福宫西配殿遗失了一张乾隆写生图小贴落,马衡便在第一时间呈报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及行政院,对此事进行查核、处理和惩处。同时,马衡还听取了被处分者孙尚容的辩解,在文件阅后批示:“所呈者点,颇有见地,是供参考。本院现对此案尚在继续侦查中,该员如有见闻足资研究者,仍望随时呈报。惟在未获确据以前,应慎重发言,免淆真相。”
对于马衡而言,组织文物南迁的点查和文物西迁工作才是他任上的主要课题和考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全面抗战在所难免,战火一旦燃烧到华北,北平肯定难以幸免。为保护文物安全,故宫博物院启动文物南迁,“南迁使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与民族独立、民族尊严连在了一起,培育和形成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
事实上,重要文物装箱南运,是对马衡组织能力、工作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尤其是石鼓的装运。石鼓是承载着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物,10个石鼓,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已经分离,稍有不慎,石皮就会落下来。马衡本身就是研究石鼓文的专家,他认真研究装运办法,并亲自押运,此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未见新的损伤。
故宫文物南运历时近4个月,至1933年5月23日,共运出五批文物到上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故宫文物被迫西迁,亦创造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传奇。当时,文物分南路、中路和北路三线向后方疏散,开始了长达10年的漂泊。马衡随中路同行,亲自考察每批文物的存放地。
其间,文物在国难日深的时局之下,命运多舛又多次绝处逢生:日军轰炸贵阳时,文物刚刚迁出,躲过一劫;从汉中运往成都,路途非常颠簸,翻车时有发生,不过都是回程空车,即便有过一次装运文物的车辆翻车,但装载的都是档案和书籍,翻车下去的河道恰是干涸的。那志良感慨道:“有人说,文物是有灵的,炸弹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运走之后,那个地方被炸;现在翻了车,也毁不到它。”马衡本人也说:“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此后,马衡又组织了文物东归。在国民党迁往台湾地区时,行政院多次函电他选择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菁华装箱分批运往南京,与南京分院的文物一同迁往台湾,但此时马衡做出了保护国宝、拒不赴台的决定。
对于在《故宫志》“故宫历届领导名录”中未出现、“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的赵尔巽,以及短暂掌管故宫博物院的王士珍,章宏伟也将他们单列一章。这正如书中所说:“介绍这些掌门人的生平行事,既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也是对故宫博物院历史的一种尊重,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保护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故宫的不易,对这些文明守护者生出由衷的敬意。”
从1925年到1949年,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又国难深重的时代,无论是开拓者、维持者还是守护者,故宫博物院的掌门人既是时代的过客,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正是因为他们,才让故宫成为今日更鲜活的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