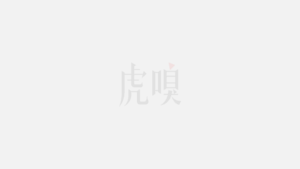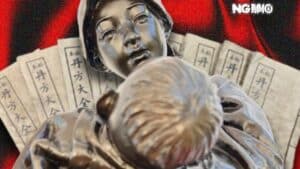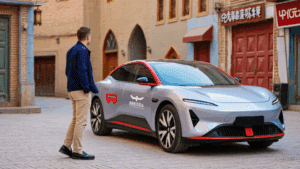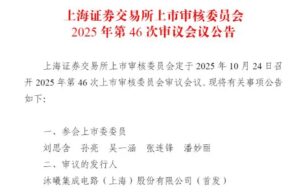日本就业冰河期:一代年轻人被冻结的青春
【来源:虎嗅网】
2023年12月,日本内阁府正式推出了“就职冰河期世代支援计划”(《就職氷河期世代支援プログラム》),向1993年~2004年间毕业、至今仍未进入稳定雇佣状态的45~54岁群体,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补贴。这一迟到了近二十年的举措,将一段长期被隐蔽的社会创伤重新拉回到公众的视野。
在日本,“就业冰河期世代”(即就職氷河期世代)是一个精确的时间标签,指的是那些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踏入职场、却遭遇企业大规模缩招的整整一代人。
这一代人的困境早已渗入日本的文化。无论是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中靠打零工维生的边缘家庭、村上春树笔下的“悬浮青年”,还是NHK纪录片《无缘社会》中那些与家庭、职场、社群彻底断裂的个体,无不折射出同一个结构性现实:当经济增长停止,最先被牺牲的,往往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据厚生劳动省《大学卒業予定者の就職内定状況》的统计,1992年,日本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正规雇佣率(即签订长期正式劳动合同)为74.3%,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了55.1%;同期,非正规雇佣(包括派遣、合同工、兼职)的比例从12.6%攀升至31.8%。
这一断崖式的下跌,不仅改变了数百万日本年轻人的职业起点,更重塑了日本社会的代际契约。
工作机会减少,企业不愿意培养新人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形成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体系,曾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职业路径:入职即稳定,努力即晋升。然而,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企业盈利持续承压,人力成本成为首要的削减对象,这套机制首先在招聘端瓦解。
1993~2000年间,日本大型企业应届生的招聘人数平均减少了约40%。与此同时,正式岗位几乎只对应届毕业生开放,这意味着一旦错过窗口期,就很难再进入主流职场。
这种“一次性机会”的机制,使得个体的职业命运在毕业时就被锁定。2017年,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第15回出生コホート調査》显示,在1971~1985年出生的群体中,约有35%的人在30岁之前从未获得过正规雇佣。他们长期在派遣、合同工或者是兼职工作中流动,难以积累可迁移的职业资本。
招聘市场的激烈程度也折射出职场供需的失衡。2003年,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大型校园招聘会,吸引了约12万名的求职者,而参展企业提供的正式岗位大概只有3000个,竞争比高达40:1。厚生劳动省同期调研指出,应届生平均需要参加20多场面试才能获得一份工作(含非正式),部分年轻人因为长期求职失败而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2010年,日本政府估算15~39岁之间的“蛰居族”(ひきこもり)约有69.6万人,其中相当比例都和就业受挫有关。
企业的用人标准也从“培养潜力”转向了“即戦力志向”,也就是要求新人入职就要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玄田有史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经验悖论”:企业只招有经验的人,但正规雇佣岗位的稀缺,又使得年轻人根本无法获得被认可的职业履历。
结果就是大量毕业生被迫进入派遣、合同工或兼职等非正规雇佣轨道。截至2018年,1993~2004年毕业群体中仍有约97万人处于“无业或非正规就业”的状态,平均年收入仅为正规员工的58%。职业起点的落差,就此埋下了长期不平等的种子。
被延迟的社会成年
在日本社会,“就职”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完成“社会成年”的关键仪式。拥有了正式的工作,才意味着具备了结婚、买房、组建家庭的资格。当职业身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整个人生的节奏便会随之错位。
IPSS的长期追踪数据显示,1970年出生的男性35岁时已婚率为72%;而1975年出生(即冰河期初期毕业生)的男性,仅仅晚出生了5年,这一比例就跌至58%。女性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期已婚率从63%骤降到49%。婚姻的推迟直接抑制了生育意愿。IPSS与总务省联合推算,1975年出生男性终身未婚率约为28%,女性约为18%,显著高于前一代人。
这种“不敢婚、不敢育”的心态,源于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内阁府《青年の意識に関する調査》显示,20~34岁的青年中有72%的人“对未来感到不安”,其中68%将原因归结为没有稳定的工作。
非正规雇佣不仅意味着收入低下,更意味着被排除在了社会保障体系之外。2005年,日本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约合10万元人民币)的劳动者达到546.9万人,占全体雇用者的25%,这一群体被称为“穷忙族”(ワーキングプア)。
以东京为例,2005年非正式员工的平均月收入约为12万日元,在扣除平均房租(约6万日元)和基本生活开支后所剩无几。他们很多人从未加入过雇佣保险或厚生年金,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严重不足。2008年“雷曼事件”之后,企业首先裁减的也是这部分员工。
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虽然存在,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证明无存款、无收入、无亲属支援。很多年轻人因为保留了少量房租或者是水电费而被审核拒之门外。部分失业者被迫栖身于24小时网吧,被社会称之为“网吧难民”(ネットカフェ難民)。
当基本生存尚需挣扎时,组建家庭便成了一种奢望。而这一代人的集体性选择,最终在数十年后演变为少子化与劳动力萎缩的结构性困境。2023年日本出生人口跌破76万,创1899年有记录以来新低。
精神上的创伤和迟来的补偿
比物质匮乏更难愈合的,是精神与心理层面的创伤。厚生劳动省《自杀対策白書》显示,20~34岁男性自杀率在1998年达到了峰值,相比1990年上升了37%,其中“经济与生活问题”(包括失业、债务)是首要诱因。东京大学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长期求职失败者中,抑郁症状检出率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在一个强调“努力就有回报”的社会文化中,就业失败常被归咎于个人的懈怠,日本媒体与公众的舆论也一度将冰河期世代标签化为“低欲望族”“失败的一代”。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冰河期世代的困境也都被视为是社会“过渡性阵痛”,未被纳入到主流政策的议程之中。直到2010年代后期,随着这个群体步入中年,贫困、孤独死、社保缺口等问题集中显现,政府才开始正视其系统性的代价。
2019年,《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才首次承认:“就业冰河期世代因为时代原因未能获得公平机会,国家负有道义责任。”2023年推出的专项支援计划,正是这一认知的政策落地。
然而,补偿来得太晚。大阪大学经济学教授大竹文雄在一次访谈中指出,45岁以上的非正式雇员即便是再培训后,也很难和年轻人竞争那些新兴的岗位,政策效果十分有限。
厚生劳动省《2022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45~54岁的非正规雇员中,32%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远低于270万日元这一维持基本生活的相对贫困线。
而心理创伤还在代际之间传递。京都大学发表于《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论文证实,冰河期世代子女更倾向于选择“稳定但低薪”的职业路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同龄人。制度性的机会剥夺,正悄然转化为下一代的风险规避。
不该被遗忘的代价
2025年的日本职场出现了魔幻的反转:企业追着应届生涨薪、发入职奖金,广岛县甚至出现了1个毕业生对应4.31个岗位的盛况。但很少有人提及,这份 “就业繁荣”的底色,是冰河期一代人的沉默牺牲——他们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不敢结婚生子,导致劳动力缺口不断扩大,才让后来的年轻人成为了“香饽饽”。如今那些在招聘会上被争抢的应届生,或许也永远无法理解,三十年前的同龄人曾为一份温饱工作拼尽全力。
据日本内阁府估算,就业冰河期世代当前约有1700万~2000万人,年龄多在45~59岁之间,其中约100万人至今仍处于无业或非正规就业的状态,退休后将会面临严峻的经济风险。
“在时代的浪潮里,有人被推着向前,有人被留在了原地。”那些在冰河期里打零工、躲网吧、被标签定义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没有“逆袭”的剧本,只是在时代的寒意中默默承受。
如今,当我们谈论起日本职场的“今非昔比”时,其实也不该遗忘他们。倒不是为了沉溺于苦难叙事,而是铭记一个共识:任何社会转型的成本,都不应该由最脆弱的年轻一代独自承担。
毕竟,没有哪代人的青春,该被时代的冰河彻底冻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