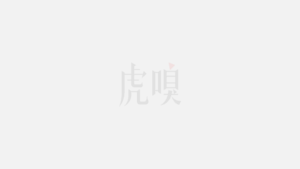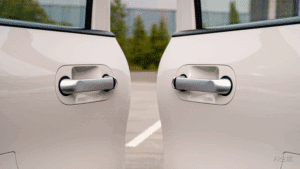斯内普的救赎
【来源:虎嗅网】
尽管哈利将小天狼星·布莱克之死怪罪于斯内普,“感到一种野蛮的快乐”,减轻了他自己的罪恶感,却无法得到邓布利多的认可。表面看来西弗勒斯·斯内普不大可信,但其实邓布利多认为他完全值得信任。将哈利的疑心归咎于情感上的幼稚,似乎是一种很吸引人的解释,可除了邓布利多之外,也没有其他凤凰社成员完全相信斯内普。斯内普杀死邓布利多之后,麦格教授自言自语道:“我们都好奇……但是(邓布利多)相信……一直相信。”她还说:“他总是暗示他有牢不可破的理由信任斯内普……但是邓布利多明确地告诉我,斯内普的忏悔是绝对发自内心的。”这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邓布利多为什么如此确定斯内普是忠诚可靠的呢?
简言之,答案是爱——不是邓布利多对斯内普的爱,不是斯内普对哈利的爱,而是斯内普对莉莉·波特——哈利母亲——的爱。尽管莉莉没有回报斯内普的爱情,斯内普也从未停止爱她,这份爱最终救赎了斯内普,虽然绕了一个大圈子。
聪明的当代读者也许会对这一段关于爱和救赎的夸大其词露出宠溺的微笑,认为J.K.罗琳实在是多愁善感。毕竟,为什么爱就是相信斯内普的原因?斯内普明显讨厌,甚至可以说仇恨哈利、小天狼星和其他几个人。邓布利多难道不应该担心这种恶意有一天会战胜爱意?还有,为什么认为斯内普已经得到救赎了?他的恨意难道不是反面证明?如果他确实被救赎了,那完全可以怀疑这些爱意和情感已经消失。呼吁爱和爱改变人的力量当然在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归根到底这种理念难道不是过时、古旧又过分简单?哲学家会怎么评价这种事情?巧的是,哲学家们真的在爱这个问题上有很多要说的。他们探寻过爱的本质、爱的种类,甚至爱是如何让我们盲目进而导致判断错误的。“波特系列”小说,尤以斯内普为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些问题的机会。
斯内普与光彩夺目的爱
从柏拉图到C.S.刘易斯,哲学家们反复探讨爱这个重要的议题。无论爱源自哪里,无论爱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光彩夺目的爱情一直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灵感来源。“波特系列”故事中,爱的重要性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主题。莉莉的爱拯救、保护了哈利。哈利的爱战胜了奇洛教授,也让伏地魔无法占据哈利的灵魂。邓布利多告诉我们,伏地魔最致命的弱点是他永远无法理解爱是最强大的魔法。
罗琳拒绝让她笔下的爱被稀释成单纯的巧言辞令或多愁善感,为此她加入了许多优秀的哲学概念。古希腊哲学家将爱分为三类:情爱、友爱和圣爱。情爱,即性爱,是指在恋爱关系中常见的爱。韦斯莱夫妇,罗恩·韦斯莱和赫敏·格兰杰,哈利和金妮·韦斯莱都是这种爱的范例。在西方哲学中,关于情爱最有名的分析可见柏拉图的《会饮篇》,书中柏拉图力图展现原始的生理欲望如何渐渐升华,提升灵魂到至臻至美的境地。友爱即友谊之爱,将友情归类为爱是非常重要的——正如邓布利多观察到的那样,伏地魔辛酸可怜,从未有过朋友,也没想过要得到朋友。其实,对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来说,友情一般比爱情更崇高。第三种爱,圣爱,是指普世的、献身的、无条件的爱。《福音书》作者们告诉我们“上帝是爱”,他们所指的就是圣爱。
传统哲学对爱的解释帮助我们理解斯内普这个复杂的角色。传统哲学强调爱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选择、一种意志行为。理想状态下,我们的情感将与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保持一致,但我们也可以在感情不接受的状况下行为向善。斯内普内心的情感冲突并不能证明他没有被爱转化。正相反,斯内普能够压抑住内心对这些人的冷漠,甚至是厌恶,一直为他们的利益工作,证明了他对莉莉的爱之深。
被抛弃的男孩们
斯内普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角色,部分因为他和哈利、伏地魔的出身境遇相似。他和哈利、伏地魔一样,出生于混血家庭,因此无论是在麻瓜世界还是巫师世界都有可能被怀疑、被仇视。他迫切想要拉近与母亲普林斯一家的联系,淡化自己的麻瓜血统,因此自称为“混血王子”。斯内普的父母长期不和,他在霍格沃茨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又和哈利、伏地魔一样——他利用魔法的力量,在巫师世界找到了自己的盟友。如同哈利注意到的那样,他、伏地魔和斯内普,“被抛弃的男孩们都在那里(霍格沃茨)找到了家”。三个人都被分到斯莱特林,只有哈利最后选择去格兰芬多。
当然,哈利和伏地魔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伏地魔选择权力,放弃了爱;选择自私,放弃了无私;选择征服,放弃了脆弱的友谊和其他所有发自真心的情感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利向朋友们敞开心扉,愿意为他爱的人牺牲自己。伏地魔选择了碎片化的灵魂,哈利没有,他让朋友们帮助他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正直、完整的人。
罗琳花费了很多笔墨描绘哈利和伏地魔各自代表的正义与邪恶。但是第三个迷失的男孩呢?那个复杂的黑暗与光明的混合体呢?那个杀害邓布利多的双面间谍呢?那个哈利的保护者和敌人呢?斯内普为何如此作为呢?
斯内普和大脑封闭术
斯内普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不仅仅因为他是故事里的双面间谍,还因为他过去和现在忠诚的对象有所不同,更因为他的情感与理性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最开始,斯内普是一名食死徒;获得救赎后,邓布利多要求他在黑魔头回来期间扮演告密者这一危险的角色。要这么做,斯内普必须完全赢得伏地魔的信任。他既不能抛弃对邓布利多的忠诚,也不能违背自己要保护伏地魔的敌人,尤其是哈利的誓言。他对哈利(包括其他人)的愤怒和厌恶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他一直冒死抵抗伏地魔的勇气。
斯内普选择保护哈利和其他伏地魔的敌人,并非因为对这些人怀有强烈的私人情感——那种毛茸茸、暖乎乎小动物式的情感,那些肤浅的、寡淡的关于爱的概念。相反,尽管斯内普很不喜欢这群人中的多数,他依然尽己所知地选择做对他们有益的事情。爱被认为是利他的欲望,不仅罗琳这么写,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到M.司各特·派克,众多写爱的作者们都这么认为。
他们都认为,友谊之爱表现为心甘情愿为他人谋福利。 “波特系列”故事中反复出现这种选择:是为了自己表面的利益牺牲他人,还是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爱需要自我牺牲,要将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爱会让人害怕失去、容易悲伤,也会加强一个人向善的意志。
这些思想家们同时强调,当强烈的情感影响到我们的理性和意志时,可以引发道德向善或向恶。换句话说,当感情影响到我们对于善恶的理解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特别是在斯内普这个案例中,爱主要不是经由感觉发现的,而是行为。爱改变了他的信仰、盟约和行动;他因为爱而忏悔,也因为选择为爱行动得到救赎。简言之,正是斯内普对莉莉的爱让他采取行动,并因此获得救赎。
邓布利多意识到哈利和伏地魔能够互通情感和思想时,他请斯内普教哈利大脑封闭术——一种能够封闭“头脑,使其免受魔法入侵和影响”的法术。伏地魔在读取他人的思想和记忆方面有非常高超的技巧,因此能够几乎分毫不差地发现对方是否在撒谎。“只有擅长大脑封闭术的人,”斯内普说道,“才能封住与谎话矛盾的感觉和记忆,在他面前说谎不被发现。”
作为邓布利多的双面间谍,斯内普经常要做到大多数人一次也做不到的事情:成功地在伏地魔面前说谎。斯内普成功完成任务不仅因为他的机智和狡猾——每次总是透露恰好足够的信息让伏地魔相信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间谍,同时又能够保密最重要的信息,他能成功也完全是因为超凡的魔法技巧。
斯内普擅长大脑封闭术这一点,同时揭示了他性格中的优势和劣势。一个擅长大脑封闭术的人需要清空自己的私人情感,哈利就做不到这一点。斯内普因此发火:“骄傲的、感情用事的傻瓜们,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沉溺在悲伤的回忆中,让自己那么容易受刺激——一句话,软弱的人,他们在伏地魔的黑魔法面前不堪一击!”斯内普能够活下来,并不是因为他放弃了对莉莉的爱——像伏地魔放弃所有的爱和友谊那样。尽管这种隐藏记忆和情感的能力对他双面间谍的身份来说非常重要,但这种能力也同时让他远离了友谊。
《死亡圣器》的最后一章揭秘了斯内普的牺牲之大、勇气之强。他被纳吉尼咬成重伤,垂死之际,斯内普把一连串的记忆交给了哈利,这些记忆记录了他对莉莉的爱,也记录了他在秘密保护着伏地魔的敌人。斯内普至死都是一个完美的大脑封闭术师,他的记忆无法被夺取,只能由他自愿提供。只有在垂死之际,他才允许哈利看到他的想法、体会到他的感受,揭秘哈利是最后一个魂器,同时告诉哈利必须做什么才能战胜伏地魔。
斯内普的选择
自孩提时代起,斯内普就爱上了莉莉·伊万斯,但一开始这种爱很自私——他看着她的时候带着“不加掩饰的贪婪”。带着一半的麻瓜血统,斯内普梦想进入霍格沃茨,逃离家庭,获得巫师世界的接纳。但在霍格沃茨,他依然是一个笨拙的外人,常与詹姆·波特敌对争斗。因为对詹姆·波特来说,所有的一切,尤其是魔法和魁地奇,都来得那么容易。更糟的是,斯内普知道詹姆也爱上了莉莉。
对莉莉的爱开始拯救斯内普,尽管这拯救最初来得十分缓慢。当莉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问斯内普麻瓜出身的巫师会不会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斯内普犹豫了一下,但依然回答没有。莉莉进入青春期,驳斥了斯内普当时错误的信仰——巫师血统的优越;她在詹姆和朋友面前为斯内普说话,却被恼羞成怒的斯内普骂成“泥巴种”。虽然后来斯内普道歉了,但莉莉毅然拒绝以后再为他辩护。二人的友情从此破裂,斯内普选择了黑魔法和食死徒。但此后他一直记得这次痛苦且代价昂贵的教训。当校长时,他斥责菲尼亚斯·奈杰勒斯用“泥巴种”称呼赫敏·格兰杰。
斯内普尽职尽责地向伏地魔报告自己偷听到的预言,说将有一个孩子能够挑战黑魔头。然而很快,斯内普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向邓布利多求助,请求他保护莉莉。邓布利多问他:“你就不能求求他饶了那位母亲,拿儿子作为交换?”斯内普告诉邓布利多他试过了,邓布利多如此回答道:“你令我厌恶……那么,你就不关心她丈夫和孩子的死活?他们都可以死,只要你能得到你想要的?”当时斯内普的爱还不纯洁;他并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二个自己”那样爱莉莉;他想为莉莉好,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他自己。如果他真正站在莉莉的立场,那就应该也要保护对莉莉来说重要的人。于是斯内普不再拒绝,承诺邓布利多只要能够保护住莉莉一家,要他做什么都可以。莉莉死后,邓布利多让斯内普出于对莉莉的爱,保护她深爱的儿子。
斯内普对莉莉的爱情,一开始沾染了自私,却在接受了邓布利多提出的扮演间谍的条件后得到了升华。柏拉图在《会引篇》中思考了相似的爱的升华,书中展现了许多不同的角色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描述、赞美爱。《会饮篇》中,苏格拉底的老师——狄奥提玛宣称:“爱是想要永远占有美好。”这种“占有”美好并非在肤浅的情爱中满足私欲,也并非只重视被爱的人能为自己提供什么,而应该是一段关注被爱者的关系:让爱人者以“独立之善”的身份靠近被爱者。
爱人者追求的是“孕育美”,这种美既可以指孩子,也可以指思想,还可以指美德。爱让父母竭尽全力地爱自己的孩子;爱会建立美德,会在爱人者身上建立神性之爱;爱通过这些方式通向永恒。罗琳展示了这两种爱。詹姆和莉莉因为爱心甘情愿地为对方牺牲,为哈利牺牲。斯内普对莉莉的爱情尽管没有得到回报,却渐渐让斯内普心生美德。在斯内普致力于反抗伏地魔之后,他身上早期的自私慢慢褪色消失了。
回想基督教的传统话语,浪漫爱情有使人改过自新之力。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评价爱是“爱望向永恒。爱其实是‘狂喜’,但不是一时的迷醉,而是一场旅行,一场从封闭的内向自我的出逃,一场通过无私奉献到达自我解放的出逃”。对莉莉的爱促使斯内普超越了自私的欲望,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即便在莉莉死后,斯内普对莉莉的爱也一直没有改变,这种爱激励着他,让他的爱变得越来越像她的爱,让他的爱由自私转向利他,转向自我牺牲。对莉莉的爱让斯内普像詹姆和莉莉那样,挡在了伏地魔和哈利之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